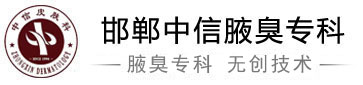为什么有的哈雷车把那么高?起源竟是因为狐臭?
提到高把机车,喜欢摩托车的朋友们脑海中一定会闪现出这样的画面:高扬的车把、拉风的坐姿、放荡不羁的骑手,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浮夸!
这种高车把设计在英文里叫做“Ape hanger handlebar”,翻译成中文就是“猿猴车把”,从下图中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为什么这种高车把叫做“猿猴车把”:
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太喜欢“猿猴车把”的摩友们吐槽说高车把设计不过是一种潮流,设计它的目的是让骑手看起来够“坏”够“酷”。而且高把手设计不仅没有任何实用性,还会对骑行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样的设计会使骑手在骑行过程中不太舒服。
许多第一次尝试过高把机车的骑手,在长时间骑行后都会出现因为把手太高使得双臂变麻木的情况。
此外,大多数大高把都设计的和普通车把一样宽,有时甚至更宽,所以这样的设计在“钻车缝”时也非常的不便。
那么问题来了,看起来并不实用的高把机车当时是因为什么被设计出来的呢?为了得到解答,我特意去搜索了一下高把机车的起源,却得到了各种不同又有趣的答案:
防止被路上的陷阱斩首
在旧时代的美国,马路附近的居民们经常被摩托团伙骚扰,于是他们会挂上一根横穿马路的绳子或者铁丝来教训路上肆无忌惮疾驰而过的摩托团伙。作为领队的骑手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脖子不受伤害不得不把他们摩托车的车把升高,防止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被突然出现的绳子斩首。而这种高车把的设计也因为其独特而炫酷的造型逐渐被其他车手模仿并流行起来。
电影《13骇人游戏》中骑手们被路上铁丝斩首的镜头,原片比较血腥所以打了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观看
关于提高车把的设计是为了保护骑手不被斩首还有另一个说法:二战时德军会在马路上骑手脖子高度的位置设置带刺的铁丝。盟军骑手们在高速骑行的过程中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被这些铁丝伤到脖子。于是军用摩托车的车把开始升高,并安装了切断铁丝的工具以保证骑手们的生命安全。战争结束后,虽然没有了被斩首的危险,但高车把的设计得以保留并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汽摩大战中的防护措施
也有人提出大高把起源于南加州,刚开始实行摩托车车道分界线行车(Lane-Splitting)时一些摩托车骑手经常违规行车,愤怒的汽车司机会拿将扫把柄伸出车窗外给不懂事的摩托车骑手一个教训。骑手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脖子,车把也变得越来越高,高车把也就成了骑手们上路必要的防护措施。
车把越高,腋下越干爽
还有一种说法把高把设计和腋臭关联到了一起。在高把摩托车出现之前,长距离骑行的骑手在长时间骑行的过程中腋下容易出汗,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湿热的腋下严重影响骑行体验,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异味。于是注重形象的骑手们把车把升高,让风直吹腋下,在骑行过程中时刻保持干爽。高把摩托成了有腋臭的骑手们的福音,同时炫酷的外形和特殊的骑姿引得其他骑手们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了“Ape hanger handlebar”的潮流。
虽然部分摩友觉得高把机车骑起来并不舒适,但是对于一些喜爱高把的朋友,尤其是身材高大的摩友们来说“猿猴车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觉得适当高度有利于强迫驾驶者坐直身躯,同时可以防止长时间骑行中造成的颈、背酸疼和灼痛感。
另外,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灵魂的骑手们非常乐于享受享高把摩托带给他们的浮夸与张扬,付出一些驾驶的舒适性和经济性也就变得不算什么了。
当然在一些极端“猿猴车把”爱好者的眼中车把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车子可以破,但车把一定要高
老铁,你这车把怎么看后视镜?
臂长不够,身高来凑
关于高把机车你还知道什么其他的起源故事或有趣的想法,可以留言与大家一起分享哦~
警察抓150人后,南宁的鬼火少年骑着自行车去翘头
在南宁的"火车头",每当凌晨来临时,这里就成了中国的洛杉矶。
"火车头"是只有鬼火少年会用的称呼,指的是动物园后面的一个路口,因为摆放着一辆老式火车头而得名。
也许广西和西海岸唯一有联系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有一个"西"字儿。但是他就是带着自己特有的、独一无二的狂野劲儿,在路口上培养除了盆景一样的"thug life"。
从去年后半年开始,因为修路,这里曾经是个不大的公园的地方,它前面的公路成了封闭路段。最开始只有稀稀拉拉鬼火少年,和三五成群过来围观小弟小妹们。他们在快手上联系,约定好暗号出车。三阳鬼一是最有面子的座驾,是可以在后座拉一个"黑麻麻"最好的工具。大多数是些中学生,他们已经彻底不习惯了和任何长辈或者是成年人的沟通,白天的相处只是沉默或者尴尬地转头走开,到了夜晚,才会骑在摩托车上发泄多余的精力。
"我们开车的当然是讨厌,但是南宁没有给小孩子们玩的地方啦。他们不玩这个玩什么呢?"把我拉向火车头的司机用浓郁的南宁口音这么告诉我。
渐渐地这里开始聚集摇着花手的小美、开跑车轰鸣着汽笛原地飘逸打转的富二代们和喜欢突然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毫无征兆地跳舞的本地小网红,高架下面不大的封闭路段成了城乡结合部的地下Club。
当然这里的主人永远还是那些鬼火少年们,在这里想要收获喝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表演翘头。更好的翘头技术是成为"火车头"核心圈的资本,当然除了技术,可能他们更多仰仗的是胆子和创意。
*图片来源b站@狐臭味的拿铁
这场派对终止于3月17日,南宁警方组织了一次专项整治活动,当晚50人被捕、150辆鬼火被没收。
但是在18日,第二天,看到他们骑着自行车翘头,换了另一种形式挑衅警察的场景。也许这些鬼火少年们从来没有听过2pac和Wu-tang是什么,但是他们可能比全中国大部分地下说唱歌手都知道《冲出康普顿》的真谛是什么。
*图片来源b站@狐臭味的拿铁
*他们自己制作的表情包
随后火车头被连夜钉上了密密麻麻的减速带,从此之后南宁马路上看见长得像鬼火的车就需要接受检查,警察也开始一家家地走访曾经有些灰色性质的改装店,曾经火车头的几个漏网之鱼的高层也被从家里一路请到了局子里。
对于鬼火少年来说,曾经热闹的火车头,如今也只剩下隔着几百米就能看见的亮着警灯的警车,来来回回,成了维护这里热闹的最后一份子。
大多数人没有资格去评判合适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子。对于鬼火少年们和火车头来说,让他们归于沉寂也许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事情。甚至说火车头的消亡是一个积极有益的事情。但只是偶尔就像那些无力的绝唱——骑着自行车“翘头”的场景,几乎发出了和绝大多数街头文化类似的声音。
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声嘶力竭却无路表达的,年轻人独有的活力。
这不到一年中火车头的变化很大,它的社区氛围相对独立,从头到尾没有太多外来文化的影响:足够自主、几乎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有太多来自其他人的评价,它的商业结构也都是原生的,由内而外的。
*图片来源柳州晚报)
现在,呈现在南宁街头的鬼火少年和电摩文化,绝大可能地走向了注定的消亡。
它就像是一个盆景,一个相对独立生态系统的实验,展示了一个街头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土壤之中,但不知道它会长出一颗什么样的植物。
长久以来,关于"鬼火少年"的讨论不外乎是两种声音。
第一种是,诸如"精神小伙"、"扰民"甚至是"迟早撞死"、"快进监狱"一类带着敌意和戾气的批判;第二种,则是能在中流的媒体报道中反复出现,常常以纪录片和特稿的形式,里面一个年纪不小的记者会对着画面反复强调诸如"留守少年"、"贫富差距","教育不平等"之类的词语。
就像是讲地下赛车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人们知道这会带来危险和死亡,但是本质上我们对刺激的渴望,像是我们对天性的神往。同样是在一部讲述地下赛车的电影中,有过这么一句台词"这儿就是一个虚拟世界,你白天可能是个律师或者医生,但是晚上这儿能让所有人都平等的,只有速度。"
当然鬼火少年还没有资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地下赛车相提并论,但它就是一个奇葩一样的盆栽,在这个故事里它成长着、也夭折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说法目前为止仍然是少数,只是在逐渐地增加
自从火车头出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舆论一些细微的变化。除了上述的两种声音,一种新的声音出现了。"电摩文化"的标签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和火车头有关的视频中,它和其他南宁地方上各种各样的的电摩风格杂糅在一起,成了南宁这个电动车之都文化的一部分,被来自各地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
另一部分,就是火车头的视频下面,可以看到许多外来者,几乎是下意识地将它和暴走族、西海岸进行对比。
这不是鬼火少年第一次出圈。但是之前不论是去年的通达路,还是2021年的鸡村新路,或者是2020年的扫把岭,还有2018年的华南城。之前我们从未看到类似的舆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审美体系在不断产生进化。
我们终究是一个感性的动物,美国的飞车党和日本暴走族不让我们讨厌。除了因为这两拨人远在天边撞不到我之外,路人的观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初代的鬼火少年可能看起来确实是通常我们认知中的"精神小伙"的形象,奇装异服、锅盖头、瘦、豆豆鞋。但是在火车头的末期,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到审美再往更加主流的方向靠近。
*图片来源b站@狐臭味的拿铁
在火车头高层中,一个名为道长的男生算是最典型的一位。在专项整治活动中,他的"落网"也一度在圈子里被当作火车头落幕的标志。但从外表来看,他略带婴儿肥的清秀长相,和所有中学生对"常服"的恶劣品味一样——总是上下两件都是深色的运动服。唯独不同的,当他出去玩车的时候,会身披一件黄色的道袍。这成了他的个人特色,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模仿的风潮。
在鬼火的语境里面,对于其他的技术党来说,可能道长成名的路子不怎么有工匠精神。
问起别的鬼火少年,"道长最有名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穿着道袍,最有特色,奥对,还有因为他被抓了。"说完他扭着身子,冲着旁边问了一句,"你说他们抓的为什么不是我。"
"那么道长是技术是你们里面最好的吗?"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倒是旁边的稍微年长些的人帮了一句腔。"你说技术肯定谁也不服气了。"
这段对话发生在一个特Underground的改装店里,周围环境属于那种抛尸胜地的感觉。南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电摩之都,足够的沉淀,让整个电摩文化在这里变成体系系统化,是鬼火少年变得更加让人接受的重要原因。
他们把练习翘头分成五个阶段分别叫做"科目一"到"科目五"。
科目一叫做蛤蟆翘,两腿跨在座位上,保持平衡,这个动作腿可以轻微接触地面保持平衡,这个时候甚至可以找个搭档坐在后座辅助保持平衡。科目二是,跪翘,膝盖跪在座位上。科目三单手翘、科目四单手翘旋转,需要把腿放到一边然后依次转动到左右两侧。科目五,则是要让车子成90度,尾架和地面接触,如果可以产生火花,那么毫无疑问,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踏上了火车头的顶点。
不过车子一定要一辆rzs三阳鬼一。这辆原产于台湾三阳机车的踏板摩托变成今天南宁鬼火少年们最向往的座驾。打开"快手搜索",南宁有上百家改车行在打着广告,不外乎是两种形式。一种找一同龄女生画着浓重的粉底和眼妆坐在车子上面,用最低的性价比实现了"香车美女"的效果,点进去是一个年纪稍大的老表给你讲,自己开着鬼一"载黑麻麻回家"的故事。第二种则更加的技术流,密密麻麻的参数,三大件,电池电机框架,写的透明而且清楚。
南宁遍地是改装店,遍地是电动车厂。也许你不知道自己的电机是由哪个深山老林的厂子里面运出来,由哪个老师傅手工拼接到电焊的框架上的,但是性能什么的,咱都门儿清。
精心地根据自己的手感和情况设计改装方案是地下赛车的精髓。虽然在鬼一下面你看不到系统的改装和设计的方案,但是已经偶尔能看见底下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着,“我的避震架必须要换了。”
但是不论魔改到什么程度,鬼一的壳子永远是最重要的,那是身份的象征,是鬼火少年的信仰。
让人不解的是,我曾经以为鬼一的流行,是因为专门修改和设计过的"翘头车"。但是问了很多鬼火少年。
"为什么要用鬼一翘头,是因为性能问题吗?是因为头轻吗?"
"就是帅哦。"
在这个回答上所有人几乎出奇地一致。除此之外得不到更多有意义的解答,
假如试图把鬼火的文化和暴走族甚至是西海岸文化相提并论并论,当我们真正地去剖析他们对于"帅"的定义的时候几乎无能为力。
日本暴走族底子是美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速攻服、飞机头都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个时代影子。西海岸歌手们直接继承了Disco普及、平权运动的美学遗产,他们早年大多西海岸歌手的制作人就是在嬉皮运动中玩腻了的那批音乐家。更早的美式机车文化里的飞行夹克,能看到一战二战军队里的穿衣打扮的哲学。
我把鬼一这辆车子,给我喜欢机车文化的朋友看。
他的评价是“好像收到了那些二十世纪初,国产机甲动画中里的东西。”
三阳机车固然是个老牌的机车品牌,但是鬼一这个外壳脱离三阳的工艺,在三阳其他的海量的优秀设计中被那些孩子选择出来,一定还是有着独一无二的原因的。
在他们童年的时候恰好碰上2006年电视台禁止播放进口动画。他们的童年几乎伴随着因政策而飞快地成长的那些动画片一起长大。
这里我想再提一下那句已经被我抛弃的概念:留守儿童。他们小学放学回到家,奶奶说,让他自己看电视,打开电视,里面都是国产造型浮夸的机器人。这样的场景变得格外具体。
有着相同的质感。甚至有着一样的行事逻辑,“当外界和我竞争的时候,我就彻底地呆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好了。”
当然在这故事里,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意象、一种巧合,而不是一种因果。
*图片来源新京报
这种断代和割裂以各样的角度存在着。
在摩托车圈子里面一直存在这一个说法。
“鬼火少年的泛滥很大程度上因为禁摩令,曾经随处可见的骑手在某个十年突然断崖式地消失了。于是后来的鬼火少年骑上了电摩,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传承。“
当然这带着摩托佬的自我吹捧,只是一种说法。不过把鬼火少年的这些特点放置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气质格外的突出。
*图片来源:南国早报
在我的观察中,留守儿童并不是鬼火少年群体里面绝对的大多数。能冲着记者滔滔不绝“我就是想有点存在感的。”更不是大多数。
他们的大多数很木讷,你一旦向他们提问,他们会很害羞。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似乎很难准确地回答问题。他们会扭一扭,更多的时候用语气强烈地语气助词来代替你的问题。
或者是用某种范式的标准的像是有一个巨大提词器的从网上抄来的回答。
你问他们为什么玩他们会说,“为了帅啊~”你问他们危险么,他们会说“鬼火一响爹妈白养。”
如果在网上聊天,他们的回答总是会用最简短的词语。大多是“好的”、“行”。甚至“不方便”、“没时间”就是比较长的句子了。
其中不是留守少年的人们,和家人的沟通大多也有些问题。
“家里面的人怎么管都管不了,后来也就干脆不说了,只是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他就一句话不说,然后出去躲一两个小时。”
“最后只是和狐朋狗友整夜整夜地不回来。”
这种闭塞已经在一年又一年地积累中变得覆水难收。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陌生的年长者走进他们的世界,然后一个深呼吸,问他说“能不能跟我真诚地分享一下你的爱好。”他们只会抬起眼睛,看看对方,脑海里闪过了一百万中不被理解和接受反馈,然后一言不发地扭头走开。
当我们看到鬼火少年的文化产生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成为品牌、成为联赛、成为审美风格。甚至当这一切发生,它们社会层面上的不良影响也会变小。
“真的,这几年的中国能有个这么纯粹的街头文化不容易。”这是我选题会上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只是或许阻止这一切的,不是政策也不是警察。而是那股子不善表达。
好的童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作为曾经长期驻扎在中东的战地记者,周轶君如今探究的最重要议题是——教育。
现代教育制度诞生是普鲁士人于18世纪的发明,「学科」的概念也自此诞生。思想与知识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单元,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但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这个问题令周轶君困惑,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周轶君开始思考教育的边界与本质:对于孩子而言,教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什么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试图寻找答案的她,本能的反应是向世界求教,在不同国家寻找教育的最优解。最终,她走访了五个国家,完成了教育旅行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拍摄,这是一个母亲的私心,也是一个母亲为了解答教育困惑而做出的个体努力。
不同国家的教育也的确令她及中国的观众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芬兰,三年级的孩子不用经历任何考试,没有科目类别的限制,在课堂里学习「时间,年龄和我」,孩子们也在森林里上课,学习分辨颜色和气味,为一棵树取名大海、或风与浪,「没有正确答案」;在日本,一家幼儿园的草地被故意设计成不平整的样子,校长会悄悄耕种孩子们每天奔跑的这片土地,有时从地里长出花朵,让他们产生好奇;在以色列的著名教育家德隆的家里,孩子们8岁开始就自己管理自己的作息,「她要学习什么对她是好的或者坏的」;印度的一位工程师阿尔温德·库布塔是「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他用一根吸管吹出笛子的七个音符,用一张报纸能折出四种印度人常戴的帽子,孩子们获得乐趣可以是「免费的」;而在以精英教育著称的英国,贵族学校中,最重要的课程是体育和道德。
记录下这些,周轶君并不是为了批判,也没有试图改变制度的野心,她只是希望通过自己作为个体的努力,给更多的在应试教育中被规训的中国观众启发——教育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发现自我。
在豆瓣,中国观众给《他乡的童年》打出了9分的高分,在视频平台上线后,获赞最多的那则短评中,一位年轻人写道:「这类纪录片最大的功德是,告诉高墙之下的人们,教育还可能有哪些形式。」
关于他乡的童年,以及教育到底是什么,以下是周轶君的讲述——
文|涂雨清
编辑|金石
自然与生活感
我们拍摄的第一站是芬兰。芬兰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特别高,所以,对于那里的孩子来说,认识这样的环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但这堂课在芬兰不是固定地说这个叫自然课,而是他们可以在森林里上任何课,可以上数学课,也可以上文学,什么都可以。
在森林里上课,老师会给孩子们发一张色卡,让他们去森林中寻找色卡上的颜色。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森林中寻找不同的气味,形容这些气味,有一个女孩就去尝了树皮的味道,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给每一棵树取名字,没有正确答案——在芬兰的教育中,培养孩子和自然的关系,特别重要。
这一点,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东京藤幼儿园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骑着一匹叫做小春的小马在幼儿园里兜风,当作一份生日礼物。小春就生活在幼儿园的庭院里,孩子们有时候会带一些树叶和草过来喂她。园长说,如果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些动物的话,能够让他们有更强的生活感。
我问一个日本教育专家,幼儿园里可以养马在日本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说还真不是,如果在东京,土地很少的情况下可能养动物比较少,但是稍微往远一点,只要学校有条件,养大型动物的幼儿园很多,他们认为让孩子接触大型动物是很重要的。
藤幼儿园的门口和办公室前还会放着类似洋葱、昆虫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蔬菜是孩子们自己种的。园长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看到,摸到,然后去感觉,去想,去问,慢慢去体会,甚至是拿起来咬一下,这都是他们体验的过程。他当时说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小的时候要多接触大自然,如果20岁看到洋葱才惊讶的话,就不好了。」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接触自然,这家幼儿园的草坪也是不平整的,看上去像是没有人打理,其实园长会在上面耕作,每年两到三次,会播种。草坪里会长出不止一种植物,有时还会长出花朵。他们觉得这些不同的植物就应该在那里生长,给孩子带来不方便更好。面对不方便,孩子们会开始思考,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如果草地是平的,孩子们不需要操心,就不会思考任何事情。在这所幼儿园里,没有把完美作为它的设计理念,真实和自然才是。
藤幼儿园的小马——小春和小骏图源《他乡的童年》
这一点令我感触很深,教育其实是生活的全部,所有的事情都是教育,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对外界的体验很重要,这个东西最后也会影响你的心理。
在芬兰一所高中的森林课上,我捡到地上的两个松果,当地老师告诉我,怎么从中看出大自然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她问我,你能看出来是什么动物吃的吗?我说不知道,眼睛怎么能看得出来?他说肥一点的、吃了一半的是松鼠吃的。瘦一点的、吃得精光的松果是老鼠吃的,因为老鼠够不到那么高的松果,它们一定是等着松鼠吃剩的松果,掉到地上再吃一遍。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师的眼睛能看到我看不见的东西。
于是,我把这两个松果带回家给我的孩子们看。松果很直观,我的孩子还小,如果我给他们讲故事,讲道理,也不一定有一颗松果那么容易打动他们,我也希望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发现一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在森林里上课的芬兰孩子,正在品尝树皮的味道图源《他乡的童年》
竞争与成功
芬兰这一集拍完之后,给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我觉得我整个人,不光是对教育方面,而是重新认知了一个社会、认知了很多新的观念。这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信心接着去拍其他国家。
在很多国家,社会中好的资源大多集中在头部,越是各种状况都比较好的人,越能得到更好的资源,但在芬兰,资源集中在底部,你越差,我越给你投入,我越教你,越拉你,投放的资源越多。
芬兰的整个社会都不鼓励竞争。小学三、四年级没有任何考试,他们希望能避免任何形式的竞争。学校唯一评估的,不是他们在学科中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搭档学习以小组为单位如何学习,在面对任务时的责任感。
积极教育对全芬兰都很重要,它意味着,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又不擅长艺术,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可能是为人公正,有创造力,有雄心,擅长团队合作或者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同情心。
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个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
芬兰孩子眼中的「成功」图源《他乡的童年》
在赫尔辛基,我问一个9岁的小男孩,在芬兰,什么是成功?他的回答是,这里没有成功,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有点钱,你已经算是成功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没有人是最好的,都是平等的。
在芬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但在学校里,老师没有职称,没有考评,每5年有一次加薪,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工作。而作为孩子,长大后你可以去大学,可以去职业学校边学边工作,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我们也采访了「愤怒的小鸟」的创始人,他告诉我们,在芬兰,最好的学校就是离你家最近的那一所。所以,对于芬兰的家长来说,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去上大学,你不会觉得是世界末日。
以色列人非常注重教育,这和他们的民族历史有关。在他的历史当中,他的土地随时可以被剥夺,这个国家也随时会没有,但是人们带不走你的脑子,你的头脑始终都能跟着你走,你到哪儿都要快速地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迅速地给自己找出一个立足之地。
「创新」是以色列的教育中的一大特色,但同时,学习失败也是他们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前不久,以色列民间有三个年轻人自发花钱研究登月,最后失败了,但他们瞬间成为了以色列的英雄,出现在以色列的媒体上。
以色列不怕失败的精神体现在教育的许多方面,比如说经常会出现在以色列学校的教育小丑。他们戴着红鼻子,来到学校里,有时捉弄课间休息的孩子,有时堂而皇之走进教室里,打破沉闷的气氛。
教育小丑就是一直告诉孩子们,犯了错误不要紧,没做好作业,考试考得不好不要紧,还有一些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腋臭、汗味等等,他们会变得不自信,怕别人闻到味道什么的,这些教育小丑也会鼓励孩子说没事啊,所有孩子们的害怕情绪,不敢尝试的问题,教育小丑都会想办法去解决。我记得小丑当时就说了,想让孩子们想起上学这个事情就觉得很开心。
教育小丑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图源《他乡的童年》
特拉维夫大学的管理学院主任乌迪阿哈罗尼还告诉我,在以色列,如果你失败并开始第二次创业,你筹集资金的时候,投资人会给你更多,因为你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会认为你拥有了更多的经验、你很勇敢。
我知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舍弃竞争是很难想象的。但或许我们可以拓宽一些对成功的定义,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清华北大,好的职业,高的收入,孩子一旦达不到就会有强烈的挫败感,身边的人也会责怪他们,生活会因此变得很难,但如果我们的成功变得多元,生活就会有趣很多。
但这个改变并不是讲几句道理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点一点的训练。比如我以前会跟我女儿说,你不要跟人竞争,没有意义或者怎么样这种,一堆大道理说完,她会跟我说,妈妈,可是我真的想赢。
她的好胜心很强,我说,那我跟你说两个事情,首先你要赢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要真的不断练习,不断地去做这些事,你才能赢;第二,你要是没有赢,你失败了,你得要接受它,这个心理准备你有没有。比如说跟她下飞行棋,她一开始的时候输了就哭啊,就闹啊,要偷步啊,要这样那样,我不会让她的,我不让她,我就让她输。慢慢的,她认识了输这件事,就会觉得输也就输了,但她仍然喜欢下棋。我现在也会更多地是让她认识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输。
芬兰学校的墙上贴着「正直」「爱」「善良」「创造力」等词汇的卡片图源《他乡的童年》
全人教育
很多人会说,纪录片里面展现的都是其他国家的教育里好的一面,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教育也面临他们的难题。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聘用当地的摄影团队。其中一位日本的录音师说,大家总是带着一点点玫瑰色去看待日本的集体精神,但他想起来这事就觉得挺厌恶,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去上学都得是先从家里走到某一个集合点,然后大家集合起来一起走去学校。看起来似乎很整齐,就像是小河汇聚成江流一样,但是他那时候就觉得,凭什么上个学都要相互等来等去,他觉得很烦。
日本教育里有很多的细节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做事严谨,让他们去学会在意和照顾他人的心情和感受,让他们从小就懂得,不要轻易给别人添麻烦。这种集体精神和完美主义使得很多日本人过于压抑自我,因此日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感泪疗法师。在日本,很多人不会在公共场合表露悲伤,大家一直把「哭」看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这会给他人造成负担,令人不适。而感泪治疗师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在他的课堂哭出来。
我也去上了一堂眼泪课,是在一间大学的教室。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段感人的视频,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个视频受到触动,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借着这段视频哭出来了。之后我们坐成一个圈,老师会问在这些场景中,你看到哪一幕的时候很感动,想到了自己的什么事情,于是每一个人都开始分享一些他们生命当中悲伤的事情,和让她们觉得情感比较压抑的事情。
其中有个男孩子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幼儿园在参加亲人葬礼的时候,家人告诉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不能在现场哭出来。我觉得太恐怖了。当时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学者也在现场做调研,她是一个西班牙人,跟我就分享了她的很多体验跟经历,她说在日本职场里面,女职员如果在工作岗位上被骂了,她一定是要冲去厕所,关起门来哭,她不能在她的公司里面掉眼泪,不然的话会被认为她非常的软弱,她不适合这份工作。她觉得这个事情挺可怕的,所以对眼泪的疗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更多地推广。
我之所以会把这堂课记录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表达,真正的教育不仅仅在课堂里面,所谓学习课本知识的教育,好的教育一定是全人教育,就是关于整个人的塑造。眼泪老师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的年轻人去塑造他们的性格,而且是针对了他们比较普遍的性格特征,这是非常重要的育人的教育。
眼泪课堂上老师除了会播放相关影片,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分享故事图源《他乡的童年》
贵族学校的精英教育是英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但这种教育并不只教给你好的礼仪和谈吐,这些都是装饰性的东西,在英国的教育中,体育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体育课程非常多,不同的学校一定会有不同的特长项目,体育比赛、体育设施也非常多。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英国的大街小巷,其实他们的公园设施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多人说英国学生有第二层皮肤嘛,他们冬天都不怕冷,这就特别英国的一件事儿,这里暖气也很差,但他们就是,穿得特别少,他们觉得人就是要有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
体育课在英国也并不只是为了提高精神力。以马术为例,片子中,中国女孩Sarah专门去英国学习马术,在那里,她才认识到个人并不重要,你和马的结合很重要。我们还拍摄了华天,他也说在中国大家恨不得都是私教,一对一的教学来学马术。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一对一,他都是上那些几个孩子,十几个孩子在一起的班,那么这群孩子之间的友谊也很重要。
骑手和马随着音乐踩出不同的舞步图源《他乡的童年》
去英国拍摄的时候,我们采访了一个华人,李爽,她在英国很多年,孩子也在英国上学,自己也研究英国教育,我问她你觉得英国教育中最好的部分是什么?她说,除了体育,是道德,我当时吓了一跳,为什么?后来发现道德其实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一种良知。
在英国的精英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去理解贵族好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一些个人能为社会做什么,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包括我采访的一位贵族,他就说作为一个有头衔的贵族,你要意识到你有多么幸运,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的精英教育有时候是那种,你眼睛只看你最终的目标,周围的东西你都不看,我一门心思要追求卓越,做那个最好的我。但英国的精英教育则是说,你要不断地看你和周围的人,周围的动物,周围的世界发生了这种关联。
这就是全人教育,不是只传授知识点,也不止停留在课堂上,更不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塑造一个完整的人。
个体的努力
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也不是想马上能改变大环境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通过这部片子让更多人有所思考,关于教育,个体能做怎样的努力和改变。
关于这一点,印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度的公立教育体系并不好,政府投入远远赶不上中国,但是当中有很多令人敬佩的个体的努力。
比如做《月经百科全书》的那对夫妇,就是非常典型的个体的努力。印度曾经有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短片,就是讲月经的,印度女孩会因为月经的事情休学,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这对夫妇做了这套书,帮助更多的印度女孩去认识月经,在社会中普及这件事。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们做了很多的国际版本,不仅是印度,在中国,在俄罗斯,在很多国家,这本书的需求特别大,节目播出后,我在微博上也收到很多私信,问我怎么找这本书的中文版——这不仅是个体的努力,也是一种生活教育,而不是课本教育。
《月经百科全书》成为印度女孩的月经启蒙图源《他乡的童年》
还有印度「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阿尔温德·库布塔,用最简单、成本最小的方法把很多「废物」变成了玩具,以此告诉孩子们,没有什么快乐是大过于双手创造的快乐。我回来以后,教孩子用库布塔的方法边吹边剪一根吸管,可以吹出do re mi fa so七个音阶,孩子们试起来特别快,当我女儿发现真的能吹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能看到她眼睛里的光,真的特别特别神奇。
「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阿尔温德·库布塔图源《他乡的童年》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的,但如果教育的功能有时候甚至是把一个人教成无趣的人,这是很可怕。
在芬兰拍摄的间隙,我跟芬兰中学的华裔老师葛云讨论,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她说,在芬兰,更多的是educating(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思考,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而我们过去传统的做法,侧重的可能是training(训练),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工匠,让他可以答满分的卷子。
芬兰的「现象教育」课很有名,这是一门基于生活真实话题,同时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课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帮助你理解生活的课。我去了首都赫尔辛基的syk小学,听了两堂现象教育课,这节课的主题是「时间、年龄和我」。老师在这门课里会结合数学、艺术、生物、芬兰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科,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讲解。这堂课也不一定要在教室里,老师还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老年人康复服务中心,孩子们和老人们坐在一起,相互认识,并且画出对方的样子。让他们在老人的身上理解年龄和时间。
我不太会画画,就用铅笔描出了我眼前一个9岁男孩的脸部轮廓。坐在同桌的一位老人画得很好,我问她是不是学过画画,她说没学过,只是从小就喜欢,而这是我第一次画一张肖像画。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带女儿去香港的一个画室,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场地,你自己随便画,没有人教你的。我发现她就是不加思索地开始画一个东西,好像画了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而我是画了一会儿,觉得不好不好,涂掉涂掉,然后再画一个什么,再涂掉再涂掉。后来画室的人跟我说,你知道你跟你女儿的区别在于什么吗?她不害怕画画,你害怕画画。
我们经常会用结果的好或不好去评价一件事,很多兴趣也会因此被打压。我小时候一唱歌就被他们打压,说我唱歌不行,跟背书似的,记得有一回,舅舅甚至说过「我唱歌要用打气筒」。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人面前唱歌,也从来不去卡拉OK。
但在芬兰这堂课上,我忽然明白过来,你画得好不好,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可以一直去画,你又不想做一个画家,画画对你来说是有乐趣的。当你的人生中有一项爱好,你永远不会孤单,不会绝望,这真的很宝贵,现在我开始明白,学习是为了生活。
第一次画肖像画的周轶君被深深触动图源《他乡的童年》
芬兰教育里训练的东西不是没有,有些东西还是要记,但他们更多的强调一种知识获取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学习的目的,他们自己讲是为了生活,就我们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一遭,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幸福,这其实是一种终极追问——这也是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我觉得最感人的事情,你对于知识的态度,忽然间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你是真心的认为我想理解它,我想认知它,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享受,我很开心。
我在圆桌派讲过一个事情,我说90到千禧是me generation,他们经常自拍,秀自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代,但是另外一点,这个me是很像的,无论是穿着喜好,还是在社交网络上形成的一个潮流,那个「我」也不是真正的我。我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蛮多例子,就是年轻人会来找我谈,说他们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觉得现在的工作他不满意,但要怎么做呢,他也不知道。那我说好啊,如果你想我帮助你,那请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哪怕你喜欢什么?他们很难回答他们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这件事情。
我不敢肯定这跟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一定相关。在我们的教育中,一切都是社会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真实自我,你想要什么,所以这种教育对人的影响是会非常深远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用双手去获取知识,并且这个知识是内心想要的。
《他乡的童年》最后一集,我回到了国内,和爱好书法的作家张大春讨论育儿,我问张大春,教孩子写字是不是他和孩子们情感沟通的方式?但事实上孩子们和张大春一起练习毛笔字的时间极少,十几年来没有超过5个小时。他说,「我从来没有试着把他们教养成一个跟我有相同志趣,或者是有相同文化负担的人,他们的自我就像那个猫,想要冲出纱门之外。」
图源《他乡的童年》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 上一篇:英国大学破解狐臭(英国大学视频)
- 下一篇:狐臭喷雾照片真实(狐臭喷雾的原理是什么)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