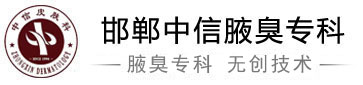小说:他重生宋代成武大郎,遇到王婆给西门庆做说客,他瞬间怒了
侍女冷哼:“看你这五短身材,一身麻布,最多也就只是个卖炊饼的,你能有什么本事?”
“我这卖炊饼的,别本事没有,却偏偏能治着狐臭。”
这吴月眉乃是千金小姐出身,嫁给西门庆之后,因为身上着浓烈的狐臭,使得夫妻两个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圆房。
她虽然把自己装扮得跟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般,但实际上却还是一个未经人事的黄花大闺女。
夫妻生活不和谐,可愁煞了这美人。
听武植这么一说,吴月眉连忙起身,她对着武植盈盈一礼:“敢问先生,真的有治疗的法子吗?”
“有当然是有了,只不过怕西门大娘子不肯相信我啊。”
“只要先生真的有法子,无论多少钱,奴家都愿意出!”
武植嘴角微微上翘,小时候在少林寺学武,经常会练的头破血流,恰好少林寺一个偏院有位扫地僧人。
这个僧人懂得医术,武植和他相处久了,也略懂一些皮毛,这其中就有医治狐臭的办法。
“方法当然是有的,只不过我刚刚来阳谷县。很多家伙什都没带过来,需要重新置办,大娘子只需给我十两银子,明日就能够把物件奉上。”
吴月眉非常迫切地想要得到治疗狐臭的办法,于是二话不说,就掏出了十两银子递给武植。
武植笑了笑:“大娘子就在家中安心等候,在下很快就会将好物件奉上。”
拿着十两银子,带着潘金莲转身潇洒离去。
回去的路上,潘金莲用一种很奇特的眼神看着武植。
她欲言又止的样子,甚是可爱,看得武植不禁食指大动。武植笑呵呵地对着潘金莲:“娘子有什么话尽管问。”
潘金莲嚅了嚅性感的唇瓣,小声问道:“官人,你真的有办法治疗西门大娘子吗?”
“娘子只管在旁边看便是,你男人我,会的东西可多着呢。”
看着武植那自信满满的笑容,潘金莲恍惚间有些愣神。如果她不是一直和武植在一起,恐怕会以为眼前人,根本就不是那懦弱无能的武大郎。
也不知怎的,有那么一瞬间,潘金莲突然发现,自己的男人长得还挺好看。
“娘子愣着干嘛,走吧,走吧,咱们回家。”
武植牵着潘金莲的手儿,穿过街道回了自家门。
潘金莲手里抱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裙,就像是抱着一个宝贝,嘴角勾勒起一抹浅浅的笑意,眼眸之中还隐隐有着一份幸福之色。
“官人,我上楼把衣服收好。下来和你一起揉面。”
一进屋,潘金莲就急匆匆的要上楼,武植则是对着她笑道:“这种粗活怎么能给你干呢?赚钱这种小事情就交给我吧。”
说完,武植撸起袖子就开始干活。
哪怕是在现代,武植也被许多企业家誉为商业奇才,他在赚钱方面有着极强的嗅觉,只要是他投资的行业,一定是大赚特赚!
武植要在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把葱油手抓饼吃腻之前,大量生产,然后把赚到的钱投到另外一个行业里去。
其实在看到西门庆老婆吴月眉的时候,武植就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靠什么赚钱了。
无论在什么朝代,女人的钱最好赚!
武植在揉面的时候,潘金莲还是换上了粗布衣服,撸起那光洁嫩白的手儿,站在武植身边一起揉面。
夫妻两人并排站着,虽然没说话,但空气当中总隐隐有一种很暧昧的味道。
潘金莲揉以前连眼角都不会斜武植一下,但现在总时不时地会朝着武植飘去一眼。
飘着飘着,不经意间两个人的手碰到了一起。
武植这个色胚哪里肯放过如此机会,当下抓住了潘金莲嫩嫩软软的手儿。
潘金莲微微挣扎了一下,但武植抓得牢,她的挣扎如一条小鱼儿,越是欢腾,给武植带来的感觉就越是强烈。
“娘子,你的手儿可真嫩。”武植没羞没臊地说。
潘金莲被武植说得羞了,那精致无瑕的脸蛋,红扑扑的,就像秋天的苹果,娇艳欲滴。
潘金莲赶忙转移注意力,发现武植准备了很多面粉,这些料放在平日里,十来天都不一定卖得光,当下不由地问:“官人,这么多饼,咱们卖的掉吗?”
武植正要说话,门外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金莲在家吗?”
潘金莲连忙说:“是干娘来了!”
只见王婆提着一个包袱走了进来,看到武植和潘金莲在揉面,一脸不屑:“我说大郎,不是干娘说你。这种粗活你自己干也就算了,怎么能让金莲也跟着?”
说着,王婆就把包袱递给潘金莲:“金莲,你赶紧去洗手,再把身上的这些灰尘都弹去,要是把这衣裳给弄脏了,你可担待不起。”
这王婆对潘金莲提出了很多要求,...
“哎。”
潘金莲乖乖地转身正要去洗手的时候,武植却是突然抓住她软软的手臂。
武植直直盯着王婆说:“这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
“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大户人家的衣裳,这里面装着的都是绫罗绸缎,平日里你连见都见不着。”
“既然这样,那就拿到别处去!”武植个子不高,但是所说出来的话却是落地有声,振聋发聩!
以前武大郎就是一个懦弱的孬种,跟别人连一句大声都不敢。王婆一开始还被武植给唬住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对着武植呵斥。
“武大,可别不识好歹!你可知道这些衣服值多少钱吗?”
武植冷冷一笑:“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钱我们自己会赚,就不劳您费心了!”
“另外,今后不要来我家里,也不要拿这些乱七八糟的衣服糟践我娘子!从现在开始,我娘子不会给别人家做任何的女红!”
“你、你……”王婆被武植呛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好啊!卖了几个破饼,尾巴就上天了是不是?你们等着,老娘只要一句话,就让你这破饼一个都卖不出去!到时候可别跪在门槛前求老娘!”
王婆怒气冲冲的离开了武植家,她刚刚进茶馆,西门庆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迎上来。
“干娘!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王婆冷哼一声,将包袱丢在桌子上:“这武大郎看样子是起了疑心啦,死活不让潘金莲跟别人接触。”
很快,王婆那张皱巴巴的老脸上就浮现出一抹阴险的笑:“他一个臭卖饼的,敢跟老娘斗!接下来有他苦果子吃的!”
西门庆问:“干娘打算怎么做?”
百万字长篇《山村小伙考进了县水利局》第66章 肯吃亏不是痴人
国庆节也是闻景精挑细选的结婚的日子,桂卿和凤贤两人作为他最好的朋友早早地就跑去帮忙了,因此桂卿并没捞着参加在同一天举办的甘霖庙竣工典礼,尽管他也很喜欢看热闹。
到了晚上的场,因为有人替换了端盘子的角色,桂卿才得以和凤贤坐到一起喝酒聊天。
他和他,都是一天吃了两场。
“端盘子干活的时候想到你了,”凤贤嘿嘿地笑道,到死都改不了随时随地犯贱的老毛病,“等晚上干真事的时候就不带你玩了。”
“猥琐男一枚!”桂卿直言道。
“龌龊男一个!”凤贤顺口回击着,然后突然又想起了一件别的事情,于是继续言道,“不过,我再猥琐也不如恁办公室的那个狗家伙猥琐,他才是天生的纯种贱男呢,而且血脉优良,质地坚硬!”
“哦,是不是上回让人伤自尊了?”桂卿一边幸灾乐祸地冷笑着,一边用极其亲昵的口吻嘲弄道,“伤自尊了你就直说嘛,你不说谁知道你的委屈呀?”
“我这不是已经说了吗?”凤贤道。
“不过这孩子确实不惹人喜,”桂卿议论道,“居然能当着你的面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来,我看也显得忒无耻了。”
“你看看我,”他接着嘻嘡道,“我就不是他那样的人,我心里明明也是那样想的,但我就是不直接说出来。”
“你这家伙多闷骚了,心眼子多多了!”凤贤乐呵呵地鄙夷道,脸上依然像刚才那样笑着的,“我明白,你和他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就他那个假聪明和真愚蠢的熊样,我睡着了都比他能,你信吗?”
“那你当时怎么不堵他的?”桂卿发问。
“噢,狗咬我一口,我能当场再咬狗一口吗?”凤贤难为着脸冷笑道,想来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只不过是在伙计面前硬装大度罢了,“那我和狗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你别看我当时嘻嘻哈哈的,”他又道,“净顺着他的话来,表面上看着对他的侮辱根本就不当回事,其实在我心里我早把这孩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对付这种不知天高地厚又没教养又不懂反省的人,就得先顺着他的思路来,不能当场和他抬杠和辩论,更不能呛着他,刺激他,只能让他继续在无知且无耻的道路上不知不觉地走下去,直到有一天他被硬茬子给好好地收拾一顿为止,懂吗?”
“洒家焉能不懂?”桂卿跩道。
“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的,你就等着瞧吧。”凤贤道。
“你这家伙可真够阴的啊,还好意思说我心眼子多。”桂卿点头笑道,眼神里全是喜悦和爽快的意思,同时他还想起了彭云启调戏梁光洲的妹妹梁静的事,愈发感觉彭云启这厮不可理喻了。
“狗,果然是条不折不扣的狗啊。”他随口嘟囔道。
“过奖了,过奖了,”凤贤将喜人的嘴角悄然一歪,玩世不恭而又意味深长地笑道,“这叫因人施教嘛,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调,见什么动物学什么叫,凡事都不能太教条了,一切都得灵活运用才好。”
“有个事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家伙据说下一个月要结婚了。”桂卿由着闻景的婚礼忽然想到了彭云启马上就要结婚的事,所以就不由自主地在凤贤面前提起了这等腌臜事。
他说到这里不禁感觉心里有些堵得慌,就像刚刚吃下一只活蹦乱跳的灰褐色的癞青蛙,而那只癞青蛙还在他胃里一个劲地想往外跳一样。
彭云启结婚的对象竟然就是那天他和晓樱在湖东区欧情街见到的徐荣,这事确实太有戏剧性了,以至于搞得他在彭云启得意洋洋地宣布这个消息时候心中瞬间就凌乱不堪了。
他呆呆傻傻地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面对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而这结果在彭云启看起来居然还幸福得要命,骄傲得不叫招。
他大胆地推想,徐荣的心里应该也是十分高兴的吧,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果吧。
难道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结果,比这更好的结果吗?
他既然想不出来,也就不准备再想了。
“哎呦,他这等鸟人结婚关我屁事啊!”凤贤非常厌恶地脱口而出道,似乎一心想要把在桂卿胃里拼命蹦跶的那只癞青蛙给拽出来慢慢地把玩一番,然后再给送回去,“不过你就不一样了,明明恶心得要命,还得乖乖地去掏钱喝喜酒。”
“嘿嘿,谁叫你们是一个单位的呢,踩上狗屎甩不掉了吧?”他直接褒贬道,也不怕得罪桂卿。
“真是活该啊,你这家伙也有今天!”他又嘻嘡着骂道。
“一个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侮辱你的人,”桂卿决心好好地刺激一番凤贤,这个嘴上死硬死硬的怪才,“一个肆意侮辱完你而又毫无愧疚之色的人,现如今不费吹灰之力就春风得意地喜气洋洋地要娶东院某某部某人的侄女,县某某局一把手的妹妹了,你不觉得应该替人家感到高兴一下吗?”
“你的度量不会那么小,见不得这种好事吧?”他揶揄道。
“什么,这孩子真的这么牛吗?”听到桂卿的话凤贤终于肯认输了,他瞪起小眼来吃惊地问道,“我的个乖乖唻,不简单啊,不简单!”
“而且,人家还一把掏清,”桂卿顺流而下,又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凤贤的嚣张气焰,索性把好人做到底,“在新开发的世纪城小区,买了一套120平方的房子。”
“怎么样,听着很过瘾吧,心里不好受吧?”他褒贬道。
“我什么,别看这孩子本身的素质和人品不怎么样,说话办事什么的都让人烦不胜烦,不过他倒是有个好爹呀!”凤贤终于矜持不住了,立马卸掉伪装多时的坚硬铠甲,转而大声地感叹道,这或许才是他本来的真面目,“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同样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我爹怎么就混得不如人爹呢?”他够不着天捞不着地地感慨道。
“唉,真是老妈妈上厕所,不扶(服)不行啊!”他又叹道。
“这就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呗!”桂卿非常不屑地耻笑道,打算进一步挖掘彭云启身上的闪光点,好让凤贤彻底认清其本来的真面目,“有些事就算累死你,你都想不出来还能这么干。”
“前一阵子俺单位的会计去交电话费,结果发现姜局长屋里的电话费明显高出平常一大截子,就感到不大对劲。”
“于是会计就把个事反映给了俺办公室的那个蓝宗原主任。”
“蓝主任,你也认识的,他就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到邮电局把通话记录给调了出来,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啊?”凤贤仰着脸问,他就是绷不住。
“除了给一个手机号打得最多之外,”桂卿揭秘道,“剩下的全是国内长途,而且全都是姜局长不在单位的时间段里拨打的。”
“哦,那肯定是有人偷打的。”凤贤猜测道。
“对啊,叫你一炮打准了!”桂卿故意夸张地赞赏道,也是为了增加聊天的趣味性,“蓝主任为了搞清楚这个事,就悄悄地用姜局长屋里的电话拨打了那个手机号,结果是一个女的接听的,而且那个女的连脑子都没动,张嘴就说,你又用这个号给我打电话了,也不怕你们局长逮着你啊,要是逮着你可就麻烦了——”
“你说这事搞笑不搞笑?”他嘲笑道,“他和她事先前也不设个暗号什么的,真是聪明劲没用对地方。”
“那个女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徐荣吧?”凤贤推测道。
“嘿嘿,聪明绝顶!”桂卿不厚道地笑道,同时在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没找徐荣当老婆,她居然都不先核实一下对方是谁,就贸然在电话里那样说话,显得太没脑子了,将来肯定不能成大事,“偷打电话的人就是彭云启,那些国内长途都是他打给他大学同学的,”
“按理说,”他道,“这家伙家里也挺有钱的,犯不着去用局长的座机打电话啊,真是不可思议。”
“他怎么能捞着偷进局长的屋呢?”凤贤抢话道,这家伙的脑袋就是好用,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
“这个好办呀,”桂卿连忙解释道,心里觉得异常痛快,“有一回蓝主任安排他去姜局长屋打扫卫生,他抽空下楼去,到外头就把姜局长屋里的钥匙给配了一把。”
“而且他这个人特别精明,平时都把姜局长的行踪给摸透了,都是算准了姜局长不回来的时候才溜进去打的电话。”
“就他那个脑子,我实话给你说,几乎就是电脑,运行起来刷刷的,我从来都是自叹不如的。关于这一点,咱不服不行。”
“我的个乖乖唻,这得是什么猴脑子、什么熊胆量、什么下三滥的狗性格,才能干得出来这种一等一的龌龊事情啊?”凤贤大惊道,显然他也是头一回见识这种奇葩货色。
“我没说嘛,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桂卿嘲弄道。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凤贤巴巴地问道。
“蓝主任这个人心善呀,”桂卿接着道,同时很是佩服蓝宗原会做人,办事比较周全,“就没往外公开说这个事,而是直接找个理由把姜局长屋里的锁给换了,算是暗着给他点明了这个事,给这孩子多少留了点脸面,没直接毁掉他的名声。”
“真是个世间少有的人才!”凤贤直接骂道,然后又想起了国庆节之后参加一个培训班的事,于是张口便问,“哎,对了,这回在什么校举办的培训班,你捞着参加了吗?”
“捞着了,怎么没捞着呢?”桂卿略微自豪地答道,盲目得有些可笑,好像这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一样。
“不过这回我算是捡了个漏,”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脸上充满了亮闪闪的得意之色,“沾了人家姜局长的光。”
“当时蓝主任去找姜局长商量名额分配的事,人家姜局长直接就说了,桂卿跟着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小青年一直干得都不孬,这回给他一个名额吧。”
“这不,就是人家姜局长一句话的事,咱连一盒烟一瓶酒都没给人家送,人家就主动把参加培训的名额给了咱,你说够意思吧?”
“行啊,伙计,”凤贤高兴地说道,也是同喜同贺的意思,两眼都放着金光,“能参加培训就说明这个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
“另外,我给你说啊,这个事就和两个人相亲见面一样,也是看缘分的,这充分说明姜月照这个人和你还是很投缘的。”
“对,看来只能这么解释了,这也是机会赶得巧。”桂卿道。
“唉,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凤贤发神经一样感慨道,“是你的,终归还是你的,不是你的,硬抢也抢不来。”
“问题是,压根我也没想着去抢啊,”桂卿不失时机地叹道,很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还被彭云启这家伙无缘无故地刺激了一顿呢。”
“哦,他又放什么屁了?”凤贤瞪眼问道。
“他说凡是那些参加工作之后再纳新的,”桂卿原原本本地转述道,每说一遍火气就增加一层,“都是没什么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早在大学就完成这个操作了,再有本事的,人家高中就进行完了。”
“哎,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憋人的,这也有点忒揍瞎了吧?”凤贤忍不住再次高声骂道,算是替桂卿报仇了。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然后他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报社里一个和彭云启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家伙,于是就兴致勃勃地絮叨起来,大有一吐为快的架势,“我倒是想起了俺办公室的一个另类奇葩,我索性讲给你听听吧,咱一块乐呵乐呵。”
“这家伙是年后从新闻部调到我们专题部来的,”凤贤缓缓地讲道,看来后边的故事应该很长,也很有趣味,“当时社长给他谈话的时候还专门安排过他,让他跟着我这个老前辈好好地学学怎么有针对性地跑新闻,怎么独辟蹊径地选题,怎么结合青云实际写好稿子什么的。”
“结果这家伙来了之后,不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什么屁活都不知道干,而且不管对什么事还都喜欢评头论足和指指点点的,差点把我给气死。”
“你不理他就是了,干嘛生那个闲气啊。”桂卿劝道。
“就是啊,就凭恁哥我那像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怎么会和他这种无知之徒一般见识呢?”凤贤稍显激动地回道,然后又不由自主地谝起能来了,“我见他也是个不入路的熊货,干脆就采取冷处理的措施,把他彻底地挂起来,什么活也不让他干,一个字皮都不安排他写,就连跑腿的事也不让干,随便他玩,让他玩足玩够玩出毛病来。”
“他自己觉不着吗?”桂卿又问。
“嗤,他要是有那个觉悟,就不会一开始弄那个熊样了!”凤贤快意情仇地嘲讽道,总算是在伙计面前出了点小气,“其实他的心思我也看透了,他主要是怕如果他主动提起安排他工作的事,我就会没好歹地支使他,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所以他才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这是典型的小聪明,太过自以为是了。”
“他曾经当着我的面抱怨过,说新闻部的王主任,整天把他支使得和三孙子一样,他早就想揍王主任一顿了,要不是他心眼好、度量大、有涵养的话。”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和那个王主任是整翻一个啊。”桂卿道。
“那是啊,这就是不同的领导风格和领导艺术问题,”凤贤有些自鸣得意地说道,也不觉得这样会累,他就喜欢用这种方式说话,“只有无能而且自私的人,才靠着领导的身份和级别去硬压着别人干活呢,而像恁哥我这样的人则完全是靠实实在在的人格魅力和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实际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大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我和那些我心里看不起的人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他跩道。
“怎么当好头,主要还是性格问题。”桂卿轻轻地笑道,并没有理会凤贤的俏皮话,算是借机敲了对方一小闷棍。
“你的话自然是对得很,”凤贤先是愉快地肯定道,然后又开始絮叨起来,既然开了头,那么就得继续说下去,“你比如天天早上,俺屋里的卫生要么是我这个当主任的亲自打扫,要么是另外几个同事轮流着打扫,反正这个缺心眼子从来都是无动于衷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打扫卫生这一块。”
“有时候屋里来客人了,也是我或者别人亲自端茶倒水,让烟让座的,他就和个瞎子没什么两样。”
“至于那些像复印资料或者装订个材料之类的小活,要是别人都不在的话从来都是我亲自干,他就是站在一边闲着屁事都没有,也不知道过来搭把手。”
“总而言之,他就是这么一个连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起来的好人,你说是不是个另类奇葩?”
“他天天就那么闲着,自己不难受吗?”桂卿再问。
“可不是嘛,”凤贤非常无奈地笑道,说得自己都有些疲沓了,都懒得再絮叨下去了,“人家从来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就那么一直心安理得地闲着,一天到晚屁活不干,还整天木麻不觉的。”
“有时候他实在无聊了,就出去到大街上溜达着玩,连给我说一声都不说,都是抬腿就走,说出去就出去。”
“发展到后来,人家干脆整天整天地不来了,就是偶尔高兴了过来冒个泡,然后过不了一会又出去了,整个儿就和一匹没人管的野马一样,干什么都是随心所欲。”
“那,他这是上的什么鸟班啊?”桂卿听后感慨道,确实有些想不通,就像他想不通彭云启那些恶心人的行为一样,“还天天和真的一样,领着和你差不多的工资。”
“唉,我就当他是团空气吧,他爱咋的就咋的吧,他上天日龙咱也不问,咱闲得惹他打那个喷嚏啊?”凤贤竟然如此叹道,看来他也是实在没法了,因为人要不要脸,阎王也难管,更何况他又不是阎王,自然管不了人家了,“无非就是我和别人多干点活而已,反正干工作又累不死人,多干点活也没亏吃。”
“再说了,你也知道的,”他接着谝能道,“恁哥我闭着眼就把那些活给干了,根本就累不着我,呵呵。”
“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吗?”桂卿继续问下去。
“哼,他到我们专题部来的第一天,”凤贤继续抖搂着他那位好同事的瞎巴事,聊天的兴致重又高涨了,“就把有些话直接给我摆明了,他说他的工作能力一般,业务水平不高,也不是写稿子的材料,希望我平时多照顾照顾他,多体谅体谅他。”
“他那个小胜人蛋话我一听就是让我以后少给他安排活的意思,我当时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我并没直接说什么。”
“然后他接着就给我抱怨说,前几天新闻部的王主任给他安排了个活,他根本就没法干,王主任还不顾客观情况硬安排他干。”
“他说他当时都想拍着桌子骂王主任,心里没点熊数,这样的活也安排给我,你的脑袋难道被驴踢了吗?”
“噢,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仰着脸讲道,“才知道原来这家伙是这么个熊玩意啊,他这明摆着是打马摩喽牛,在猴子面前故意讲杀鸡的事啊。”
“那行,我知道了。”
“我心说,既然堂堂的王主任都用不起你,那我就更用不起你了,对不对?”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把他当祖奶奶一样给供起来,我就当他不存在了,随他怎么折腾去吧……”
“唉,各人有各人的造化嘛,”桂卿酸酸地叹道,也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他天生就那个熊样,你能怎么着人家啊?”
“说不定在家里,他爹都管不了他呢。”他冷笑道。
“这倒也是,”凤贤回应道,“可能性比较大。”
“哼,最后人家也不一定混得比你差。”桂卿又刺激道。
这种后来者居上和无能者或无耻者上位的事情多了,本来就没什么稀奇的,桂卿能说出这种话来也是很正常。
一般人都对一反常态的事情印象比较深刻,他自然也不例外。
“但愿,但愿,那样最好了。”凤贤不无讥讽地笑道,那意思就是就算那孩子将来侥幸当上皇上了,他照样从骨子里瞧不起那种人。
他说的当然是反话,透着一股子浓重的酸味。
“据说啊,当然都是地摊杂志上说的,”他又冒傻款道,好像天下就没有他不敢嘲笑的人和事情,“那些敢于向领导说不的人都不是一般人,人有的时候就是要敢于说不,敢于拒绝,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该有的尊严和地位。”
“仔细想来,本事越大的人,其实就是说不的能力越大的人,你既然没什么本事,当然只能对别人俯首称臣和唯唯诺诺了。”
他既然记住这句话了,那么无形当中就会模仿这句话来行动,把这句话奉为人生的坚定信条,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人的潜意识就是有这种奇怪的功能,任谁也不能例外,除非这个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明确的概念,那就另当别论了。
“唉,老黎,地摊杂志上的话也能信吗?”桂卿摇头晃脑地卖弄着劝慰道,他认为自己早就脱离了深受地摊杂志影响的低级阶段了,思维方式已经更上一层楼了,“再说了,从来都是能受苦乃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啊,你千万不要被几本毫无价值的地摊杂志给带沟里去了,那上面的话基本上都是胡扯的,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全是七拼八凑的烂玩意,根本经不起推敲,没有任何营养价值。”
“嗯,老弟言之有理,确实有一定(腚)的道理啊!”凤贤由衷地赞同桂卿的话,然后又连讽刺带挖苦地描述道,“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一个事来,也挺可笑的。”
“这伙计刚到俺办公室的第一天,就嫌电话机太旧了,门口的垃圾桶太烂了,办公桌上的玻璃太模糊了,给他配的办公桌抽屉都坏了等等,而且他还挺着脖子问我,怎么咱屋里连个洗脸盆子和肥皂都没有,你这个主任怎么当的?”
“把我直接给问晕了,好像他嘴里有着极其浓烈的顽固性狐臭一样。”
“他第一天就敢这样吗?”桂卿很是震惊地问道。
“当然了,你不知道,这小子立愣得很!”凤贤继续有滋有味地陈述道,心情似乎比刚才好多了,如同蹲厕所时已经把肠子里的大便拉个差不多了的劲头,“他在那里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半天,见屋里也没人理他,结果直接跑办公室主任那里要求更换这些东西。”
“好家伙,算他真有种!”桂卿发自肺腑地佩服道。
“办公室主任当然也不能任由他摆活啊,对吧?”凤贤像个说书的年轻老姑娘一样眉飞色舞地讲道,勾得桂卿是越听越想听,甚至有时候自己都想给续上一小段更为精彩的章节,“人家当时就没好气地告诉他,等东西彻底坏了,确实不能用了,再给他换。”
“结果这小子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回到俺屋里之后一脚就把那个看着不顺眼的垃圾桶给踢烂了,把电话线的水晶头拔出来直接给弄烂,然后第二天一早又去找办公室主任了,说这回东西彻底坏了,确实不能用了,必须得换新的。”
“我的乖乖唻,这孩子真是神人啊!”桂卿再次惊叹道。
“神不神的咱不知道,咱也管不着,反正人家就是这么玩的,”凤贤冷笑道,连自己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第二天,”他极为鄙夷地讲道,并没有因为沾到光而感到半分的高兴,“办公室主任还真给他换了个新的垃圾桶和电话机,还给了俺屋一个新洗脸盆和一个新毛巾。”
“那要这么说的话,”桂卿哈哈笑道,开心得不要不要的,简直都想和那个玩意一块办公了,这样的话没事就能看看戏了,“你们还真得感谢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为你们争取到了一定的利益,要不然你们肯定还得凑合下去。”
“你看看,有时候历史的伟大进程就是由这些讨厌的刺头来推动的,而像你这种人只是跟着沾光罢了。”
“我们也只能这样想了。”凤贤道,也只好笑了。
“那桌子换了吗?”桂卿又好奇地问。
“桌子是肯定不会给他换的,”凤贤严肃地回道,看来他在他口里的那个家伙面前只能永永远远地甘拜下风了,这辈子脱了鞋恐怕都赶不上人家矫健的步伐了,“因为他的那个桌子只是有一个抽屉不大好用了,其他的地方都还好好的,简直和新的一样。”
“不过,这也没难倒他这个货,”他又用较为佩服的神色讲道,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看不起的意思,“到底他还是换成了。”
“因为俺屋里当时有个小伙子被借调到东院某某部去了,平时根本就不过来上班,他直接把那个人的桌子和他自己的桌子给调换了。”
“哼,你说他到底有多大的胆子吧?”他道。
“哎,不对呀,按理说这些事他都得先给你这个当主任商量商量,然后再行动啊,也不能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对吧?”桂卿按捺不住心中不断涌起的好奇,于是便问,“另外,他怎么着也得先给那个人说一声再换桌子才行呀,他这样自作主张偷偷地换桌子,人家回来要是找他的麻烦怎么办?”
“兄弟,这只是你个人心中非常肤浅的想法,也是一般人的常规想法,但不是人家的真实想法,懂吗?”凤贤又一次冷笑道,笑桂卿还是没有太大的见识,“人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块,人家干这些事的时候根本就没鸟起咱这个当主任的,也没鸟起那个桌子的主人。”
“你可真是碰上人才了。”桂卿笑道。
“唉,这个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凤贤像个短臂猿一样仰天长叹一声,叹完之后才把臂膀重新收拢好。
小说:他卷入县衙党争之中,为保全自身他圆滑处世,却仍惹对方不满
在那尼姑装扮女子的引领下,乐和安和西门庆看到了那十名良家女子。
那十名女子站成一排,都是寻常百姓家的服色,虽然身材有高有矮,但是个个都还有几分姿色。很显然,这些女子都是经过了乐和安的“初选”才领到这里来的。
乐和安看着自己的“功绩”,得意的问西门庆道:“西门大官人,如何啊?是否满意啊?”
西门庆微微颔首道:“不错,还行。”说着西门庆又摸了十两金子给那尼姑装扮的女子,道:“姐姐,这些女子烦劳你先关照则个,让她们都洗个澡,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那要奴家教她们如何侍候大官人吗?”那女子一脸媚笑。
“别,千万不可教,大官人我要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感觉。”接着西门庆又对乐和安道:“乐相公”
乐和安道:“大官人,今后你我二人就以兄弟相称,如何啊?”
西门庆笑道:“求之不得啊!乐兄,那这些个事就拜托乐兄了。”
“只是.”乐和安故意顿了顿道:“只是那结识翟管家的事儿”
“请哥哥放心,这都是小事!”西门庆道:“小弟我一定给哥哥安排的妥妥当当。”西门庆忽然想到,他在东京救走了林娘子,如果因为进城去找翟谦而被高衙内再碰上,那可就麻烦了,看来原本去东京最好是能带上乐和安一同去,进城联系跑腿的事总得要个人来做不是。
离了庵堂,回到家里,在庞春梅的房中吃酒,吃了酒以后洗澡,洗完了澡,就在春梅的房里歇了。
后来的几日,西门庆忙碌得紧,家里,韩道国家、庵堂,三点一线的跑,又是请先生,又是购置衣衫,另外庵堂的十个良家女子中,竟有两个身上有狐臭,乐和安又在监牢里选了两个犯人的闺女来补充,换下了那两个有狐臭的。
这日晌午,西门庆刚从北门进城,只见有一群人正在围着瞧热闹。西门庆闲来无事,也挤进人群去瞧瞧。但见三个泼皮,将一个黑矮的汉子摁在地上拳打脚踢,另有一个泼皮在打一个半大孩子。地上横倒着一副担子,满地散落着炊饼和梨。
西门庆一看,挨打的不是别人,正是武大郎和郓哥。西门庆喝道:“都给老子住手!”
那几个泼皮一听有人喊住手,正要发作,回头一看,竟然是西门庆,其中一个泼皮忙变成了笑脸道:“哟,原来是西门大官人,您老去忙您的,咱们这是在教他一个外乡人如何做人呢!”
“放屁!”西门庆走上前去:“你们为何打这卖炊饼的啊?”
围观的众人一看西门庆出面了,都觉得这出戏越来越好看,围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那泼皮道:“大官人,您老也是场面上的人物,这规矩您老是知道的,他一个清河县来的,想在咱们阳谷县过活,那就得懂咱们阳谷县的规矩。”
“什么规矩!”
“想安安生生的做买卖,那就得交上份子钱。”
“份子钱?什么份子钱?”西门庆道:“左卫相公是我岳丈,知县相公、县丞相公、主簿相公是我兄长,我从未听他们说起过什么份子钱?你倒是哪里来的乌龟王八蛋,竟然敢在阳谷县要起份子钱来了!这还是不是大宋朝的天下了?大宋朝且不找他们要,你们敢找他们要,不给就打人,砸摊子,莫非你们要揭竿造反,将阳谷县说成你们的天下吗!”
众泼皮一听这话傻眼了,他们原本只是想欺负外地人,找他要点散碎的银子花花,没成想竟然成了图谋造反。
又一个泼皮站出来,虽然他知道西门庆不好惹,可是照着西门庆的说法,那得满门抄斩,正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嘛,他道:“西西门庆,你.你不要含血喷人”
西门庆一看还真有不怕死的,走上前去,扑的一拳,打在了那反口的泼皮的鼻子上。只打得那反口的泼皮鼻血迸流,歪倒在一边,西门庆冲上去,又是两脚,踢在那泼皮的胸口,痛得那泼皮哇哇惨叫。其他三个泼皮见西门庆动手打自己的伙伴,出手颇为狠毒,个个都噤若寒蝉,哪个敢上来相帮?
打了这个泼皮,西门庆又走向另外三个泼皮,指着他们从容的道:“该到你们了!”
一开始和西门庆说话的泼皮噗通一声跪在西门庆的面前道:“大官人饶命,饶命!”
西门庆瞪了一眼众泼皮,低声喝道:“滚蛋!”
三个泼皮搀扶着挨打的泼皮,连滚带爬的逃了。
围观的百姓看了,一起喊道:“大官人威武!”
西门庆将武大郎扶将起来,关切的问道:“没什么事吧。”
武大郎连连作揖道:“多谢大官人。”
“没事,没事,再有人找你麻烦,你不要和他们争执,要钱先给钱,然后去我府上找我,看我整治不死他们。”接着,西门庆又对爬起来看着满地被踩得稀烂的梨子的郓哥道:“好了好了,别哭了,这些梨就当我买了。”西门庆掏出来三钱碎银子给郓哥:“你年轻,跑得快,再有事就去我府上告诉我,知道吗?”
郓哥抹去了脸上的泪水,破涕为笑道:“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
西门庆又去帮着武大郎收拾担子,见担子被打坏了,西门庆又掏出二两银子给武大郎道:“这钱拿着,去治一副新的。”
武大郎连连给西门庆鞠躬道:“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
“好了好了,不用鞠躬,我有事先走了。”说罢,西门庆又挤出了人群,扬长而去。
刚走出不远,只听身后有人喊道:“前面走的可是西门大官人啊?”
西门庆回头看去,只见喊自己的是华何禄,反身走了过去,唱喏后问道:“主簿相公有甚事啊?”
华何禄笑道:“都是兄弟,主簿相公称呼的生分了,日后我就称呼你四泉兄弟,你唤我做哥哥,如何啊?”
“哥哥有甚事唤住小弟。”
华何禄笑道:“四泉兄弟,这几日在家中做得好大的事啊。”
西门庆笑问道:“哥哥这是何意啊?”
华何禄四下里看了看,低声问西门庆道:“你是不是在乐和安的庵堂里养了十个年轻貌美的良家女子?”
“是啊。”
“知县相公第二天便知道了,嘴中喃喃的说:看来这个西门庆倒是个有心之人啊!”华何禄看着西门庆,不无忧虑的道:“这话不是好话,兄弟得当心啊。”
“多谢哥哥提点。”西门庆问道:“只是,兄弟该如何处理这事呢?”
“与其等着知县相公来问你,不如你主动告诉知县相公。如果知县相公埋怨,你就将这事都推给乐和安,只说是他要你这般做的”华何禄微笑着微微点头道:“我的意思想必兄弟也明白吧。”
西门庆一愣,难怪华何禄巴巴的给自己通风报信,原来是想借自己的手来对付乐和安啊。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