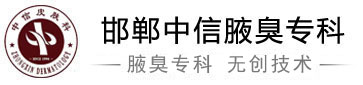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闻不出味反而是好事?
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席卷全球,到目前全球经过实验室确认的的感染者已经超过300万,致死超过21万。
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对这种全新疾病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比如,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嗅觉丧失(降低)/味觉减低是新冠病人常见的症状之一。
而且,有人通过观察发现了嗅觉和味觉功能障碍与Covid-19之间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在互联网上,有关嗅觉/味觉丧失搜索数量的不断增长与Covid-19流行程度密切相关,提示这是新冠病人非常普遍存在的症状。
而在门诊病人中,患有流感样症状和嗅觉丧失的患者Covid-19检测阳性率高出其他人6到10倍。
同时,门诊Covid-19患者自我报告嗅觉丧失的比例高达59-86%;远高于住院患者5-35%的比例。
这些迹象都初步显示,嗅觉丧失不仅是Covid-19的一种常见症状,而且,门诊轻、中度患者中出现这种症状的可能性似乎远高于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
这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嗅觉障碍是不需要住院轻症良好的预测因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分析发现,出现嗅觉障碍的患者更大机会为轻症,是是否需要住院的良好预测指标。
研究者对2020年3月3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共有169例Covid-19患者进行了回顾分析。
其中的128人的资料包括气味和味觉数据,这128人中26(20.1%)名患者符合住院标准。
与仅需要接受门诊治疗的患者相比,入院患者报告嗅觉丧失/障碍,以及味觉障碍的比例小得多,分别是26.9%vs 66.7%,23.1%vs 62.7%,
已知,像年龄大,有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都与新冠患者出现重症和需要住院治疗有关。
这组患者中,年龄大(53.5岁 vs 43.0岁),患糖尿病(30.1%vs 5.9%),呼吸困难(76.9%vs 43.1%),咳痰(30.8%vs 11.8%,呼吸加快(19 vs 18次/分钟),体温升高(37.7℃ vs 37℃)与需要住院有关。
除此之外,医生判断需要进行胸部X光片检查(92.3%vs 34.3%),以及检查获得阳性结果(88.5%vs 14.7%)更能提示最终需要住院治疗。
经过统计学分析,嗅觉丧失/障碍与入院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自我报告发生嗅觉丧失/障碍患者仅需门诊管理比需要住院的可能性高5倍。
这个相关程度明显高于年龄(1.04倍),呼吸困难(4.39),咳痰(3.21),体温高(2.33),心跳加快(1.04),呼吸加快(1.04)等因素;
仅次于糖尿病(6.67),是否需要进行胸部X光片检查(21.94),以及胸部X光片检查发现浸润和/或胸腔积液阳性结果(20.91)。
就是说,Covid-19患者存在嗅觉丧失/障碍,强烈提示为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轻、中症;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比年龄,呼吸困难,咳痰,体温高,心跳加快,呼吸加快等更灵敏;仅次于患有糖尿病、需要进行胸部X光检查,和胸部X光检查发现存在肺炎的征象。
为什么嗅觉丧失/障碍的Covid-19患者更可能是轻症?虽然Covid-19患者发生嗅觉障碍的具体机制还不清楚。但是,一般认为,这可能跟一般感冒等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暂时性嗅觉障碍的原理一样,就是由于鼻腔黏膜发炎、充血,肿胀,导致鼻腔通气不畅。
我们知道,负责闻味的嗅觉上皮处在鼻腔顶的后部,粘膜之间的空隙即所谓嗅裂原本就狭窄,鼻腔发炎更容易被挤压不能通气,因而,发生鼻炎时容易出现嗅觉障碍。
也或者嗅觉上皮细胞直接受病毒侵犯发炎,功能本身受到影响导致暂时性嗅觉丧失或障碍。
那么,嗅觉障碍为什么可以预测更可能为轻症呢?
已知,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需要与人体细胞膜上的ACE2受体结合才能进入细胞才会造成感染。
在不同个体,不同部位细胞上ACE2受体分布密度,或者与病毒的亲和可能有所不同,因而,病毒侵犯的部位也不尽相同。
新冠病毒感染者出现嗅觉障碍可能是因为病毒只侵犯或者更主要侵犯鼻腔引发鼻炎;而没有或者更少感染下呼吸道,因而更少机会表现为重症。
临床研究已经发现,嗅觉障碍的Covid-19患者影像学检查显示,双侧鼻腔嗅裂阻塞更严重,提示局部炎症更明显。
早期的研究已经发现,鼻腔嗅上皮细胞也表达ACE2受体,原本就是容易被新冠病毒攻击的目标之一。
总之,Covid-19患者出现嗅觉障碍提示感染可能更加集中在上呼吸道的鼻腔,下呼吸道没有受累或者感染轻一些,因而,临床上更可能表现为轻症。
加州大学的研究中,嗅觉障碍与咳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与植物相互缠绕的布朗族世界
编者按:植物与人类的世界相互缠绕、相互影响。在云南普洱市澜沧县的景迈山上,布朗族与各种野生植物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但布朗族与植物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变迁。
荷兰莱顿大学视觉人类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纪录片导演刘晓慧,在景迈山进行了半年多田野调查,从夏季到冬季,用民族志摄影记录下了景迈山上各个季节生长的植物、相关的植物信仰、植物传说、不同时代的布朗族与植物的故事。本文为刘晓慧的纪录片作品《三个世界》的创作手记,其中布朗族相关图片皆为刘晓慧的摄影作品。
在2023年夏天的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也是我在景迈山田野的第15天,我依旧在树木芳香和鸟鸣声中醒来。与往常不同的是,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鼓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像是一部神秘学小说的序幕。循着鼓声的指引,我遇见了一位背着大竹篮的布朗族奶奶,竹篮里装满了芭蕉叶。询问鼓声的来源时,她并未直接回答,或许是语言的隔阂,她只是轻轻挥手,示意我跟随。尽管心中困惑,我依然紧随其后,途中又遇到几位同样肩扛芭蕉叶的妇女,最终我们抵达了茶祖庙。庙中约有二十位布朗族女性,分作五组,忙着用芭蕉叶包裹糯米。一位看似组长的妇女向我解释,明天是布朗族的中间节,大家正在准备供奉给祖先和神灵的菜包。我好奇地问她,为何选用芭蕉叶,她神秘一笑,言道:“芭蕉叶是特别的,能带给祖先祝福”。
刘晓慧
她的话让我惊讶,却也觉得合理。我在半个月的景迈山生活中,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植物与灵媒、与治愈的故事,也目睹了当地人用植物沟通祖先神灵、治疗疾病的实践。景迈山,位于中国西南的群山之中,布朗族是这片山地的原住民族,依旧保留着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植物不仅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他们用植物建造房屋、制作食物、治愈病痛,也会在信仰仪式中借助植物传递祝福,而精神沟通正是布朗族人能感知到植物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体现。因此,我开始想要探索:植物能动性在布朗族的生活世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人类学学者又该如何呈现植物能动性,使其跳脱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述局限?
在过去,我们往往只专注于用人类语言对于原住民自然世界进行文字性描述,而忽视了视觉和听觉的呈现方式。于是,在2023年夏季的景迈山田野结束后,我又在2024年1月返回景迈山,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去记录和拍摄这种复杂而生动的关系。为了让不会说话的植物“自我表达”,我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植物内部的电流转译为音乐的设备——plantwave,并在景迈山进行了一场植物音乐实验。布朗族老者说,“榕树是布朗族的神树,有榕树的地方就有寨子”,于是我邀请布朗族人来到寨口的大榕树下,一起倾听这棵高大乔木的“声音”,让大家重新感知植物的存在及其与他们自身的联结,最终制作完成一部关于布朗族与植物世界的纪录片。
纪录片《三个世界》海报
1. 景迈山的布朗族
布朗族是一个居住在中国云南省、缅甸和老挝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果从旧石器时代的“蒲人”算起,布朗族的历史已有约8000年。早在中国的商周时期,布朗族的祖先蒲人就已广泛分布在古永昌(今保山)县的辽阔土地上。之后,古蒲人继续迁徙、融合与分化。如今,布朗族仅分布在云南省的勐海、澜沧等市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统计,中国境内布朗族的人口数为127345人。从人口数量排序,布朗族排在中国民族第37位。此外,他们还分布在缅甸、老挝和泰国。
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布朗族人生活在森林茂密的山地,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和温带气候。景迈山位于东经99º59’14”~100º03’55”,北纬22º08’36”~22º13’7”,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山上的植被结构主要由三层组成:乔木层、灌木和草本植物层,垂直空间分层明显。这个生态结构为布朗族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多种野生植物,使他们与植物形成多样而复杂的关系。
景迈山的布朗族人信奉一种被称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形式,体现为所有自然界的实体或现象,如森林、河流、雷电、太阳、月亮和星星等,都是由神灵主宰,并依据神灵的意志运行。布朗族人最重要的神灵大多与山脉和森林有关,如森林神、水神、昆虫神等等。大多数植物也被认为具有神圣的力量,例如,在雷雨天里燃烧腊肠树的果子能减弱雷声,榕树作为神树是布朗族村寨的庇佑者,而芭蕉叶则是帮助布朗族人与祖先和神灵沟通的精神媒介。因此布朗族人对森林怀有敬畏之心,并认为许多树木具有灵性和能动性。
《景迈山布朗族与植物群像》我邀请布朗族老年人和年轻人们以自己舒服的姿态,在景迈山芒景下寨的大榕树下合影。景迈山上的布朗族世世代代与植物共生,但是与植物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
2.世俗与灵性世界
在景迈山,植物不仅构成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还在布朗族人的生活世界中产生影响,例如被用作世俗世界里治愈疾病的草药,以及与灵性世界中无形的存在(灵魂和神灵)互动。
我的第一位对话者是苏医生,一位60岁左右的布朗族男性,是芒景村最受尊敬的草药医生。每个布朗族村庄通常有1-2名从事医药活动的民间医生,他们大多数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传统知识。在西医被引入布朗族地区之前,当地草药医生主要使用山林原生的植物作为草药来治疗一些常见疾病,也会通过召唤灵魂、向神灵祭祀和进行占卜的方式来治病。村民们称这些草药医生为“moya”。在布朗族的传统知识中,大多数植物是药食同源的,用作食材的同时也用来疗愈。在访谈中,苏医生提及的有传统医学效果的植物多达74种,其医疗作用不仅包含了常见的解毒、清热、利尿、补肺等,还包括族内一些治疗疾病的偏方,比如四棱豆可以治疗小儿惊风,宽叶韭的根(撇菜根)用来除狐臭。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苏医生用一种布朗语里称作“mengmawai”的植物熬一大锅药汤分给村民喝,山上的新冠病很快便消散。尽管接受过现代医学的教育,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医药手段时,苏医生说,“西医只是一种方式,在我们布朗族的山上,我们有自己的方式”。
《布朗传统舂食》在布朗族的饮食传统中,舂,是非常独特的烹饪技法。图展示了舂所用到的器具——木制的锥形木臼,及其植物性食材以前布朗族人去茶园或者田地中劳动,常常会带上一包白米饭和一包舂好的植物拌辣子作为午餐。
我的另一位对话者是一位名叫“Kupia”的布朗族老人。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字,而是因为他负责主持村中的祭祀仪式,其他人尊称他为“Kupia”。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他的本名。Kupia告诉我,布朗族老人曾用腊肠树来减弱雷声。关于腊肠树(Cassia fistula L.),它是一种高大的乔木,果实呈暗棕色、圆柱形,种子被隔膜分开。在我与Kupia的对话中,我了解到布朗族人相信腊肠树具备与天神沟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在特定条件和仪式中展现。Kupia告诉我,当他还是小孩时,他的母亲会将榕树的果实放在火上烧,同时诵念一些“口功”(记载在傣经中),这时会发生神奇的事情,雷声和雨势都会逐渐减弱。关于腊肠树的故事,Kupia并不是唯一提到的人,我在村里询问了五位老者,他们都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有些人是亲身经历过的,而其他人则是听人述说的。
除了腊肠树,Kupia还提到了同样具有神圣力量和能动性的榕树。腊肠树的能动性在于帮助减少人们对自然的恐惧,而与腊肠树不同,榕树的能动性在于惩罚族内的越界者。Kupia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寨子里有一个人在白天故意破坏了榕树的一节树枝,晚上回家时就感到背痛,睡觉时也做噩梦。求助过多位医生而始终治疗无效后,他找到Kupia进行诊断。Kupia告诉他,榕树在森林中扣留了他的魂,而Kupia可以帮助他把魂叫回,“在日出之时、日落之时叫回你的魂,去寨口、寨尾、森林边缘和河边叫回你的魂”。
这些关于灵性植物的故事,我不仅从Kupia那里听到,还从芒景村的许多布朗族老人那里得知,尊重神树已经成为族内约定俗成的规则。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被赋予类似神圣性与能动性的树,多属于高大乔木,是古代族人在缺失观测工具的情况下难以触及的自然一隅。当我行走在山上的原始森林间,抬头向上望去,它们的树干高耸入云,有些树冠能遮蔽天空。那遥远神秘的树冠层寄托了布朗族宇宙观里最朴素的浪漫想象、恐惧与敬畏。
《寨口的大榕树》布朗族村寨的头和尾一般都有一棵大榕树,在布朗族的传说里,榕树是寨子的保护神。布朗族老人们对我说,“有榕树的地方就有寨子”。
3、布朗语与植物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丰富的文化宝库。正如蒙古语中有很多词汇用于描述马儿的特征和行为,布朗语中的植物名称也蕴藏着很重要的文化讯息。苏医生跟我说,布朗族祖先与榕树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从布朗族语言的词源角度进行解释,“在我们的语言中,榕树叫做kangwang,这个词表明了这棵树是‘鸟类动物栖息的地方’。我有时思考,为什么傣族人叫我们wang,这与kangwang的发音非常相似,而我们不能砍伐的神树正是这种榕树,随便乱砍的话人会生病的。因此,我想布朗族祖先与这棵榕树必须有某种关系,以至于我们的族名与这棵树的发音相同”。
布朗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布朗语,属于南亚语族中的孟-高棉语支,但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使用普通话和傣文作为书面文字,尤其是借用傣文来记录和传承自己的历史文化。关于口语的使用程度,目前这一代布朗族小孩还能够使用布朗语来交流,但其词汇水平仅停留在日常对话的层面,关于山林中植物名称的词汇已经掌握甚少,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植物之间的联结度正在弱化。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作为书面语的傣文在山上正在濒临失传。这背后的原因是结构性且复杂的,由此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祭祀等盛大的精神性仪式中,布朗族长辈通常会朗读或吟唱用傣文书写的傣经,来与神灵沟通,或者为族人祈求福祉。因此,能够阅读傣文是族人理解仪式内容的重要能力。然而,根据我对傣文传承人倪老师的采访,村里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尚在学习傣文,这与前几代人相比,人数非常少。当年轻人无法理解和学习这些经文时,他们也不再相信布朗族传统认知当中的植物灵性,神圣仪式都将沦为形式展演。
《开门节中的芭蕉叶》景迈山的布朗族每逢傣历开门节,会用芭蕉叶来制成饭包、菜包,并将其作为贡品来供奉先祖亡人。
《布朗族妇女制作饭包》在傣历中间节的第一天,布朗族各个寨子的妇女会自发集结起来,分工有序,制作敬献祖先等贡品。
我的另一位访谈对象小艾,一位22岁的布朗族大学生,是芒景村傣文传承人的儿子,目前在昆明学习体育教育。小艾告诉我:“作为傣文传承者的儿子,我必须学习傣文,这有点像是被赋予的使命。但我目前还不是太想学,我的梦想是通过打篮球进入国家队,甚至想去美国留学”。谈到自己的梦想时,他神采奕奕,充满热情,与我无限畅谈去欧美游学的愿景,以及自己喜欢的球队球赛。像这个年纪的其他青少年一样,小艾与流行文化、全球文化接轨,精神世界无限向外扩展,但同时,属于他的另一部分始终被烙上传承布朗文化的印记,向内收束在景迈山。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景迈山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虫害,族人仍然选择通过祭祀昆虫神的传统方式来解决问题。由于外人不被允许参与,我只能在参与者拍摄的视频中观看仪式的全过程。在祭祀台旁边,我再次见到了小艾,他正在跟随自己的父亲诵读傣文。但与父亲专注而虔诚的状态不同,他面无表情,思绪似乎在游离,或许已经越出了山林间。
4. 普洱茶与植物
在布朗族地区,茶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近年来逐渐演变为单一作物。景迈山拥有全球最大的、最古老且保存最完好的古茶林,是中国普洱茶最大的种植、生产和贸易中心,现有茶园7万余亩。自2003年美国101公司进入景迈山,开始包装和推广当地茶叶以来,族人逐渐通过茶叶获得经济收益,来自景迈山的普洱茶也逐渐被世界所知。根据芒景村委会的记录,2003年的年人均收入仅为800元,而到2022年,年人均收入已提升至15000元。
《叶掇与晒茶》图为布朗族奶奶叶掇与自家晒干的茶叶。茶是景迈山布朗族的信仰寄托,布朗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茶祖,茶祖用茶叶救了迁徙途中布朗族的性命。现在茶叶也成为布朗族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来自外界的工夫茶泡法也深入影响了本地人饮茶生活。
茶不仅是景迈山的一种重要经济作物,最初也是一种生长于垂直生态结构中部的植物,与上层乔木和下层草本植物和谐共处,每种类型各自占据其生态位,彼此既促进又互相限制:乔木层反射和吸收大量光线,在干燥炎热的天气中具有一定的储水功能,保护茶树的生长。但乔木的生长也会遮挡茶树的光照,从而限制茶树的过度繁衍;草本层生长着低矮多元的植株,这种植物多样性可以有效防止茶树遭受虫害,但也会与茶叶争夺土壤中的养分。然而,随着普洱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古茶树被过度种植,逐渐挤占其他野生植物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人们也在人为砍伐树木和过度除草,以增加茶树的种植面积,这一举动短期内似乎有利可图,但从长远来看正在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芒景村书记告诉我,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景迈山的严重虫害与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模式也有关系。原本能够抵御虫害蔓延的草本植物层被大量拔除,因为它们被视作茶树生长的障碍。可以见得,景迈山居民与野生植物的关系正在因普洱茶经济而发生变化。过去,老一辈族人视野生植物为神圣、灵性和有能动性的主体,而年轻一代则越来越将其视为被人类经济行为所支配、驯服的对象。
《南康爷孙与茶叶传承》图为布朗族非遗烤茶传承人南康书记与他的孙子,二人手握茶叶,采自古茶林里的古茶树。茶叶是景迈山最重要的植物之一,关于茶叶采集知识与信仰传说,将在布朗族代际之间传承。
在此,我还想讲述我的一位对话人的故事,来表明普洱茶经济给一个布朗族家庭带来的变化,以及如何改变了年轻族人对野生植物的认知和感受。小叶是一位18岁的布朗族女孩,目前在澜沧县上高中,即将进入大学阶段。根据小叶的回忆,普洱茶最受追捧的时期是在她小时候,当时她只有6岁,采茶季节时必须跟随父母上山。由于采茶是一项非常耗时的工作,小叶和家人需要在早上6点天刚亮时上山,直到日落才回家。有时候他们只随身携带几个干粮,午饭时在茶田中随手采摘一些植物来饱腹,营养且美味。小叶告诉我,在她的记忆中,茶田里有很多种类的草都能吃,味道很好,还有些可以用作玩具,像是可以用来吹气玩的气球,还有一种叫做无患子(Sapindus)的植物,搓一搓就能产生像肥皂一样的泡沫,可以用来洗手。但随着她渐渐长大,有很多植物她几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家茶园里的茶叶越来越密集,需要她经常除草来保障茶树的生长空间。小叶还提到,为了建房子和开辟茶园,路边许多植物被砍伐,有一种甜笋是她小时候最美味的食物之一,长大后很少见到了。当我问她是否听说过腊肠树和榕树的故事时,小叶表示她似乎听家里的老人提起过,但她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相信这个,认为这都是迷信。
5、植物音乐
在景迈山,布朗族对植物能动性的感知正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于是,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帮助布朗族人重新认识植物,或帮助他们唤起关于植物能动性的记忆。我选择了一种超越语言的诗意方式来完成——声音。事实上,声音一直是被人类忽视的感官形式,其地位始终次于视觉,但却在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人类学家Ihde认为,“事物的声音并不是语言的声音,而是表达了一种直接的声音,反映物体的本质和潜在的丰富性”,多物种(尤其是植物)的内在声音是“感知与多样性的共同体”。虽然植物不像动物一样,能够发出人类听觉范围内的声音,但植物内部进行生物活动的动态过程,可以通过一种技术,被转译为人类听到的音乐。
于是我借助这种技术,在芒景下寨的大榕树下策划了一场植物音乐会。我和小伙伴录制了许多段不同植物的音乐,并邀请不同年龄段的布朗族人进入森林收听这些植物音乐。我们还邀请他们将设备的探测器贴在植物身上,即时感受植物当下的律动。但这毕竟是一项源自西方科技的发声技术,其音乐类型也与布朗文化难以接轨。在这一过程中,我的意图并不是告诉布朗族人这就是你们熟悉的植物所发出的声音,因为布朗族有着自己的植物认知方式和本体想象。我的意图是利用技术让族人感受到植物内部的波动,看是否能够激起他们对于自身与植物相互联结的回忆,并引出他们的讨论。
刘晓慧在“探测”植物的状态变动和对应的音波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布朗族人对植物音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他们并不试图弄清楚其背后的科学原理,而是欣喜地向我分享自身关于植物的故事。例如,当一位布朗族女性听到“longsan”植物的声音,忍不住与我分享说,这种草药曾在她们家附近随处可见。在她女儿九岁那年,女儿咳嗽得很厉害,于是这位女性为女儿采了一些“longsan”煮成药水给她喝,经过短短几天,女儿的咳嗽就被治好了。那时,西药方式尚未进入景迈山,人们遵循着布朗医学体系,也熟悉各种草药的疗效。这位女性还说,那时他们在采集草药时非常注重保护其根部,以便它们能在来年再次发芽生长。
参与植物音乐会的其他族人也回忆起了自己与植物相关的童年记忆,年轻人开始忆起在成长过程中消失的植物。例如,我上文提及的小艾也开始跟我说,在他小时候,同学们放学后会一起去山上爬树,摘一种叫“binguer”的水果,但这种水果如今已很难找到。围坐在小艾身边的成年人由此开始感叹许多植物的布朗语名称已被遗忘,而这些名称常常蕴含着祖辈传下来的宝贵植物知识。他们还对每种身边植物发出的声音非常好奇,尤其是那些通常难以接触到的高大乔木。一位布朗族女性表示她想听榕树的声音,因为自己对这棵神树敬仰已久,想要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听到榕树生命的律动。此时,布朗族的认知系统与现代技术的探寻方式不再冲突,技术开始帮助布朗族人找到他们与植物之间的连接。
在激发布朗族人分享他们对植物能动性的认知方式之外,我的这场植物实验还意在让观影观众,尤其是来自城市的、西方世界的观众感受大山深处植物的声声浅吟。影片制作结束后,在2024年10月份的世界粮食论坛-良食边会的放映结束后,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观众私信我分享他的感受,“我此前对于景迈山布朗族和人类学纪录片一无所知,但片子里树木声音的呈现和布朗族姑娘的谈话,总让我想起在我长大的地方——奥地利南部那片森林,也在发生着相似的故事”。
2024世界粮食论坛放映现场
6、写在最后
自拍摄结束起,距我离开景迈山和布朗族朋友们已经过去了近八个月的时间。我非常怀念在山上的时光,还有那些发生在族人与野生植物之间的故事。于我个人而言,景迈山的创作旅程深深治愈了我自己,既关于从树的力量中汲取到生活勇气,也关于重新认识人类存在于世界上的位置。亦真亦幻的见闻构筑了一个轻盈灵动的梦,而创作完成后的每一次播放、讨论,都让我重新进入这场梦中,与那片山林里的植物和族人相逢。创作者既是造梦者,也是援引人,“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
《叶灵,有灵气的叶子》布朗族小姑娘叶灵,目前是一名初中生。她的名字叫叶灵,他父亲说,名字的意思是“有灵气的叶子”,来自于布朗族的万物有灵信仰,并希望这种信仰代代传承下去。
事实上,景迈山的故事,不仅是关于布朗族文化的一次纪录,也是关于全球生态关系的一面镜子。布朗族的信仰与生活方式展现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态观,在他们看来,森林不仅仅是资源,而是家园,是知识和情感的载体。而在当代世界,人与自然的分离正在加剧,生态危机、物种消失、传统知识的流失,使得许多与自然共生的文化濒临消亡。我的纪录片不仅关心布朗族的过去与当下,也希望触及更广泛的问题: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控制自然,我们是否也在丢失某种更深层的联系?
在电影的结尾,我将自己的所见所思写成学术论文,但又将它掷入水和土壤中,让它被景迈山的野生植物覆盖、被那片茫茫大地上的众生吞噬。作为人类学学者,我们习以为常的人类语言记录工具,或许根本不足以呈现多物种世界的活力和意识;作为创作者,我引导布朗族人反思自己对植物的认知,但我从来都不应占据主导地位,我所引入的科技工具也不能替代他们自己的认知体系。布朗族人和森林里的众生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不断生产着独具智慧的生态知识。我只希望做一个传播者,记录和放大他们的声音。
参考资料:
Archambault, J. S., 2016, Taking Love Seriously in Human-Plant Relations in Mozambique: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Affective Encounter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2), 244-271.
Chao, S., 2018. In the Shadow of the Palm: Dispersed ontologies among Marind, West Papua, Cultural Anthropology, 33(4), 621 -649.
Ihde, D., 2007. 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2nd e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Kohn, E., 2013.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苏国文, 2009, 芒景布朗族与茶,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杨圣敏, 2004, 中国民族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统计年鉴,2021
来源:刘晓慧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死亡人数是新冠数倍,人类第一大疫情黑死病,当年是怎么结束的?
如果在未来的百年、千年内人类会灭亡,那将是由什么引起的?资源枯竭?核战争?答案或许是病毒。
这种预言在近十年来经常被人提起,虽然发言的都是那些专家或权威学者,但人们对此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感觉这些问题离自己太遥远。
直到2019年底,一种名为“COVID-19”的病毒席卷全球,让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无数人的生活因其受到重大影响,在中国,我们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总量六百多万,这还是在国外很多地区预防、解决不及时的情况下造成的。
虽然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但在这种超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面前,新冠的致死率连2%都不到。尤其在中国,由于严密的防控和治疗措施,在人口密度、基数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死亡人数被牢牢扼制住了。
要知道,比起新冠的前辈,人类历史最著名的三大死神——黑死病、天花、大流感,新冠病毒实在柔弱无比。
连我们现在人人脸上都必备的口罩,也是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第一次开始被大规模使用,从此以后成了抗疫的第一道防线。
或许只有回顾历史,在那曾经死于剧烈痛苦的上亿人面前,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病毒的可怕,坚定与其抗争到底的决心。
1347年,在欧洲,一场伟大的“圣战”刚刚落下帷幕不久,当罗马的天主教廷得知自己的圣地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占领后,立刻拉动一大批西欧国家开启了前后多达九次的征战,史称“十字军东征”。
战争结束后,军队纷纷回到欧州,但这次凯旋却成了一场巨大灾难的序曲,因为这些士兵中有人带回了一种致命的病毒——鼠疫,又称黑死病。
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地中海的商人带来的病毒。
当时的欧州海上商业贸易极其发达,而地中海正是必经的交通枢纽,病毒被携带过来以后又顺着其他的商船扩散到了欧州各地。
总而言之,不管到底是哪种来源,在当时,原本只存在于中亚地区的鼠疫杆菌的确传入了欧州,并且瞬间全面爆发开来。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让超过两千五百多万人丧生,占当时整个欧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堪称灭绝级别的灾难。
鼠疫杆菌,顾名思义,这种细菌一般会以老鼠这类啮齿动物作为宿主。
而老鼠的抗性十足,所以可以携带病毒到处传播,同时,老鼠身上的跳蚤也会被感染,然后在叮咬了人类以后把病菌传入其体内。
当时正值中世纪,是欧州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著名的城市拔地而起,人口也不断增多。
但众所周知,欧洲人是非常依赖商业贸易的,很多物资都必须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商贸成了不少国家生存的根本,甚至许多地方干脆就不种植粮食,完全服务于海上贸易。
在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欧州的贵族、庄园、艺术,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场景背后,他们基层民众的生活可谓一塌糊涂。
客观来说,和同时代的中国相比,他们过的日子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
当时欧州城市才刚刚兴起,结构很简单,设计上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御敌功能,至于像排放污水之类的系统可以说几乎没有,相关的公共设施更是完全不存在,因为政府觉得卫生是个人问题,自己去解决就好了。
所以欧洲人的解决方式很简单——不解决。
他们可以说根本没有卫生观念,由于淡水资源的不充分以及个人意识不到位,而且底层民众较为贫穷等一系列原因,欧洲人几乎还处于一种野蛮时期。
他们很长时间才会洗一次澡,所有垃圾全部都丢放在门口, 大小便更是随意解决,城市内的道路也没有经过修整,基本上几经践踏就一塌糊涂。
而西方人,尤其是男性,本身体毛就十分旺盛,很容易滋生细菌,就像他们发明了香水是为了遮掩狐臭一样。
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城市中越来越拥挤,但卫生条件却没有相应增强,这就导致了城市的环境越来越糟糕。
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欧州,医学的概念基本上还处于萌芽时期,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才被发现,在欧州被这种病毒忽然袭击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染上的是什么病,又要怎样才能治好。
在1347年时,鼠疫突然出现在中亚地区,但是这里荒芜偏僻,人口也很少,病毒根本传播不开来。
但是这一年正值蒙古铁骑再次与欧州发生碰撞,黑海旁的一座小城卡法被团团围住。
但此时,鼠疫开始在蒙古军队里流行起来,让攻城变得十分艰难,蒙古人便采取了一石二鸟的计策——将染病死者的尸体用投石车直接丢入城中,这完全就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生化武器。
而后,卡法很快被鼠疫摧毁,城里的人纷纷出逃,他们有些人携带的鼠疫病毒也就此在欧州传播开来,而那些每天在海上不断往来的商船更是为病毒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意大利第一个被攻陷,感染人数与日俱增,病人们头晕、发烧、干咳,淋巴肿大,越来越严重后,他们的皮肤上开始出现黑色的斑点,最终伴随着身体内脏的全面崩溃而死亡,最快的病例,从感染到死亡仅需要一天时间。
对于这种完全未知的病毒,因为病人死后,尸体会腐烂发黑,所以在当时,被称作“黑死病”。
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千年古都,也是欧州的经济文化中心,从这里辐射开来的贸易线路几乎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而当鼠疫在这座城市爆发以后,很快就沿着无数条航路向着整个欧洲甚至非洲扩散,英国、法国、俄罗斯......
这场瘟疫来的太快,传播的也太快了,而且对欧州当时那地下的医疗环境来说,人们一旦被感染,几乎不可能被治好。
那些手足无措的医生们,还在采用着老掉牙的烟熏、放血、催吐等疗法,后来甚至用蜡把人整个裹起来,用高温的火焰直接灼烧人的淋巴肿块。
但,没用,可怕的鼠疫根本不可能用这些好笑的法子就被驱除了,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活的人、死的人,都会成为继续传播的源头。
那些已经被疫情攻陷的地区,人们会在墙上画下一个大大的白色字母“P”,可是后来,这个白色大字几乎随处可见。
那个时候,死人的规模简直难以想象,在第一个被病毒感染的国家意大利,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佛罗伦萨里,超过八成的人都被感染,每天都有几千几千的人不断死去。
有些人无比恐慌躲在家中,结果被发现后,早已经腐烂发臭、死去多时,尸体就像小山一样被车辆拉到郊外掩埋。
当时的信息传递是很缓慢的,欧州更是无法做到严格的人口户籍管理,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统一控制情况,尤其是早期,许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或许只听说到处都在死人,于是便惶恐地、散乱地开始逃命,从城里逃到乡村,从沿海逃到内地,黑死病也就如蛆附骨般地跟着这些人群进一步扩大感染规模。
只要想一想,在如今政府严格管控,群众积极配合进行隔离,人人带口罩、做核算的情况下,疫情仍然偶有反复,可在当时的欧州,医生根本束手无策,政府完全无法掌握情况,人们把病毒带着到处跑,所造成的影响简直是毁灭性的。
在数量惊人的死亡面前,民众们终于拿出了一些措施,他们意识到了疾病的传播性,开始焚烧病人的尸体和那些可能携带病菌的物品,城市和城市之间切断了往来,不少地区开始实行小范围的隔离政策。
可是这样做的效果很是微薄,毕竟在对微生物一无所知的时候,大家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疾病是由老鼠、跳蚤这种东西带来的。
人们的内心只剩下绝望,在宗教信仰强盛的欧州,许多人把这场瘟疫当作是上帝降下的责罚,他们根本无力抗拒,只能祈祷,还有人每天鞭打自己试图向上帝赎罪。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干脆把责任全部推给犹太人、异教徒,这是中世纪很典型的做法,说是因为这些人从恶魔那里带来了瘟疫,于是到处展开屠杀。
因为医生太少,而且没用,走在抗疫最前线的反而是那些教堂中的神父、牧师,在思想愚昧的大环境笼罩下,他们手捧圣经、挂着十字架,行走在病人们中间,以上帝的名义实施拯救。
但拯救的手段居然是祷告、洗礼,他们坚定地相信这些生病的人都是因为罪过,只要罪过被赦免,他们就会好起来。
当然,这些思想在黑死病面前当然是毫无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神职人员反而大批大批地被感染后死去。
当时的欧州处于政教合一的统治下,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下算是半公务员性质,他们一死,政府的控制力就更弱了,民间完全混乱了。
不仅是疫情,各种暴动、偷窃、抢劫等等全冒出来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持续下去,欧州的灭绝并不是不能预见的。
但到了1352年,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居然瞬间消失了,人们忽然发现没有新的感染者了,大家纷纷走出家门,迎来了新的黎明。
直到现在人类也没有搞清楚黑死病当年到底是为什么消失的,不过最合理的推测是因为这种病毒的致死性、传播性都太强。
因为人是病毒的宿主,如果死得太快,也会隔断病毒的传播,而活下来的人都已经产生了抗体。
这场席卷欧州、让许多城市几乎变为空城的大瘟疫就这么随风而来随风而去,但其所留下的深远影响,不只是那巨量损失的人口,还有对宗教的冲击。
灾难中,那些自诩上帝使徒的人没有任何阻止瘟疫的办法,人们直面了最恐怖的死亡以后,觉得自己应该活在当下、尽情享受,在这种环境下,后来著名的“文艺复兴”、“大航海”、“工业革命”才陆续发生。
如今,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但绝对要认识到它的危险性,人类与病毒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如今的医疗科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武器,但病毒也同样在不断变异,每个人都应该居安思危。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