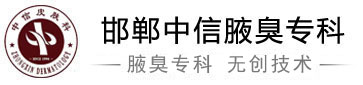清宫秘藏珍本医书《种杏仙方》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古代医药图书,大多上承清内府藏本菁华,就文字而言,已有汉文、满文及蒙文等中医占籍,藏品堪称丰富齐备。因历年久藏官阙之中,为皇室秘籍或海内孤本,迄今尚未世人所知。2000年,故宫博物院与海南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了《故宫珍本丛刊》,其中包括中医古籍善本数十种。
明万历刻本《种杏仙方》一书为清宫秘藏珍本医籍,因版本稀有,故传本甚少。现《故宫珍本丛刊》收入其中,通览其书,所载病例皆为日常易见,涉及内外妇儿诸科,涵盖病理诊治、常用药物、简便验方等方面,是研究古代中医处方学的珍贵史料。
版本款识
《新刻种杏仙方》四卷,明万历十一年金陵周庭槐刻本。一册。黄竹纸封面,线装。版框高19.5厘米,宽13.6厘米。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均有句读。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注“种杏仙方”四字,版心镌卷次及页码。扉页刻“金谿云林龚廷贤编辑,金陵前山周庭槐刊行”。书前有明万历辛巳岁孟秋觳日大梁进士何出图“刻种杏仙方引”、万历九年(1851)岁次辛巳盂秋,金溪云林山人龚廷贤序。凡例四则。次为目录卷次。
龚廷贤序云:“余窃自信,乃取家大人所传方书而续其余,成医鉴一帙,镌之以便世用。第方多萃味,而宴人僻地,或掏之难,诫杏林遗春也。乃复窃父志,括俚言,切病情,选方择味,类以一二易致者,动疗钜疴,见者奇之,命曰《种杏仙方》。”
卷末刻万历癸末仲春金溪云林山人龚廷贤跋。劝谓世人医药治其已病,不如预防未病,平素在于养生之道,培养身心健康。并附诗一首:“海上仙传秘,人间杏作林。谁知方药简,何谓病根深。守业经三世,回生抵万金。但存斯卷在,不用召医临”。
此书《中国善本书目》子部(医家类)、《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为:《新刻种方》四卷,明万历九年辛巳(1581)金陵周庭槐刻本,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辑撰者龚氏生平与著述
龚廷贤(1522-1619),一作应贤,字子才,号云林,又号悟真子。明江西金溪下澌里(今合市乡龚家)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其父龚信,世以医为业,曾任太医院医官,著有《古今医鉴》十六卷,经廷贤整理刊行于世。
龚廷贤年幼时,曾习举子业,屡试不中,遂秉承庭训学医。尝以“古良医济世,功同良相等”自励。故博考历代医书,自《内经》以下,“莫不穷源竟委,拆奥抉疑,贯穿融合,临证设治复以己意”(《金溪县志》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后寻师访贤,更勤于临证,久之贯通医理。诊治遵古而不拘泥,深明五脏症结之源。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均有建树,尤其擅长于儿科。被誉为“医林状元”、“回天国手”,曾是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
据清康熙年《金溪县志》记载,龚氏在河南一带行医,时值开封疫病肆行,“连染于间巷,有阖门病卧者甚众。时医大都因循古法,治而无效。廷贤察其症状,以己意立方,获佳效,全活者甚众,名噪中州。尚书闻其名,荐为太医院吏目”。时“鲁王妃患疾有年,太医治而不效,廷贤诊之,药下而愈。鲁王酬以千金,固辞不授,乃命刊刻其所著《禁方》(即《鲁府禁方》)一书行世,又画其像礼之”。志书中称赞他“志在济世,不以技鬻声利”,遂名动京师。
龚廷贤一生行医,勤于著述并传承医术,所著书凡十数种,至今为人传诵。今存者有《济世全书》八卷、《云林神毂》四卷、《万病回春》八卷、《寿世保元》十卷、《种杏仙方》四卷、《鲁府禁方》四卷、《医学入门万病衡要》六卷、《小儿推拿秘旨》三卷、《眼方外科神验全书》六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十卷等。其中《小儿推拿秘旨》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儿科推拿专著。《万病回春》与《寿世保元》两书取材广泛,选方切于实用,在国内及日本、朝鲜刊印和流传最广,它从理论上分析病理、症状和治法,并附有方剂及数百味药性歌诀。迄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万病回舂》清经纶堂刻本、清善成堂刻本;《寿世保元》清康熙六年大业堂刻本、清道光九年广顺堂刻本、清道光二十四年苏州老桐石山房重刻本及满文抄本。
内容选介与医方特点
《种杏仙方》之所以珍贵,并非版本流传稀有,而在于此书所载之医案辞浅旬俗却医理深奥,论证析源多有独到之处。所例医案逐次说明病源、病象、诊断、治疗和处方,其中汇集了不少民间医方中的精粹,以及各种外治膏药的配制和劝善良规四十歌诀。本书切于民间实用,在古籍医方的延存与借鉴中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此书是按内外妇儿诸科及急救用方分类汇辑,卷中所涉内科49种、外科31种、妇科9种、儿科6种。每门首为歌括,概述病源。各门下列常用效方,每方下详载药物、剂量、炮制方法、治法禁忌等。其内容以上述诸科分为四卷:
卷一:中风、伤寒、(附伤风)、瘟疫、中暑、中湿、脾胃、伤食、痰饮、咳嗽、喘急、哮吼、疟疾、痢疾、泄泻、霍乱(附青筋),呕吐、翻胃、欬逆、吞酸、诸气、痞满、胀满、水肿、积聚、五疸、补益、痼冷(即阴证)。
卷二:失血、出汗、眩晕、癫狂、五痫、健忘、邪崇、不寐、头痛、须发、耳病、鼻病、口舌、牙齿、眼目、咽喉、结核、心痛、腹痛、肋痛、腰痛、疝气、脚气、脾痛、消渴、浊证、遗精、淋症、小便闭、大便闭、痔漏、肠澼、脱肛、腋臭、诸虫。
卷三:妇人、经闭、崩漏、带下、种子、妊娠、产育、产后、乳病、小儿、惊风、疳疾、癖疾、小儿杂病、痘诊、痈疽、瘰疬,疗疮、便毒(附鱼口疮)、疳疮、杨梅疮、臁疮、疥疮、癣疮、癜风、诸疮、杖疮。
卷四:折伤、金疮、破伤风、汤火伤、虫兽伤、中毒、诸骨骰、救急、附日用杂方,附经验杂方、金铃法、造酒法、春雪歌。
《种杏仙方》一书属于单验方集,故流传很少。其特点为:一,它以收集民间偏房、验方、单方为主,收方1000多首,其中含有大量珍秘的中医药方。但也夹杂少数具有迷信内容的方剂。二,书中各方多系一、二味中药组成。偏房或验方中所用米类,豆类、果类、姜蒜、油酒等皆为日用所食之物。三,书内集方原则,效方皆出自平昔试验有效者录之,民间相传之方亲验者录,未验者虽近理固合之。四,药有奇罕、价高、不易取得间或猛烈峻攻之药不予收录。由此可见,书中所集虽以单方、品少、实简为特点的小型方剂,但是却汇集了龚氏多年搜集的经验效方。另外,本书中诗歌赋颇多,歌括用韵多以方言人韵,显示出“括俚言”的特点,且文旬简练,格调活泼,颇具文采,实为龚氏著书的一大特色。尤其他编辑文献审慎择方的严谨性和尊古而不拘泥的科学态度,是其医书传承至今的准绳。
《种杏仙方》的不同版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又两种:一,《新刊种杏仙方》四卷,明刻本(残),藏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二,《新刊种杏仙方》四卷,明龚廷贤辑。日本庆安三年(1650)室町通鲤山町小岛弥左卫门刻本,四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 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
陈寅恪和钱锺书为何都撰文讨论“狐臭”问题?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围城》里方鸿渐海外归来,到中学演讲,开口即是鸦片梅毒,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它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容安馆札记》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坐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围城》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本段借用“视昔犹今”新浪博客《容安馆札记》释读文字。此君将《容安馆札记》全部释读并公之于众,功莫大焉!)
《寒柳堂集》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幅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寒柳堂集》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
《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 上一篇:狐臭冬天严重(狐臭冬天严重嘛)
- 下一篇:狐臭的痛苦(狐臭的困扰)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