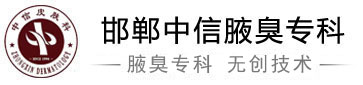花香满人间,聊腋臭
我们这代人,都是看着动物世界长大的。
场景一:非洲大草原上,几只羚羊正在啃食草叶,一阵微不可察的风吹来,所有的羚羊都闻到了远处草丛中蛰伏的猎豹的气味,两眼瞪大,耳朵竖起,发足狂奔,猎豹悻悻离去......又是减肥的一天;
场景二:一只猎豹在非洲大草原上游荡,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晃荡出了自己的地盘,但是“肚子好饿啊”,顾不得了,一阵微风吹来,另一只猎豹的气味将他定在原地,思忖片刻,掉头回去......,又是XX的一天。
气味,是进化赋予的识别与威慑;当闭上嘴巴的时候,气味从身体上各个毛孔渗出来,尤其是,顶泌腺(apocrine sweat gland ASG),又被称为大汗腺。(职业生涯早期,我无数次将它和AUG搞错,人家是霸气的突击步枪。)
顶泌腺人人都有,幽兰之香的有,鲍鱼之肆的也有。不同的不过是顶泌腺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以及分泌物被定植的细菌分解处理为了“氨”和“支链脂肪酸”,由此可知,顶泌腺和细菌感染是导致分泌物向腋臭转身的关键。
历史上有个腋臭的君王,就是宣太后芈月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楚怀王,因为有腋臭而被自己的妃子嫌弃,唯独南后郑袖提出“这是一种君王之气的表现,是男人味的极致”。由于郑袖阿姨的特殊癖好或者是强大的自我心理暗示,她成功了!鸠占鹊巢好多年,史书上只有南后郑袖,不知道楚怀王的正经夫人是谁。
那会儿楚国还是强大的,因为芈月还小嘛,当时魏国交流过来一个美女,一时间风头无二,楚怀王也演了一出“自此君王不早朝”。郑袖阿姨羡慕嫉妒恨之下,进行危急公关。“妹妹啊,你长得那么美,大王很喜欢,但是你觉得不觉得啊,你的鼻子有点点歪,大王不太喜欢。那咋办呢?你每次见大王,拿扇子遮一下吧,晚上熄灯了就不要紧了。”“哎呀,大王啊,魏美人就是不喜欢你身上的那股味道,才遮鼻子的。”于是,魏国小姑娘被割了鼻子,然后自尽了。
一个由腋臭引发的血案。
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对腋臭是带负面情感的。少年时,我知道除了夏天还买花露水的,是狐臭;现在我知道,香水老往胳肢窝喷的,是狐臭。且不说那个味道让周围的人不适,衣服上的浅黄色斑点,以及衣物混洗后家人衣服上长期存在的异味,让人远远逃离。
幸而外科手术切除,是治疗中重度腋臭最有效的方案。执业以来,我接触并治疗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腋臭治疗的关键点还是顶泌腺(ASG),作为皮肤腺体,在产生一定量分泌物以避免皮肤干燥的作用之外,分泌物会带有细微的异味,甚至有些异味是好闻的,我们运动之后身上荷尔蒙的味道,不是真的性激素外放,人作为哺乳动物还没有进化出这个功能(昆虫有),不过是较高浓度的顶泌腺分泌物在交感神经兴奋时大量分泌的效果,一群二十几岁的大男孩踢完球,脱了上衣在校园走过,T恤甩动,带着温度,夹杂着一丝丝硝石硫磺的气息,对着下风口的女性飘去,无论拿着书本的,还是拎着书包的,免不得有部分偷偷扶下眼镜,打量一下,微微脸红,这就是,令人侧目的“行走的荷尔蒙”风景。别问我怎么知道了,问就是:曾经年少时,我也是行走的一员。
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经常愁的是切不干净和皮肤坏死。
虽然说外科手术是金标准,顶泌腺在切开直视下也是清晰可辨的粉红色粟粒状,分布在真皮下的浅层筋膜,文献中的(3.169±0.589)mm是统计学结果,而临床操作中为避免复发,还是会在6~8mm的深度“宁错杀,不放过”。浅筋膜的厚度在全身各处并不相同,在腋窝是相对厚的,也导致此处的浅筋膜甚至可以分成浅深两层,浅层存在真皮下血管网,深层则包裹部分腋窝淋巴结,浅层切的多了,可能是皮肤坏死的原因,深层切的多了淋巴液渗出可能导致手术切口不愈合和渗液,执业多年的,谁没有被腋臭惨痛教育过?
传统的认为,顶泌腺的分布与腋毛相关,于是刮除毛发后画圈标记就可以开始,但是复发和残留的报道让国内外的同行开始思考。思考和讨论的结果是,顶泌腺分布范围与腋毛无绝对相关性,顶泌腺不是毛囊的一部分,也不承担毛囊的保养工作,解剖与功能的不相关,导致进化路上两个虽然相伴,但是并无唇齿相依的关系。还是我们国家的团队发现并提出了顶泌腺分布的血管相关性,哎呀,它们居然是被腋窝周围内外前后的血管弓围绕起来的,充足的血供支持了顶泌腺大量蛋白质和脂肪相关产物的合成分泌,能量充足的地方可以有盈余的干点别的,这个经济学的道理在腋窝,很经济啊!
有显微外科血管情怀的我,看到这些资料时的那个小激动啊!脑子里电光火石的闪过无数临床科研的念头,才发现,利用血管弓定位啊,阻滞血管减少顶泌腺数量和质量啊,处理血管相关交感神经减少血管活性啊,都被人报道了,默念“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不过,也好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期的工作越多,我们的临床科研方向可能越细化和精准的解决现实问题,避免一部分不能落地的基础研究。
交叉学科的血管超声定位可以缩小预设的手术区域,就像定位导航一般。而每每跨界而来的技术总是让人又激动一把,整形外科成员里的脂肪抽吸技术在浅深层次的浅筋膜抽吸应用就是当下做腋臭手术时的宝藏。2022年的报道提出,“肿胀抽吸 皮下修剪术>皮下搔刮 皮下修剪术>皮下修剪术>梭形皮肤切除术>皮下搔刮术>肿胀抽吸术。”我总是很喜欢那些善于思考的同行,并引为“同类”。传承而不固守,吸纳而不盲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脂肪抽吸技术对浅深层脂肪的工作分析,认识到对浅筋膜内的一切组织都可以有全面彻底的清理,而“真皮下血管网并不是皮肤唯一血供,周围血管弓存在交叉支配。”的研究进展更坚定了基于抽吸的综合技术在腋臭外科治疗的C位。切口,可以很小。研究,还在继续......
然而,缺憾依然有,比如说,残留。
我带着歉意再次面诊,而沟通却并不伤感。大部分求美者要的是不特异于他人的气味,而淡淡的,并不令人反感。甚至我收到了安慰:王医生,挺好的手术效果,我觉得我身上没有什么味道,周围的人不会与我特意保持距离了,我感觉我很融入。是慰藉,也有一丝释然。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根除”的问题。
能不能做到保留皮肤活性,不导致并发症的根除,经常是学术交流中让人自豪的技术流。我也炫目于彻底铲除与皮肤无痕愈合,但是我们也知道,周围的血管损伤及深部的淋巴结损伤可能导致皮肤不能如期愈合,或者愈合后残留瘢痕,而毛囊附近的瘢痕又是那么的不能接受。我没有找到根除的标准以及根除的有效率与皮肤切口并发症的相关性的文献,但是临床观察下,似乎不刻意做到彻底清除,保留部分浅筋膜组织,切口相关并发症会低一些,自觉案例累积还不够,我汗颜于不能提出自己的结论。
但是从“融入”的角度看,我们好多求美者的面诊诉求是腋臭,逆向分析下,动机其实是职业人的社会性受到影响,潜在的意识层面的原因是我们东亚国家对于“狐臭”的文化层面的抵触和鄙夷。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异味”,轻度的腋臭是仅有棉签拭子在凑近时的异味,以及30cm的距离之外存在少许异味,而国人正常社交距离是80~120cm,在这个距离上,轻度的腋臭可能根本闻不到,而社交场景里的其他味道,淡淡烟草味,浓浓咖啡味,以及运动后的“行走的荷尔蒙”,都会干扰你对面人对于“气味”的判断,可能就根本意识不到有一丝丝的异味是来自对面的你。于是,在正常社交距离下可以平凡生存的个体恢复了人的社会属性,心理的缺憾得到了修复。
那么,还会追求根治吗?毕竟,我们在层流环境中单独面对一个人,而周围没有咖啡、没有烟草味的场景,很少;要说有,手术室吧,但是那会儿你和对面的人都戴着口罩,空气中还有浓浓的消毒水的味道。
那么,与少量的被轻度感染的顶泌腺共存,似乎,是可以的。
我的一点思考,还不能作为临床的争鸣,但稍作求美者的宽慰吧,毕竟,这世界上的人,要是都没什么味道,这世界岂不是很尴尬?既然拥有各色人种的世界才算是彩色的,那么各种气味的人熙熙攘攘,应该也会增加些人间烟火气吧。
幸运的是,我所面诊的,都不缺乏在这世间的自信,在门诊,尤坐花香;而在自媒体端,分享自己的一些理论学习和实践感受,解答求美者的疑惑并揭去整形外科一些技术上的面纱,我感受得到对面屏幕前的豁然开朗,与众乐乎,其乐无穷!
理解并接受,精益且求精,
我意更上层楼,为求花满人间。
#腋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做腋臭手术?#
抒情朗诵作品: 遥致外星女郎
遥致外星女郎
史征波
遥致外星女郎(此图来源于网络)
一
可想而不可及的外星女郎啊!
虽然我已风烛残年,但我的心中总是对你燃烧着一盆爱恋之火,我向往于你,我崇敬于你。
我相信这个宇宙间不仅仅只有一个地球。在庄周和孔丘没有发现的地方,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没有发现的地方,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发现的地方,定然有另一个地球,那里便是你的家园。
你的家园在上帝的目光之外,在人类的想象之外,在我的梦之翼能够飞到的地方。
那是怎样美丽的一个家园啊!
二
而我已没有了家园。
无数的老鼠毁坏了我家房子的墙基。
无数的虫子啃吃了我家房子上的椽檩。
无情的冰雹击碎了我家屋顶上的瓦片。
盗贼入室,一夜之间,我的家里被窃掠一空。
不知是谁的罪恶之手,又燃起一把火,让我的房子化为灰烬?
而我村庄的周围,已没有绿色的田野。无数的野兽践踏了我的庄稼,如今已是满眼荒芜,只有无数野兽的背影行色匆匆。
外星女郎啊,真的,我现在已没有了真正的家园。
三
你应该是有着同地球上的女人一样的模样,对吗?
当然,你是最美丽的,你是一尘不染的。
我想你有着绿色的头发。那是麦苗一样的绿,是玉米叶子一样的绿。
披肩而下。你绿色的长发流成绿色的河,流成绿色的瀑布。
你的阳光也是绿色的,而且是透明的,它照耀着你的河流,你的瀑布。
流淌着,你绿色的长发。在遥远遥远的地球上,有一个失去家园的男子,倾听你长发演奏的绿色旋律。
四
我的天空很低,我的天空布满了乌云。
是谁强暴了我的月亮?是谁奸污了我的太阳?
我的空气好沉好重啊!重压!重压!重压之下,我已喘不过气来。
四周的山峦在缩小包围圈,要吞掉我吗?要埋葬我吗?
我心中的那面旗帜早已被淫风撕裂了,那座金字塔也已崩溃倒坍,那束美丽的火焰早已熄灭。
我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攥着,外星女郎啊,我已不是曾经的我。
给我一双翅膀,让我飞到你的身旁,好吗?
遥致外星女郎(此图来源于网络)
五
你是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吗?
是深秋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样的蓝色,是细雨之后风平浪静的湖面一样的蓝色,是独处于幽谷山泉边马兰花一样的蓝色。
你蓝色的眼睛流泻着蓝色的光芒,所有的一切,都沐浴在你的光芒里。
我的心,也沐浴在你蓝色的光芒里。这是多么的温馨、惬意和幸福啊!
你黑色的眉毛一如画家笔下的栅栏,围拢着你蓝色之目的安静、清纯、祥和以及美丽。
在你的目光里,我找到了我曾经的梦想和希望。
六
我已看不到蓝蓝的天空,我已看不到绿绿的流水。
魔鬼钻进了我的眼睛,我眼前的一切都在变形。
我的山峦总是蒙着一层阴影,我已无法看到那迷人的风景。
我曾放飞的一群白鸽,被乌云吞没了。
我曾放飞的一只风筝,掉进了黑暗的深渊。
我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长着狼一样贪婪的眼睛,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总是奸笑着狰狞。
我还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手里拿着屠刀、棍棒和枪支。
他们从城市里穿过,他们从村庄里穿过。
我还看到无数无数乞求、流泪的眼睛,看到无数无数被抢劫、被强暴、被蹂躏之后的背影。
点亮我最初的目光吧,外星女郎!至少,不要让我怀疑我的眼睛。
七
你的微笑比上帝的目光更慈祥。
从你微笑的双唇中所露出的一丝牙齿的洁白,让我想到了雪的晶莹。
你圆圆的笑靥旋在你青春红晕漫过的双腮上。我感到有音乐般的月光照耀在你的酒靥里,似有淡淡的柳絮轻拢着你酒靥里的月光。
你微笑着,你的微笑散发着一种文静、醇美和至纯的光芒。
我已小醉在你微笑的光芒里。
八
我已听不到阳光照耀流水的声音,我已听不到月光沐浴花朵的声音。
我也听不到夕阳中清脆的牧笛,也听不到一只布谷鸟在翠柳上求偶的热烈的鸣叫。
迷失在叫作人类的森林里,我满耳听到的是老虎的凶恶,是狮子的霸道,是野狼的贪婪,是毒蛇的阴险和狐狸的狡猾。
无法拒绝豪华酒店里春雷般的猜拳行令的狂叫,也无法拒绝乡下老妇人在病炕上的呻吟。
时光不再是一曲美妙的歌谣,我已无法听到它的美妙。
外星女郎啊,难道是魔鬼钻进我的耳朵了吗?
遥致外星女郎(此图来源于网络)
九
你有着一双富有灵感的手。
雪白的手,纤细的手,艺术的手。
是站在白色的云头演奏洞箫的手。
是坐在绿色的湖边演奏古筝的手。
是漫步在蓝色的大海边演奏铜笛的手。
是伫立在火色的晚霞中演奏小提琴的手。
你双手的每一次灵动,都有一曲让我陶醉的音乐从你的指下飞起。
那些从你指尖飞起的音符,就像美丽的彩蝶在梦境中翩翩起舞。
十
我的鼻孔失灵了。
那晨露湿润过的空气的清新呢?
那月季花浓浓的甜美呢?
那紫丁花烈烈的醇芳呢?
我已无法闻到所有的美味。
而扑鼻而来的,除了腐臭还是腐臭。
这是人们手心里夹杂着汗味的铜臭。
是茅坑里的污臭。
是汗水热浸着腋下的狐臭。
草叶在污水沟里发霉的味道,死尸在酷暑里腐烂的味道,淋漓在刽子手屠刀上的血腥味儿。
外星女郎啊,我已闻不到我的清新、我的甜美和我的醇芳了。
我将窒息在无边无际的臭味中。
十一
你穿着透明的衣裳,薄若蝉翼。
绿色的阳光照耀着你,蓝色的月光照耀着你。
光的交错中,你穿了一身朦胧。
是云?是雪?是梦?
你的身段流畅起来。
是山风吹过麦子地的流畅。
是流水滑过河岸的流畅。
是夜莺歌唱一样的流畅。
是泰戈尔抒情诗一样的流畅。
你透明的裙裾飘曳着,姗姗而来,姗姗而去。
你的背影,成为一部小提琴曲的经典之作。
十二
我的牙齿已不再咀嚼生活中的山珍海味。
我没有美味的早点、午饭和晚餐。
我咀嚼着让牙齿瞬间发软的酸。
我咀嚼着足以让人肝肠寸断的苦。
我咀嚼着让人心头起火的辣。
我咀嚼着让人发呕的辛。
所有这些,都是难以下咽的,可又是我必须咀嚼的。
人世间的甘泉已经枯竭,我只能咀嚼酸辛苦辣。
除此之外,我还能咀爵什么呢?
遥致外星女郎(此图来源于网络)
十三
外星女郎啊,你有着怎样的小屋呢?
是神话中的那种小屋吗?是童话中的那种小屋吗?
红色的小屋?蓝色的小屋?金色的小屋?
是否有天鹅绒一样的阳光照耀着你的小屋?
是否有睡莲一样的月光照耀着你的小屋?
是怎样的小鸟用怎样的歌声在你的窗前歌唱?
有浪漫抒情的菩提树在你小屋的门前摇曳吗?
在你的小屋前是一座很大很大的花园,花朵是透明的,蝶翼也是透明的。
你总是在那个花园里飞翔,你的双臂就是你的翅膀。蝶群跟着你起舞,你是一只最美丽的飞蝶。
十四
在人类的森林里,我的双脚迷路了。
野草像针刺一样,扎透我的鞋底,穿进我的脚掌,我的脚印里浸满了鲜红的血液。
陷阱埋伏在道路上,我总是失足,因而我总是掉入一井绝望之中。
还有黑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毒蛇藏在路边的草丛里,晃动着闪电般的舌头,用阴冷的目光盯着我的双脚,随时发起攻击。
还有蚂蝗。
而小路尽头,又是万丈悬崖。
我没有去路,又无退路。在人类的森林里,外星女郎啊,我已是寸步难行了。
十五
外星女郎啊,我知道你没有烦恼。你总是快乐着,你透明的心头有一只透明的快乐鸟在飞翔。
你生活在透明里,生活在五彩缤纷的花园里,生活在一尘不染的小屋里,生活在音乐、舞蹈和诗歌里。
绿色的阳光和蓝色的月光照耀着你,照耀着你唱歌的姿势,照耀着你飞翔的姿势,照耀着你舞蹈的姿势,照耀着你睡眠的姿势。
花园的芳香每天为你洗礼,在你的身上,除了音乐的节奏、旋律和韵味之外,再看不到任何污点。
因此,你成为我的一种向往,一种至死难渝的追求。
十六
外星女郎啊!
伸出你纤长纤长的手臂,我会用我的中指勾着你的中指,沿着你拉回的方向,走进你的怀抱。
用你蓝色的目光呼唤着我吧,我会沿着你的视线,走向你的小屋。我知道,门前你已为我准备好了一把小椅。
对我微笑吧!在你微笑的光芒里,我会张开双臂作翼,飞到你的身旁。
真的,我压抑得要命。我的眼睛失明,我的耳朵失聪,我的鼻子失灵,我咀嚼的是苦难,我的双脚已举步维艰。
我想回到你的身边,同你厮守千年,哪怕是我化成一片透明的叶子,还是化成一只透明的鸣蝉。
让我离开人寰的红尘吧,外星女郎!我已不是曾经的我,人世间不再有我的家园。
鲍尔吉·原野|花瓣落下来很轻
花瓣落下来很轻
文丨鲍尔吉·原野
园子里的桃花落了之后,丁香开了。丁香一开香就下雨,香气被雨水裹挟,流进了土里。雨后,丁香被太阳晒干。它在风里抖动肩膀,调动精神,准备大香。
我在赤峰师范读书的时候,常常被丁香熏得记不住读过什么书。夜里,丁香花的香气如水一样浓烈,我在树下找被熏死的蜜蜂和甲虫。虽未找到,我觉得丁香足以矫治有腋臭的人士,因为它更浓烈。
然而园子里的丁香刚要香,又下雨,一天一夜。出两天,又下雨,两天两夜。其结果是今年春季的丁香没香成。
我觉得雨水干什么都是有意的,哪一种能力太强,难免遭嫉,包括遭到你所想不到的来自雨水的嫉妒。
丁香花谢了之后,变成老实的绿树,雨也停了。山楂树悄悄开出了白花。山楂的红比葡萄酒更红,根本看不出它小时候开这么白的花。山楂花集结一束,好像方便别人摘下来不必用绳子系在一起。
五月,鸟儿的鸣唱更加清脆,它们在天空转弯更加自由。春天的云层已降落到山后,夏云堆积,站立或斜着行走。
蓝天像刚刚苏醒的人,回忆暴雨的每一个细节。我只记得雨在孝信桥南头下起,雨线粗斜,打在脸上甚至有声(可能脸上肉少才有此声)。等我跑到桥北头,雨停。
我回头望这座钢筋拉索桥,以为它启动了桥顶的喷淋装置来对付我。其实不然,河里也落了雨。河岸的锦葵被雨浇得水淋淋。山楂树并没被雨水打落多少花,它的花比丁香结实。
早晨,开在楼门口的山楂花如同落了一群白蜜蜂,几十只蜜蜂挤在一起好像在听戏匣子。
蒲河大道两边有绵延数里的山楂树,在夏日丰茂的绿叶里白得耀眼。春天的梨花没有绿叶扶衬,如雪花,易飘零。山楂花稳健,在绿叶长出之后才从伸出的嫩枝上开花,有叶子替它遮风雨。
在这条路上走,仿佛可以通向花的山谷,此刻排列路旁的山楂树只是迎接的队伍。
一位老人在我前面散步,穿一件蓝夹克,背在身后的右手婉转地转一对发红的核桃。微风吹过,他肩头落上山楂树的几片花瓣,如绣上去的徽章。
他驼背,落上去的花瓣比直背的人要多一些。过一会儿,又有花瓣落在他肩上,并没有风。也许花瓣去投奔他驼背上的花瓣,怕它们孤单。一个手转核桃的老人浑然无觉地驮着花瓣踽踽孤行,显得幽默。仿佛他心里藏着一个目标,山楂花如猴一般趴到他背上跟他一起做这件事。
他去哪里?前面是鸭子湾村,对面是医科大学。那里有谁?时间在他手里旋转的核桃里流逝,仿佛秘密全在核桃里。如果不转动,核桃会裂开,跳出别样的精灵,跳到山楂树上。
山楂树枝丫横逸,挡住人的去路,像伸手往人嘴里喂花。我左右绕开花枝,回头看,自己的肩头也落上了白花瓣。这些花瓣归我了,我竟不知道。有多少花瓣拍人肩膀,人却无知无觉。
我见过花瓣被掺在粥里煮,泡在水里喝,还有人蒸发糕放入花瓣,如桂花、玫瑰花。这些都不如花瓣落在人的肩头上好。人如不觉,带着花瓣跋山涉水尤好。
除了雷声,自然界的一切都很轻,花瓣落下来很轻,鸟儿飞行很轻。竹叶甩落雨滴,蜜蜂飞向花朵,月亮出山,流星下坠都很轻。
重的声音是人类发出的,他们建设、破坏或战争。花瓣落在人肩上不仅轻,而且准,仿佛骑在牛身上游逛,去看远处的风景。
春天远去,夏天到处扎起绿色的帐篷,那么多花朵去了哪里?我只看过被风吹落的花瓣落在树下,花瓣似乎哪儿也没去。
我觉得如此盛大的春花飘零时可以落在公交车顶,落在邮筒上和人们的帽子顶上,落在路人的衣兜和楼房的窗台上,落在两条铁轨和送牛奶工的推车里。
然而花只去花去的地方。虽然风吹,但不可能把花瓣吹到它们不想去的地方。在世上,哪样东西从哪里出来,又回到哪里,均有定数。
比如在大街上见不到小鸟的尸体,花朵只从树枝与草的枝头绽放,然后去了一个地方。蜂蜜藏在蜜蜂身上,蚂蚱折叠成草叶的形状。在世上,花瓣去一个神秘的地方集合,桃花、杏花、梨花,一样都没有少过。
小鸟在一个地方集合,一只也没少过。曾经出现过的早霞和晚霞完好地待在一个地方,雪花和冰也待在它们待的地方,完好如初。它们一起去了那个地方,一排排装进一个箱子,等待冬天和明年的春天再出发。
它们佯作飞雪梨花,把世间装点一番后告退,这世上谁也没问它们去了哪里。人们以为冰雪融化了,花瓣零落成泥。人天天想着骗别人,却被大自然骗了。
我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转头看肩膀,花瓣已消失。风吹不走它们,花瓣被召集到那一个地方。
前方的驼背老头肩上的花瓣还在,只是核桃换到了左手。
来源:六根公众号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您推荐↓↓
王雁翔:雪山上的灯光
美文 | 迷失在丽江的街巷
王雁翔:那些孤独的报刊亭
散文:堡子,土夯的骨肉
王朔:回忆梁左
杨绛:《傲慢与偏见》有什么好?
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柴静:有些人的灵魂,能让你记得一辈子
刘亮程:先父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 上一篇:孕妇祛除狐臭(孕妇祛除狐臭的办法)
- 下一篇:轻狐臭怎么治疗(轻狐臭怎么治疗效果好)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