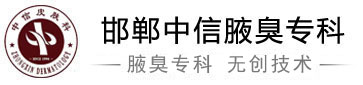长篇小说连载(34)《四只虫子》•上卷(作者刘灵)
“脏水沟里的唐菖蒲已经干枯了,遗弃了我的人,从前不少,今后肯定会更多。”
“我现在更多的是气愤,胸口会炸。”
徐方婧对一只家蜘蛛特别感兴趣,它同样会织出轮状网,但不大可能吃掉性伴。他心想,那就得好好活着,并理清楚思路,别最后等来的只是彻底决裂。她恐怕就是一种职业习惯。他俩在病房兼卧室快速用手机拍照,那种好的关系成就感十足,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什么类型性格?她突然喜欢上庭院中一株高大四米的腊梅树,现在,应该是还没到开花季节。感觉所有人正把她当成了替罪羊,就差没有当面骂你,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就这样,自称卢诗茵的外省婆娘轻容易就和肖家沟的村民达成一致看法,他们这群人变成了合作伙伴。傍晚,开车来到他们基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们在一个名叫玫瑰花酒店二楼上的包房里吃的晚饭,那个老板记得是姓张,他从前肯定药物滥用过,也多次在针叶林阳光屋自愿戒断。然后再一次复吸。
“头真的晕死了。”
“有可能是套头衫衣领太高。”
“警告你,别这样嚣张跋扈,可以不。”
“倒不如认命,可能更自由一些。”
(我是吃饭中途从他们聊天当中反应过来的,就是还没办法确认那个真正直接下手家伙,当然了,凶手是在他或她身后的人。终究功夫不负有心人,别着急,有了线索,别轻易放弃,把线头牢牢抓在手上,还去想那么复杂干啥呢?我可能是在精神病院让别人关憨了!你仔细想想,那个有狐臭的理发师凭什么值得我爱他?更何况,肖福先确实还骗了我。包括王艳死得活该,有狐臭的帅哥更应该先死,他连守自己的老婆都缺少勇敢。就是一个缩头乌龟!可怕的是人心复杂,太难猜测了。就算转了这样大的一个弯也显得力不从心。肖福先不是病死的,也不算吸食过量。噢,对不起,你绝对搞错了!默默地来无声地走,这正是小人物的悲哀。如果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劲,没共同语言,不知道如何相处,那就别轻易打招呼。可能是你没有换一把椅子坐着想,必须要设身处地替那个有狐臭冤死的帅气男孩着想,从来没有我幻想中那样的勇士。)所有家庭成员没有太吃惊,发现对面一个兄弟继续在咳嗽,孙荣浩不知道那名戒断者不停在给什么人打电话。有几个是他的客人,老朋友了。就连张子蕃对这些人也很熟。
他们应该都在基地做过社工。徐方婧快活地站了起来:“那么我们去先换衣服。”
“请!”那人做了个优雅的手式。
所有人边吃边聊天。这样,就算是不怎么正规的最早接触,勇敢者渐行渐远,有心人貌合神离,真正希望干事的,心里也忍不住担心,自戒不像逛商场那样。(我还有自己的许多工作,已经忙得晕头晕脑,也确实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过往行为。只想抓紧时间把一切策划尽可能地落在实处,怕的是夜长梦多,特别牵联到禁毒与戒毒这样的事,容易触碰红线,麻烦也绝对少不了。)徐方婧也再三表达自己的意思,她真的是不想平白无故浪费他时间。从某种不易理解的意义上说大家其实是同类。
“我好像觉察出来,他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感。患了同样病,看是啥东西?”
“更可能是迷茫。”男孩试探性问。
在扑朔迷离的眼神注视和更柔和一些的灯光下,徐方婧显得非常憔悴。她原本仍有许多话,其实压根不知道应该对哪个说。酒店都是最热爱生活的人。现在,他俩简直什么都不想再往下说,也不敢当真这样理解,有种结论不是光凭固执可以获得的。“当然也不必再多说废话,我们这种人从来都命运多舛,稍不留神都会掉进陷阱,更可怕的是,无疾而终。”他其实想说的话是,怎么死法根本不知道?
假如说,他们最初答应这件事有两方面企图,一方面使收集个案更顺利,尽量减少点阻力,还可以看清杜小田的真面目,这个张子蕃究竟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徐方婧有可能恨屋及乌,也就是看桃花的面子上。然而现在,第二条已经不复存在了;说起来肖宗俊脑子转变实在太快,“让我们手脚无措,即惊讶,又非常难适应。”
“他是把最困难地方说在了明处。”
为了能够溜进十号院的总统间洗澡,孙荣浩故意下班稍迟,只不过这种机会太少,想彻头彻尾地享受一番,哪怕今天晚上不回去也值。总统间常年难打开,只有碰到定期检查的时候,他们近水楼台才能够混得进去,也必须要小心谨慎。什么套路?
甚至,包括他本人在内,长期以来也总有不少怀疑。所有人知道徐方婧现在陷入了困境,好像是,针叶林阳光屋财务上很糟糕,她的资金链一下子断掉了。“我也不会再对龙波琼老师提起钱的任何事。”在此之前,这群人长期误会了,原本以为她有许多钱,但她找的钱实际上已花完。大家真正高度赞同她就是态度,最后保存的那种善念。现代人,这种品质特别稀有。
“更应该珍惜的是她作为医生的良知。”
包括每一次分开,他们都会不经意想到会成为永别,好像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有见面的机会,甚至时间节点也感觉不对。她是嫁给了老外还能继续对国家,甚至哪怕对药物滥用者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我太容易受到情绪影响。”
“可能患了抑郁症。”
“就算这样,不太严重。”
“胸口像压着铅球,会窒息的感觉。”
“就是心情尽量放宽松,别太多想法。”
“我会的,她一个女人都可以做到。”
“仔细想想,我们又凭什么不能自拔。”
“难道毅志差别这样大,我绝不能输。”
“失去希望,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他们并不是存在偏见。所有人对她事实上已经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种敬意,甚至是敬畏。而这样的敬重就在肖世豪后来所接触到的家庭成员中普遍存在着。她身后依靠的是谁?肖宗俊再次被人误当成了疯子。
“感情是不是需要彼此信任才能长久?”
袁建详这样对阳光屋的兄弟姐妹们说。
第三章
事隔了多年以后,肖宗俊仍住在疯人院。
他时而清醒,时而变得有些糊涂。他其实不是真正深陷在幻觉中。好像是让人强制性注射了某种并不了解的无色药水,要么,这些“医生”就是把药混在肖宗俊每天必输的液体当中,他心里清楚,事实真相并不是戒毒。他过去提炼过冰,但疯子自个儿从来不去触碰冰。肖宗俊哪怕是对其他苯丙胺类、阿片类、氯胺酮、制幻剂,包括大麻从来敬而远之。他清楚那东西厉害及其滥用后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他的后台老板虎口桃花多次警告过。
“绝对只是治疗!袁建详说,“也许开头是用来帮助戒掉酒瘾,他低估了作用。”
他偶尔会喝点酒,但量不足以使肖宗俊酒精中毒。护士长就是护士长。高瑶瑶和张子蕃其实都有可能是酸枣沟精神病医院给尸虫治疗的医生——或者说,就是他真正的病友。但是,现在他已经逐渐老了,而且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有时候尸虫会把别人做过的事,生拉活扯强安在自己身上,貌似他愿意对那个人或者那件事情负责任。都知道就是句空话,肖宗俊根本也承担不起。他倒不准备当替罪羊,真相就是爱犯糊涂。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患上了绝症,而这个病用大多数病友的话说——包括医生同样认为——应该和爱情有关。医生偏向于滥交的可能性更大。一眨眼功夫肖宗俊从成熟、帅气,充满了魅力男人变得格外苍老,他感觉浑身泛力。去年,也许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像极刻舟求剑,肖宗俊试图找到一个叫纪波涛的残疾老头。连蜈蚣也说他好像并非心血来潮。肖宗俊真发现了一个怪人,(我非常清楚这是呆过的第几家精神病医院,也并不是我最早的时候住过那家,在短短数年之间,我其实已经被他们转移过不少地方。疯子告诉我,常被人塞进汽车。有时可能是囚车,反正人逃不掉。很有可能仍然是那家精神病院。那种地方其实相当正规。他们也许只是拿我在大操场上不停兜圈子,一准儿兜了无数个圈子。更像早年间在一个什么地方,肯定不会是东南亚,那里是真正的劳教所。同样也在大江边,听得见咆哮奔腾的江水,莫名其妙的就知道江面颜色发黑,波光粼粼,汹涌澎湃。医生说,你还记得起四合院来那就说明脑子并没有彻头彻尾坏掉。医生啊,我想知道,实际上我都从来不碰那种东西,又怎么可能会经常出现脑袋旋晕、头痛并伴有幻觉。我肯定会记住的,那些七坡八缓,阳光明媚,一个个被抛弃在脑后的车站。缓升坡草木葱笼,大家置之死地,我碰巧活了下来。
“那些难忘的长途旅行,不知道第二天会出什么事。真的有人莫名其妙会消失。”
“付出得心甘情愿才会有收获。”
“你不是在骗我?”
“你不信那就随便你。”
“当然,一切都有因果循环。”
我始终忘不掉属于我的车站。我的确是曾经有过妻子和儿子吗?现在我想不起来,好像是把他们的名字忘完了。我觉得什么时候搭错了车。于是我在病房放开嗓门唱道:孤独让我不能不说,处境迫使我从不敢随便张嘴乱说,过去那些岁月,究竟糊涂有多少!我落空的希望多不多?那些坏蛋把我绑在小铁床上,我的周围黑了又白了,熬到心碎,汹涌波涛就这样把我吞没。那时候,身体掉进用我的泪水汇集而成的溪流。医生当场笑了起来。他冲我说,尽管放心,真冲不走你的!“那你替我打一辆出租车吧。”噢,完全不对。我压根不想离开这个房间,外面到处有人在追杀我!“我反正早都豁出去了。”他又冲着我笑,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敏感。
“到底方不方便呢?”
我说:“肯定方便,你就跟我挤小床。”
“用不着特意安慰我。”
“找不到任何拒绝理由。”
“你就在我家安心呆!”
他又问,你老婆呢?我说,她跟儿子睡大床。等回到那个工作间时婆娘突然从黑暗中窜了出来,当场把我吓得不轻。那跟变装也确实没关系啊,光凭身形,包括体味也能够区别得出来。怎么可能会发生那种事,那样糊涂,男人跟女人完全不一样。
“你来干什么?”我气愤地问。
他回答说正找你呢。真的是有些尴尬。
致敬发型师:你们辛苦了!
不要再抱怨美发!
更不要再抱怨你的职业!
因为:
我们不仅仅是发型师!
我们不仅仅带给别人美丽和自信,
正是从事的这份职业
改变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借新春佳节,祝每一位依旧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发师说句:“新年快乐,诸事顺利!”
记得一位老师傅说过一个发型师值得骄傲的不是他在事业上有多成功,开了多少家店,月收入多少钱,而是有多少顾客愿意从年轻到年老一直忠实的跟随着你。
借由本文献给一线奋斗的美发师们--你们是值得骄傲的!
发型师,这是一个与“美”息息相关的时尚职业。他们的双手与工具、仿若能够点石成金一般,让各种头发变得更加美丽照人。
有人说发型师就像魔术师,能变出美丽。但是没人知道,发型师有多累。每个理想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要么美好,要么苦涩。走上发型师这条路,其实并不容易。每一位发型师背后,都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辛酸磨练,他们每天忙碌疲惫的工作显得生活单调乏味,不是他们没有追求,也不是他们没有梦想。而是他们大多没有殷厚家庭背景,没有很高的文化学历,没有过硬的坚强后盾,有的仅仅是那份小草般的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请问你知道从小工到合格的发型师要经历多少年吗?腊月的冬天,整天把手泡在碱性的洗发水里,一双双娇嫩的手都洗的跟鳄鱼皮一样,充满血口,每洗一个头,手辣的钻心的疼…好不容易熬3年到了发型师,每天最少要站6个小时,一天能按时吃三顿饭的发型师少之又少,外出学习进修一次动辄几千上万,逢年过节,万家团聚的时候,顾客都希望做个漂亮的发型过年过节的,而我们发型师却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回家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已经睡去了,晚上饿了就泡碗方便面(据统计80%的发型师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90%肩周炎、静脉曲张,100%亚健康)。
相信很多顾客朋友发现,现在的很多发廊已经寥寥无几了,洗头妹早已转行成洗脚妹了,(洗个脚最低50—100元,成本就是一桶白开水,加0.5元的各种中草药,培训15天就可以上岗,而想成为一名发型师最少3年,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工资却不到3000块)
她们不会介意你的头发几天没洗、不会介意你早上有没有刷牙、不会介意你的狐臭有多熏人、不会介意你的脸上长了多少斑点和豆豆、不会介意你眼睛多么敏感掉眼泪,他们都会一概不拒,认真而耐心地默默做同一件事情:努力让每一个顾客都成为她一生中最美的样子!让你成为最耀眼的女主角!
虽然发型师这份工作很苦很累,但是看到客人露出满意的笑容时就会非常地开心,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更加坚定了要走下去的决心。
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发型师,必须是经历无数次的磨练与质疑,必须是经过无数的冷漠和排斥,然后在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里寻找经验成长起来。
我去理发馆理发,里面的姑娘年轻而漂亮,还可以陪顾客聊天等服务
理发我去楼下的美发中心理发。
说起来怪可笑的,这家美发中心在我家楼下开了十多年,我却没有踏进去过一次,我每每舍近求远而从没去光顾的缘由仅仅是,这家美发中心的名字叫作“千变美发制作中心”。
美发中心就是美发中心,为何偏偏要弄巧成拙,添加“制作”一词?多别扭呀!美发,实质上是一种艺术行为,可是一旦称之为“制作”,就大煞风景了。“制作”一词总让我联想到作坊或工厂之类,无论手工业或现代工业,在我眼里,都是俗不可耐而让我不屑一顾的。
但我决定破例了。我破例是因为我对这家美发中心越来越好奇了——我连续几次凑巧听到有人在秘密谈论这家似乎永远生意兴隆的美发中心,他们都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在谈论,说什么哪个美发师是大神,哪个美发师是妖孽之类的。
大神或者妖孽云云,显然是谈论者无意间使用了修辞手法吧。不过,我得承认修辞的力量了。很显然,我被这样的修辞打动了。
我大大咧咧地进了门。美发中心开了两个门,底楼有一个,二楼走廊上也有一个。对于我来说,不用彻底下楼就进去,太方便了。
谁知道,我被一个妆浓成鬼魅模样的服务生给挡住了。她指给我看地面的箭头,那箭头向着门外。接着她给我做了许多手势,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二楼的这个门,只出不进,顾客是从底楼那门进来,“制作”完毕,再从二楼出去的。
我去了底楼,果然,门口的地面画着由外向内的箭头。
进去之后,顿时觉得美发中心排场好大。三个单元的住宅楼,一共七百平米,全部打通了,再用低矮的玻璃屏风分割成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单元,一眼望去,光是站着忙碌的美发师就花里胡哨一大片。
“先生,您一楼还是二楼?”
猛回头,有个妖冶的服务生在我身后发问。
对了,还有二楼的七百平米呢!
“我上楼吧,就是洗一下,理个发。”我答。
服务生凑近了,我才看清,又是一个鬼魅。她的年纪应该很小,浓妆,让人看不见真面目,这么打扮,可能是美发中心故意卖弄噱头吧。
“不,美发在一楼,其他在二楼,如果您不美发,就直接上二楼。”“鬼魅”猩红的大嘴近在眼前,“您有固定的美发师吗?”
“没有,我是第一次来这儿。”我不由自主退了一步。
“那您随便挑吧,我帮您挑也行。”“鬼魅”说着,带我转了几道弯。
面前有三个空位子,三位美发师都像模特那样坐着。
“要不,白姐或青姐为这位先生服务吧!”“鬼魅”指了指穿白裙和青裙的美发师。
但是我发现穿红裙的美发师,她的眼眸里似乎闪了一闪。
“我请她理发吧。”我朝她走去。
“嗯,红姐也行啊!”“鬼魅”说了这么一句,马上飘走了。
我坐下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以裙子的颜色来区分美发师,那么多美发师,怎么区分得过来?
正觉得奇怪,红姐提着一块红色围布,袅娜地过来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红姐的裙子里竟然露出了一截大尾巴,火红的大尾巴,活像红狐的尾巴,它还会活动,时隐时现!
我张大了嘴,可是马上,一股浓烈的狐臭迎面扑来。
对于狐臭,我从小就敏感,也最闻不得了,总觉得让人作呕。
讨厌的狐臭,久违了!自从人类发明了在胳肢窝切除大汗腺的手术以后,在生活中闻到狐臭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没想到,一个如此漂亮的美发师,她竟然没有做这个简单的手术。
当然,我也忍不住怀疑,也许红姐身上的狐臭不是真正的狐臭,它可能是一种时尚到极致的变态香水的味道。这么怀疑之后,怪事出现了——我试探性地深呼吸了几次,慢慢地,感觉那狐臭并不让人作呕了,甚至,它在我身上有了类似于麝香的刺激作用。
“先生您好,您要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红姐帮我系好围布,随手拿出一把喷雾手枪,对准我的脑袋“连开数枪”。
“随便吧!”我微笑着回答,“哦,不!你是美发师,你觉得什么样的发型跟我最配,就……”
我没能说下去,是由于红姐为我梳头,我的后脑勺感觉出来了,她把我的脑袋揽到她的胸前,我的后脑勺,显然正好处于她的两只鼓囊囊的乳房之间。
好在红姐已经听明白我的意思,一边为我梳头一边开始端详起我的脑袋来了。
我打量着镜中的美发师。好奇怪,红姐和旁边的白姐青姐,她们好像都没有化妆,或者是化了素颜妆,反正都以本色示人。红姐当然是漂亮的,但她这种漂亮,不奇怪,因为这是属于青春少女特有的漂亮——大眼睛,眉毛有些浓黑,还连眉呢,眉心也长眉毛;翘鼻子,笔直的鼻梁,鼻翼比较大,嘴唇布满皱褶,上唇还有隐约的茸毛;至于脸蛋,皮肤细腻得让人嫉妒,但不是特别白,刚好是那种健康的肤色,这样的皮肤,恐怕根本就是原色,绝对不是化妆品可以粉饰的。
正打量得出神,发现镜子里的红姐刻意瞥了我一眼,我赶紧出声掩饰。
“刚才你被称作‘红姐’?难道,她比你年纪还小?”
红姐又瞥我一眼,嫣然笑了。
“我年纪很大吗?”她说。
“哪里!我是说,你年纪这么小,难不成她能比你还小?”我说得真诚。
“她当然比我小啦!小好多呢!”
“怎么可能?还小好多?”
我盯着镜子。镜子里的红姐眯起一只眼,吐出很长的舌头,向我做了个鬼脸。
“真的,我年纪不小了!”她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驻颜有术,因为我是个道行很高的妖精啊!”
红姐说得严肃,可能发现我吃了一愣怔吧,马上扭了一下脖子,妩媚地一笑,耸耸肩,然后又在我耳朵边吐出湿漉漉的猩红舌头。
“哦,妖精,妖精好哇!”我不由自主地说。我感觉自己的耳廓差点儿碰到了她的舌头,被她嘴里的热气一哈,随即,整个身子过电一般,麻了大半边。
半身不遂中,我看见妖精般的红姐收回舌头,忽然又张开嘴巴,在我的脖子上虚空咬了一口。
“妖精吃了您!”她对着镜子里的我说。
“这应该是外国的吸血鬼,不是中国的妖精吧?”我呵呵笑了。
玩笑过后,红姐神情突然变得严肃了。她拿起一把牙剪,咔嚓咔嚓就飞快地剪开了。
“哎,当心我的耳朵!”我一阵阵头皮发麻,不禁担心起耳轮的安全。
可红姐的牙剪“嚓嚓嚓”飞舞得更欢了。
“您知道怎么区分美发师的好坏吗?”她自问自答,“很简单,首先看速度,凡是技术高超的美发师,动作都快,相反,动作慢的,技术肯定不怎么样。”
“那为什么说慢工出细活呢?”我笑。
“对呀,话是这么说!”她也笑,“可是您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谁说的?”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那些动作慢的美发师啰!”她答。
话音刚落,牙剪被收起,她换了一把很小很尖的剪刀。
类似这么小的剪刀,我家有一把,是我用来修剪鼻毛的。年轻的时候,鼻毛好像是从来不需要修剪的,可后来就不行了,小小的鼻孔里,每天总是有一根或几根莫名其妙探出尖儿来的鼻毛,还弄得人痒痒的,修剪鼻毛,差不多成了我必修的日课。我认为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但据说,鼻毛长得快是因为空气污染。对了,这样的剪刀以前我买过几把,除了修剪鼻毛,还用来剪白头发——每次理发之后,由我妻子花上半小时的时间,把那些显眼的白发一根根从根部剪去,尤其是在两鬓重灾区。那是个瞪得人两眼发酸甚至流泪的活儿,要有非比寻常的耐心,还要有巧手,后来,我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妻子终于在某一天彻底放弃了,再也不帮我剪白发了。
现在,红姐手里的小剪刀,像是一只,不,是一大群微型的啄木鸟,它们纷纷飞快地用自己的小嘴啄啄啄,啄我的两鬓,极其轻微的断裂声,响在发丝与头皮的交界处……
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使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随即,我想起了自己成年以前的乡村生活:提着竹篮子,握着镰刀,去田里割草,锋利的镰刀贴着泥土划过嫩绿的草茎,那一刻我经常听到极其轻微的嘣嘣嘣的断裂声……
红姐居然想到帮我剪去白发!我这满头白发,她即便神速,即便剪去其中最显眼处的一小部分,也得剪半天吧?
我闭了眼享受,慢慢地,居然彻底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红姐拍醒我的时候,我甚至还能听到自己轻微的鼾声。
“哟,您睡得好香啊!”她在我的肩头笑,“梦见了什么呢?”
她说对了,我还真的在做梦。我梦见自己带着弟弟走在路上,经过了一座桥,长长的窄窄的桥面让人心里发毛,我们不时地瞥一眼下面的河水……接着又经过一座桥,每一回走到这座桥我们都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池塘上面的石板桥,桥身几乎贴着水面,那水,清凌凌的……
“我正梦见自己带着弟弟去理发,去离家三里地外的一个老头子家理发,我们走的正是小时候去理发的那条路,我们来到了一座桥上……”
“桥断了?”
“那倒没有,我是在发愁,因为天色不早了,我想到待会儿到了理发师傅家,弟弟一坐上那张椅子,就会睡着……”
“为什么跟天色有关?”
“有一次,弟弟理完发还睡着,怎么拍他也不醒,可是我背不动他,只好把他抱到理发师傅家的长条椅子上让他继续睡,后来天黑了,我心急如焚,这时,我爸爸找上门来了……”
“哈,有这样的事儿?”
“对呀,说起来像是编的故事,可这是真的。”
奇怪,我刚才像是被催眠了,不由自主婆婆妈妈地说了这么多。
心中一激灵,我清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脑袋上包裹着蓝色的大毛巾。
“剪好了?”我问。
“对呀,很酷的一个发型。”红姐说。
我身上的围布被摘除了,我在等红姐解开毛巾,可她没有动作。过了几秒钟,我只好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干吗?”红姐诧异。
“你看,还裹着毛巾呢!”我说。
“对呀,毛巾当然裹着,您还没洗头呢,上楼去吧!”红姐笑说。
“包裹着脑袋上楼?”我还是困惑。
“对的呀,”红姐睁大了眼睛,“哦,对了,您是第一次来吧?我们这儿都这样,要不然那些碎发会掉下来,掉到衣领子里,也会掉这儿一地的。”
真是汗颜!我尴尬地向红姐一抱拳,像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一手捂着脑袋,转身循着地面的箭头标识往楼梯而去。
到梯脚,有四个浓妆鬼魅模样的服务生,其中一个要带我上楼,我直摆手,但她执意要开路,我无可奈何。
楼上的景象让我好生意外——洗头嘛,与剪发有多大区别?我原以为应该与楼下的格局差不多,可我没有像看到一大片美发师一样瞧见一大片洗头工,因为楼上除了楼梯口一小片空地和收银台,其余全是小包厢。
我被引入某个小包厢,看到一个体态娇小的戴面具的女子,尚未出声,身后“吧嗒”一声,门被反手带上。
我不由得转头一愣,而女子在面具后面出声了。
“先生您躺下吧!我叫小胡,很高兴为您服务。”
听声音,小胡年轻得很,嗓音娇嫩甜美。
“我是洗头哇,不是按摩。”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对的呀,就是洗头,我们没有按摩。”小胡在面具后面痴痴一笑。
也许我太老土了,我真的没有见过按摩床一样的洗头床。
我躺下来,小胡为我摘除毛巾。
“哇!”她惊呼一声。
“怎么了?”我奇怪。
“好有个性的发型!”她说。
哈!洗头工赞美美发师的手艺,算是配套的吧?我没有在意。
我仰躺着,脑袋悬挂在外面,托在小胡手里。小胡手里的小喷头和她的小手配合得恰到好处,让我有一种浑身通泰之感,我很快又睡着了。在睡着之前,我照样闻到了小胡身上传过来的浓烈狐臭,但我已经见惯不惊了。
再次醒过来,是由于突然感到呼吸困难。我发现自己整个脸面被蒙了毛巾,而小胡在毛巾上浇水。
那一瞬间我想到了上中学的时候看过的一场电影,里面有个细节——慈禧太后下令处死某妃子还是某大臣,用的就是在她或他脸上覆盖一层层的湿布,直至下面的人窒息死亡。
我一阵扭动,小胡马上停止了浇水。
“您不会游泳?”她问。
“会呀!游泳怎么能不会?”我答。
“我觉得您不会。”
“怎么说?”
“我在您脸上淋水,您马上有反应,不镇定,这是呼吸困难的表现,也是怕水的表现。”
“怎么会?小时候,在乡下,我家后院有条小河,也有个池塘,前门也有两个池塘,都可以游泳!”
“哦,也就是说,您没有受过正规的游泳训练。”
小胡这么一说,我愣住了。她戳到了关键点。
“那倒是!我是狗刨式游泳,我不会潜水……”
“啊?不会潜水?不会潜水,那怎么能说会游泳?”小胡一副很吃惊的口吻,“所以我说嘛!”
我想反驳,可是一时间找不到词了。幸亏小胡掀了我脸上的毛巾,自动转移了话题。
“您修脸吧?”她问。
“怎么修?”我脱口问,话一出口,发现她手里多了一把剃刀。
“我不修!”我赶紧补了一句。
“应该修呀,我看您好像从来没修过脸的样子。修过之后,神清气爽,仪表堂堂,以后您每次都会修的。”
“我怕剃刀上有病菌,什么乙肝啦,艾滋病啦,什么……”
“您看清楚了,我们每次都换新的刀片!”小胡果断打断了我。
我无话可说,而小胡直接从我上方俯下身来了。
这一回,我从她的狐臭里闻到了浓烈的骚味,这是真真切切的狐骚味。睁眼仔细一看,她的面具原本就是夸张变形的狐狸面具。
我盯着面具中的两个窟窿眼。
“你为什么戴面具?”我问。
“我们都戴面具。”她答。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丑。”
“是吗?”
“遮丑呗!”
显然她是故意自黑。我那么近距离地目睹她露在面具之外的部分:脖子、下巴和部分脸颊,认为她绝对堪称美艳。
接着,我们无法对话了,因为她已经无比细致地开始工作,刀锋掠过,“唰唰”作响,我不便张嘴,更怕她分神,导致任何闪失。
有那么几分钟,我好像又睡着了。当小胡再次在我脸上覆盖毛巾然后又开始浇水的时候,我霍然一惊。
小胡很快掀去毛巾,问了我一个在我听来相当震撼的问题。
“您要不要刮眼球?”她说。
“眼球也能刮?”我几乎惊骇了。
“对,刮眼球。这是我家祖传的绝学,我是这里唯一有此绝学的员工。”她语气淡定。
“刮破了怎么办?”
“既然是绝学,就不会刮破。”
“我还是别尝试了。”
“您年纪不小了,眼球上堆积了太厚的垃圾,如果刮去这些垃圾,视力可以恢复到最佳状态,就像积满灰尘的玻璃茶几,抹布一擦拭,玻璃马上透亮了。”
趁着小胡转身的刹那,我赶紧坐起来,下了洗头床。
小胡的眼睛在笑。她过去开门,然后伸手指了指外面。
“那么,就去吹一下吧。”说罢,她又痴痴一笑。
外面早候着一个鬼魅。她带我来到楼梯口。那里有两把椅子,椅子边分别静候着两位戴狐狸面具的美发师。
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美发师拿起吹风机,呼呼地吹起来。
这时候我仔细端详起镜子里的自己,“呀”的一声惊呼起来!
我看到了镜子里满头白发的男子!
“是焗油了吗?焗成了白色的?你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呀!”我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快。
“哪里,不是焗油,是美发师把您的大部分黑发都剪掉了,特意彰显了您的白发。”美发师用梳子梳了几下我的头发,笃定地说,“先生您不觉得这样更酷了吗?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您看,是不是比以前更年轻了?”
是的!我已经看出来了,镜子里的自己,足足年轻了十岁!而且,我发现自己脸上有了妖魔的神态!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