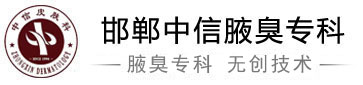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犬夜叉】第二十一集:犬夜叉
第二十一集:犬夜叉。
犬夜叉首次使出风之伤,仅一刀便劈开云霄,无数妖怪瞬间灰飞烟灭。奈落得知后,深知再派妖怪劫杀已无意义,遂决定先夺刀。没了刀的犬夜叉犹如废物。
于是奈落派出珊瑚的弟弟琥珀,并用四魂之玉碎片控制其身体,抹掉其记忆,使其成为没有感情的工具人,再派至犬夜叉等人必经之路上,屠杀整个村庄。
面对这悲惨的画面,弥勒本想分头调查。但琥珀突然出现,瞬间挥出镰刀。幸好犬夜叉反应迅速,一刀挡住。但面对重逢亲人的珊瑚,她已混乱不堪。奈落得知计划成功,立即收网,控制琥珀向自己方向跑。珊瑚也追了上去。
但他们发现前方有一道结界。只有珊瑚能进入,犬夜叉等人被隔离在外,无法进入。弥勒心中隐约感到不安。
在结界内,珊瑚与奈落相遇。奈落表示,如果想救弟弟,就必须取回铁碎牙。否则,就取走弟弟体内的四魂之玉碎片,让他立即丧命。
奈落以弟弟的生命要挟珊瑚,她十分愤怒,但还是决定偷回铁碎牙。
犬夜叉和弥勒突然醒来,感觉到敌人来袭。外面被妖怪包围,他们赶忙冲出。
弥勒知道难以应对,但七宝阻止他使用血,因为它的伤还未痊愈。
快住手弥勒,别为了那些杂碎去送死,这里我能解决头目。
犬夜叉挥刀砍向琥珀,无数妖怪蜂拥而上。犬夜叉拔出铁碎牙,瞬间斩杀几头妖怪。但很快,铁碎牙被琥珀的镰刀锁住,犬夜叉被迫防御。然而,经过几轮交手后,他发现琥珀并不强大,于是立即发起反击,一刀将其逼退,并轻松扯下镰刀的锁链,将琥珀摔在地上。就在他准备杀了琥珀时,阿离阻止了他。他只好放下铁碎牙,并挥拳打向琥珀。我太心软了,杀了他就好了。这是奈落的圈套,我明明杀了这小子,大家就安全了。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琥珀说话了,他自责地痛恨自己,因为他杀了父亲和村里的所有人。于是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取出了维系生命的四魂之玉碎片。
然而,就在这时,珊瑚出手阻止了。她知道这是奈落对她的试探,于是立即拔出铁碎牙,向奈落的城堡飞去。琥珀也紧随其后。
奈落的实力究竟有多强?犬夜叉和杀生丸费了半天劲,都拔不动铁碎牙,但奈落却轻易地拿了起来。是因为阴刀城主的身体吗?当珊瑚为了拯救弟弟的生命,拿着铁碎牙飞向奈落的时候,奈落不肯放了琥珀,两人一言不合,直接开打。珊瑚持着铁碎牙上前,本以为她要砍人,没想到她却把铁碎牙扔了出去。这波操作让人看不懂,最后她把刀交给了奈落。两人开始了刀战。奈落似乎不是珊瑚的对手,狼皮伪装被珊瑚轻易地劈开了。他不得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然而,珊瑚并没有被他迷惑,而是继续追击。最终,他忍无可忍,拿出真正的实力,一刀砍碎了珊瑚的匕首,然后再顺势一刀划开了珊瑚。云母从背后袭来,一口咬住奈落的肩膀。但奈落的狐臭太臭了,直接熏得她满地抽搐,没有比我的瘴气更毒的东西了。珊瑚也一样。
奈落制服了珊瑚后,叫出了琥珀。原来他用四魂之玉的力量救活了琥珀。他不仅威胁珊瑚偷铁碎牙,还计划让两姐弟自相残杀,让珊瑚憎恨弟弟,然后亲手解决弟弟。这样,弟弟背上的四魂之玉碎片就会沾上邪气。
这就像当年让桔梗和犬夜叉互相憎恨自相残杀的圈套一样。奈落的计划可谓一石二鸟,既能轻松拿到铁碎牙,又能让碎片沾上邪气。但他没想到,无论琥珀如何伤害珊瑚,珊瑚始终没有拿起飞来骨反击。奈落不明白,一个杀了父亲和同伴的弟弟,姐姐却不肯取其性命,甚至弟弟的命比自己的还重要。
他实在想不通,珊瑚为什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就在这时,犬夜叉等人也赶来了。奈落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了,于是用瘴气包围了众人,想把犬夜叉淹没在这片瘴气之中。然而,阿离却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因为他身上带着四魂之玉碎片,阿离果断拉起弓箭,一发破魔之箭射出,瞬间引发了核弹爆炸。犬夜叉也被那股强大的气流所震慑。奈落更是惨不忍睹,直接断去了一臂。奈落,你真的太弱了,你净化了邪恶之物、瘴气和毒气,却被桔梗的破魔之箭所伤。
于是,奈落为了验证阿离是否真的是桔梗的转世,又硬生生地吃下了阿离射出的箭。这一次,他终于确认了这的确是桔梗的破魔之箭。因为它已经能够穿透瘴气,将其击退。他急忙带着琥珀逃跑,甚至连铁碎牙都顾不上。
因为刚才已经用生命验证了对方,再不走真的就危险了。
小说:准备和美女约会,道长师傅却告诫我,她被脏东西附身了
刚想问他有啥问题。
帐篷外突然传来一句急促的娇呼声。
我们慌忙跑出去看。
许可琴正一脸惊恐,花枝乱颤,颤抖着手指着常羽说,你帐篷里怎么有蛇?
常羽依旧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没事别靠近我!”
说完,他弯身掀帘,钻进帐篷。
我隐隐感觉常羽那副冷冰冰的模样,有点像儿时在黄河边上遇到的那个白衣少年,神秘、阴冷、果绝。
须弥勒笑呵呵地打圆场:“许老板,蛇有什么好奇怪。黄河边上,没有蛇,那还叫黄河吗?别说蛇了,蛟龙都有!我小时候,还看到过蛟龙渡劫呢。”
单三叶拉着许可琴:“可琴姐,我刚解个手,你怎么跑出来啦?赶紧回去吧。”
深更半夜的,许可琴跑到常羽的帐篷里干嘛?
左胖子嘴角上扬,发出冷笑。
回到帐篷,我问左胖子咋回事。
左胖子嘴角叼根烟,露出一脸邪魅的表情:“许可琴长相不赖,身材也棒,要不是这几日是祖师爷斋祭日,门规禁止我办那事,道爷真想上了她!”
我差点晕过去,难怪死胖子刚才一直盯着人家看。
道貌岸然,衣冠禽兽指的就是他。
我向左胖子竖起鄙视的中指。
“可我要不上了她,又对不起她,太他娘纠结了。”左胖子不理我的鄙视,继续自言自语,随后,似乎想到什么,转头对我神经兮兮地说:“要不便宜你小子,把她给办了?”
我算是服了:“纠结你大爷!叫你是来做事的,你X虫上脑算怎么回事?”
左胖子用眼睛虎着我:“我问你,许可琴有没有勾搭过你?”
我愣了一下,这事我没同他讲,他咋知道呢?于是,不好意思地解释:“那什么……我长得还行,像她这种年纪的女人,容易对我产生冲动。”
左胖子嘴巴啧啧几下,立马制止我:“你可拉几把倒!还以为你长得帅呢?刚才她去常羽帐篷,是去勾搭常羽来着,被他帐篷里的蛇给吓跑了!”
卧槽,无情!
我刚建立的自信心瞬间崩塌的支离破碎。
许可琴那么耐不住寂寞吗?多撩我几天,说不定我就勉为其难答应她了!
见我不言语,左胖子说道:“她是被小五通鬼缠上了。我推测,她已经忍了七天了,今天必须找人败火,否则晚上要暴毙而亡。”
我吓了一跳,问他啥叫小五通?
左胖子解释,就是俗话说的色鬼,学道的人叫小五通,臭和尚叫它们啖精气鬼。这些玩意儿害人的方式就是不断撩拨人的邪念,让人成天想办事,七天内办不成事就害死人。许可琴也不知道怎么被缠上了,要是今晚不解决,东沙岭是出了名的荫尸地,鬼找鬼,不仅她会死,咱们上山去还不知道会招惹来多少脏东西。
“办完事小五通就走了吗?”
“不是。只能让小五通暂时消停三天。三天后小五通又会缠她,总之,不断地缠她,直到她油尽灯枯为止。要解决小五通,必须先办事,办完事后,乘小五通三天消停的间隙,打诀念咒送走。道爷我今天不方便,所以叫你干脆在上山之前成全许可琴,省得等下孤魂野鬼找咱们麻烦。反正,你也不吃亏。”
我听得目瞪口呆,随即又一想,不对啊,许可琴要真被小五通缠上,需要找人成全,她手下年轻壮汉一堆,早跟别人那啥了,还用得着忍耐七天?
我把疑惑讲给左胖子听,左胖子一脸鄙夷:“你没看到单三叶跟着来了吗?她一个女大学生,大晚上跑山上来,逮麻雀呢?估计单三叶发现这些天许可琴不对劲,盯哨她,怕她吃亏呢!有一个姑奶奶盯着,哪个手下敢乱来?”
结合单三叶刚才讲的话一寻思,还真像那么回事!
我不得不佩服死胖子管中窥豹的分析能力。
今晚许可琴要死了,这单生意就黄了。
钱倒是其次,可九儿姐交待,取尾貂灵是解决我身上憋蛊诅咒关键环节,尽管取完之后该怎么办,她当年并没交待关老头,但我相信,个中必然有机缘。
“要不,让须弥勒试试?”我试探着问。
“他不行。”左胖子摇摇头。
“丑是丑了点,等下我们偷偷劝一下许可琴,保命要紧么。”我说道。
“我是说,他不行,没听明白?”左胖子翻了一下白眼。
我一下石化,左胖子还有这本事,能看出人家行不行。
“那船夫呢?”我继续问道。
“船夫身上有狐臭,小五通不喜欢。”左胖子回答。
五个男人,一个拒人千里之外,一个门规忌日,一个不行,一个小五通不喜欢,符合条件的,好像只有我了。
咋办?
要不从了?
可一想到她身上附体的是小五通,我瞬...
正聊着呢,船夫突然招呼大家,黄河水流向变了,马上出发。
左胖子摇摇头:“糟糕,时间来不及了,看来今晚有的忙活。”
我暗自腹诽,许可琴怕憋宝时出问题,交待要带上个厉害道士。她倒好,自己带个小五通鬼晃晃悠悠出门了。
东沙岭就在河对岸,河水顺流,预计两三个时辰能到。
按书里所说,紫貂在天狗食月之际,会跳上山岗拜月,乘它在拜月,用圈套把它给逮了。看着奔腾的黄河水,我心里既激动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从事憋宝行动,而且事关自己生死。
许可琴上船之后,屁股一扭,坐在我身边,身体斜斜地紧贴着我,没话找话,问我金牙先生怎么没来。
我有点感伤,回答她,金牙临时有别的任务。
许可琴似乎有点瘙痒难耐,媚眼带笑,偷偷地用手摩梭我腿。
我血气方刚,哪里经得起这样撩拨,非常尴尬地往边上挪。
可她身子又锲而不舍地贴过来。
左胖子在一旁,像看戏一样,嘴角戏虐上扬。
小五通讨厌船夫狐臭,可她怎么不去撩拨左胖子和须弥勒?难不成小五通知道一个是道士,一个压根就不行?
我转眼一看,发现单三叶正怒气冲冲地盯着我,眼神恨不得剥了我皮。
老天,这跟我有啥关系?
我无奈地起身,见常羽一个人坐船头,借口找他聊天,赶忙离开许可琴。
常羽冷冰冰的,大家都不爱搭理他。
我过去递根烟给他,他看了我一眼,说不会。
“有人会招鬼。”
常羽看着河水,淡淡地说。
不知道他指的是我还是许可琴,但不管指的是谁,他这句话都让我刮目相看,常羽并不是一个监工那么简单。
我回他:“不足虑,船上有个厉害角色。”
常羽回答:“知道。”
我忍不好奇:“你看得出来?”
他瞄了一眼左胖子:“他一身紫气。”
我一时哑口,不知道怎么接话头,呆呆地坐了一会儿。
后背肩膀突然被人一拍:“你过来一下!”
单三叶站在我后面,俏脸冰冷地说。
她带我到船的另一侧,樱桃小口一开,非常直截了当:“我警告你,可琴姐是我哥的未婚妻。你别打她的主意,要让我哥知道,你会吃不了兜着走!”
敢情这小丫头是来监控自己未来嫂子。
可她怎么就光警告我,不警告一下常羽吗?
难道我和蔼可亲在她眼中倒还成了软柿子?
“美女,你搞错了吧?许可琴是我雇主,我同她只有简单雇佣关系,你啥时候看出我打她主意了?”我非常无语。
“哼!简单雇佣关系?那我问你,可琴姐昨晚为什么约你来酒店?还有,为什么刚才一见面,你就赶我走?你昨晚没敢进酒店,是因为在酒店门口看到我带人拿刀在等你吧!”单三叶话像机关枪一样突突传来。
我突然觉得后脊背发凉。
幸好老子昨晚做了回正人君子,不然今天可能躺殡仪馆了!
可单三叶这些问题我又该怎么解释?
“我如果说……你未来的嫂子被色鬼上身,你会信吗?”我试探着问她。
单三叶瞬间气得满脸通红,胸脯上下剧烈起伏,用手指着我:“你……”
正在这时,船夫突然说:“大家别说话,冷水排到了!”
须弥勒闻言,脸色一变,立马猫身躲进了船舱。
左胖子反而冷着脸从船舱里出来。
常羽,一脸凝重地从船头站起。
住在黄河边上的人都知道,冷水排另一个名字叫—“尸水排”。
单眼皮双眼皮(短篇小说)
张实在穿条短裤,一条腿耷拉在沙发下,另一条腿盘在耷拉着的那只腿上,眼前的茶几上放着一盘猪头肉和一盘花生米,自然还有酒。他已酒至微醺,醉红的双眼迷迷糊糊地盯着正在地上蹲着玩耍的儿子。儿子叫小悦,刚满三岁,此时正专心致志地趴在地上玩手里的小汽车玩具,嘴里不时地吐出一串“嘟嘟”的模仿汽车的马达声。
他的眼神射出的不是作为父亲的慈爱和喜悦,而是一种冷漠、仇视和夹杂着的痛苦。
他突然就控制不住地暴怒起来,声嘶力竭地吼骂道:你“嘟嘟”你妈个屁!吵死了!
那摘掉眼镜后凹陷的眼窝看起来很闹心。
儿子显然是被吓到了,惊恐的小眼睛紧盯着张实在,“哇”地一声就哭了。
儿子的哭声并没有改变张实在对他的冷漠,反而在与儿子那惊恐的小眼睛对视时,尤其是看到儿子那双单眼皮,他一头火“噌”地蹿了起来:你再哭!……老子弄死你这个小王八蛋!
儿子突然就止住了哭声,抽泣着,很委屈、很乖地走向爸爸,一头扎进爸爸的怀里,哽咽着说:爸爸,小悦错了,小悦改。
张实在很冲动地本想一脚把儿子踹开,但他却突然瞬间克制住自己,没有那么做,反而把儿子揽在怀里,撕心裂肺地“嗷嗷”哭了起来。
虽说是酒后的作派,却也真实地暴露出他内心的情感,酒后吐真言嘛。
这令人十分费解与困惑,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儿子这般粗暴呢?为什么一看到儿子的单眼皮就火冒三丈呢?
其实,他最窝心最痛苦的事就是儿子的这双单眼皮。
那还是在儿子一岁多的时候,一天,他抱着儿子坐在小区广场的排椅上,看大妈大爷们跳广场舞。一曲终了,邻居李大妈随着散开的人群向他走来。
李大妈50多岁,脸面保养的要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她着一袭蚕丝红衣,飘洒着一身狐臭味,令他避之不及。
李大妈躬身逗着小悦:臭蛋蛋,认识你娘娘不?你娘娘就住在你家脚底下,你一泡尿就可以把你娘娘家淹了。哟哟,臭蛋蛋,瞧这小胳膊小腿胖嘟嘟的,俺家孩子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哟,这白白净净的,随你妈。哟,看这双单眼皮,怎么就不像你妈的,也不像你爸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大妈的两个“不像”让张实在的心“咯噔〞地沉了一下。
李大妈走后,他仔仔细细地端详起儿子来,“不像你妈,也不像你爸〞这句话始终萦绕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他越看儿子越觉得奇异,越看越觉得陌生。怎么会是这样!他反复唸叨着。
我是双眼皮,他妈也是双眼皮,生出的孩子必定也是双眼皮,怎么会是单眼皮?如果说在基因遗传上有变异,或者说有隔代遗传的现象,那也是不可能的。在家族史上,从曾祖父那辈开始,到祖父,到父亲这辈,娶的女人都是双眼皮,好像这个家族对双眼皮的女人格外偏爱。即使是基因变异出个猴来,也决不会变异出一个是单眼皮的后代。
难道是她?
他一将疑问打在老婆的身上,心就哆嗦了一下。他的思绪努力想着分析下去,却又有另一个念头控制着他不去想,最后又不得不去想。她是不是有外遇?是不是婚前就有相好的……
问题只能会出在她的身上,而且,一定是这个婊子和别人下的种。没错,这是最合理的判断,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想到这,一种被被叛的耻辱感,一种莫名的嫉恨令他痛苦不堪,绝望感使他想要把一切都撕碎。他感到天塌了。
他把卧室的门一锁,一头扑在床上,然后扯起一床被子蒙头盖在身上。愤怒和耻辱紧紧缠绕着他,思绪如麻。他回想着与她的过往及点点滴滴。
他与她的相识是由街道办事处乔主任牵线搭桥。乔主任的身段像是相扑运动员,为人随和,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架子,总爱跟人打个哈哈,背地里人们都管他叫“弥勒佛”。
一天,乔弥勒佛叫住了张实在:小张,昏(婚)了吗?
张实在赶紧回报:报告领导,我还没昏(婚)呢。
乔弥勒佛呵呵呵地乐着,随后认真地说:城西办事处刚来个小妞,人长得跟仙女似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
那行,那行。一向不善言笑的张实在,说起话来舌头都发硬,跟领导说话更是拘谨。
乔弥勒佛的话,他只当做是玩笑,并没有往心里去。没想到乔弥勒佛还真的给他当了媒人。
她叫乔小慧,原是市歌舞团舞蹈演员,歌舞团因经济原因难以维持宣布解散,乔小慧通过弥勒佛的关系调到了城西办事处任职员。
他第1次见到她的时候,那双躲藏在眼镜片后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直勾勾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女孩,像是傻掉了,忘记自己相亲的身份。
女孩身材窈窕,气质高雅,皮肤白皙,一一张瓜子脸配着一双灵动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尤其是那双眼皮双得让人看得心旌摇荡。
女孩莞尔一笑:哪有你这样看人的。
他的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可人儿就是他的相亲对象,他感觉与她有着无法言说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他十分的不自信,甚至有些自卑。虽然他还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
然而,爱情就是这么奇妙,它常常忽视了不可能而让一切变得可能。他居然和她走到了一起。
……他和她站在齐长城上,舒爽的山风阵阵吹来,撩起她的长发随风漫舞。漫山的红枫叶随风“刷刷”摇曳,偶尔响起归巢鸟儿的鸣叫和时断时续的蝈鸣。夜色缓缓降临,月牙越显明亮,远处高楼大厦的身影渐变模糊,不时弹跳出一点一串灯光。他和她双目对视,眼神里荡漾着青春的激情和爱情的甜蜜,他忍不住把她搂在了怀里,她颤抖的身子顺从地迎合着他。他吮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气,沉浸在那颤抖的、滚烫的身躯涌溢的蜜意里,他猛地吻住她的唇:慧,嫁给我吧!她没有言语,也无法言语,只用更猛烈的吻回应着他,滚烫的热泪涓涓流出,浸润着他的脸庞,他的心……
每每回忆起他们的爱情及婚姻生活,他非常知足,内心是满满的幸福感。他感谢上苍赐予他这么美妙的礼物,让他享受到了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而此时此刻他蒙在被子里想起这一切,心犹如锥扎般的疼痛。他流泪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美好的回忆都即将失去。他十分清楚他将面临的结局,如果这个孩子真是她与别人所生,那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即将解体,他将妻离子散。结果只能是这样,因为他无法忍受、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卧室的门被敲得咚咚作响,门外传来妻子的话音:你在里面干嘛呢,开门啊。
他本能地坐了起来,他已习惯于对妻子的顺从。他想了想:证据呢?没证据凭什么这样想。他感觉自己的一腔愤怒在面对自己妻子的时候显得那么脆弱。他乖乖地打开了房门。
小慧走了进来,他无语地回坐床上。小慧见他一副颓废的样子,关心地问道:怎么?你不舒服?
他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只是口气有些冷淡: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小慧很体贴地上前试了试他的前额,说:你没发烧吧?
每日清晨上班之前,乔小慧照例提前2个小时精心梳妆打扮自己。若在平时,他根本不在意这些,女人嘛,爱个臭美也是正常的,天性如此。而今天,乔小慧一起床,他就从浅睡中醒来。
自从有了那个窝心事之后,他几乎每夜都失眠,只是在后半夜天亮之前的二三个小时浅睡一会儿,稍微有点静,哪怕是儿子翻个身,他都会惊醒。窝心得他睡眠不足,没精打采,工作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还让一向严肃不起来的乔弥勒佛很严肃地在晨会上指名道姓地尅了一顿。幸好没扣奖金。
晨解时,过客厅,他看见乔小慧正专注地对着梳妆台上那面镜子描眉画眼。她像是看到他的身影,冲着镜子做了个鬼脸,抿了抿朱唇,笑眯眯地说:怎么样,你老婆,漂亮不?
若在往常,他会极尽谄媚之功,给她个甜枣:老婆你太美了!而此刻,他看她就满心的厌烦,心里骂道:抹得跟个鬼似的。他只是鼻子“哼”了一声,进了厕所。
陈晓慧只是语气平缓地说了句:你哪来的这些毛病。继续摆弄着她的头发。
等张实在从厕所出来,乔小慧起身说:老公,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办公室的老郑说今天要请客,说是他儿子在市奥数比赛时拿了个一等奖,庆贺一下。
张实在只是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他突然转过身,很突兀地问了句:在哪个酒店请客?
哟,快到点了。在“小情人”酒吧。说着,她忙乱地取下挂衣架上的橘黄色小包包,“噔噔噔”地走出门。
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他重又倒在床上。他咂摸着小慧刚才的话,心里又犯了嘀咕。“小情人”酒吧,结婚前,他跟小慧去过几次,熟悉那个地方。那里都是情侣座,老郑摆贺席,一桌至少也得七、八个人吧,怎么会摆到那里去,那么多人容得下吗?难道是他和她两个人?想到这儿,他又头冒火。他对老郑多少有些了解,老郑就是从他们总办调到城西办事处的。这个人为人不错,但就是有个毛病,动不动就好在女人身上搞点小动作,占点小便宜。办公室的女员工都很烦他这点。那么大年纪的人也没点节操,心理是不是有病?有一次,老郑摸了人家小姑娘的臀部,小姑娘气呼呼地哭着喊着嚷着将他告到乔弥勒佛那里。幸亏没有告到警察那里,若是告到警察那里,老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搞得乔弥勒佛很是挠头,只好把他调到城西办事处。
一个是暧昧的“小情人”酒吧,一个是糟烂的郑老头,把二者联系起来想,他心里的醋劲儿就“蹭蹭”地往上蹿。他也宽慰自己,想那么多干嘛,但又对乔小慧实在是没有信心。他就像是一只护食的狗,吃食时是绝对不容忍别的狗抢食。强烈的嫉妒心折磨着他,使他做出决定:晚上一定要去看个蹊跷。
下午下班后,他去父母那儿看了一眼小悦,回到自己家,简单吃了两口,然后骑上摩托车,向“小情人”酒吧驶去。
来到“小情人”酒吧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小情人”酒吧店外灯火闪烁,宽敞的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他不知道将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心里盘算着,如果是群聚,那是他最希望的结果;如果真是他们俩人“庆贺”,那就要狠狠地教训他们。久抑的耻辱、痛苦、愤怒和妒嫉之情酝酿出一股强大的报复心。临来时,他还特意地揣上一把水果刀,以备不时之需。
他贴着墙根慢慢地走近“小情人”酒吧,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墙,他居然看见大厅里小慧和他的同事们正围坐在圆桌周围有说有笑地吃喝呢。他没料到“小情人”酒吧内部已经做了重新布置。他深深地舒了口气 ,浑身感到一阵轻松。他转头向马路对面走去,身影消失在黑暗里。
晚上快10:00时,小慧走进了家。她一身酒气,身子有些摇晃,看来酒喝的不少。
她眯着醉眼,对张实在质问道:你盯我梢?你今晚去“小情人”了?
我闲得慌。他这话说得没什么底气。
我有同事看到那人像你。小慧说完,便也没听他反驳,晃晃悠悠走进卧室。一会听到她的呼噜声。
借着从卧室上窗透进的大厅光线,卧室才显得不那么黑暗,她蜷曲在床上,他站在她头部位置的床边,怔怔地望着她,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她只穿条粉红色内裤,几近赤裸,安安静静的样子。他望着她洁白如玉、散发着青春活力的驱体,想着这个活生生的人给他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一种强烈占有的欲望充满整心间,他不想失去她,只想好好地守护着她。但他一想到那双单眼皮,一想到她因此而对他的背叛,心如刀割般地“滋滋”作痛,一种绝望感让彻底崩溃了。他觉得什么都没有了,活着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他突然目露凶光,一可怕的念头冒出来:活着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一块死球算了!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想要紧紧地扼住她的脖子,让一切痛苦、屈辱和种种烦恼都从此消失。然而一瞬间,他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再也无法挽回的画面,那细若游丝孱弱的理智却顽强地阻止了他的一念之差,也许多年文化的滋养及生的欲望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底线,拯救了他。我是不是昏头了!我是不是昏头了!他急忙退出卧室,大汗淋漓地站在客厅里,一任汗水往下淌。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直视的是太阳和人心。
他绞尽脑汁,试图解开心中一直折磨着他的那个死结。既然认定事情出在她身上,那证据呢?什么事总该讲个证据吧。
他想偷偷带孩子去医院做个DNA鉴定,可是,左思右想总觉得不稳妥。万一事情泄漏,且不说结果如何,单就这种行为,怎么向父母解释;传到单位,他的这张脸怎么办;至于对乔小慧来说就等于向她摊牌了。如果结果孩子是自己的,他要承担风险;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离婚是必然,但是到底是怎么的后果难以预料,他一时还想不清楚。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到万不得已不出这张“王炸”。
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向单位领导借口说要去外调,骑上摩托车向市中心奔去。此地距离市中心约30公里,半个小时的路程。他此程的目的是去市图书馆找乔小慧的闺蜜沈媛媛。沈媛媛也曾是市歌舞团舞蹈演员,现在市图书馆工作。他想从沈媛媛那里获取一些想要的信息。
他走进图书馆,上了二楼的阅览室,一进门就见沈媛媛正端坐在工作台前专注地看着书。阅览室一排排桌椅上空无一人。
她抬头时的目光正好与他的目光相遇,他看出她眼神中的疑惑和惊讶,他微微一笑,刚想礼节性地打招呼,却被站起身的沈媛媛先声夺人:哟,是张哥呀,这是哪阵风把你给吹这儿来了。快坐,坐。
他一向对她高八度的嗓门很不适应,让你感觉在她面前必须低调。二年前在春节聚会上,她那高八度的嗓门几乎让他晕掉,而且还是紧挨着她座位。
我这是来市里办点公事,正好路过你这里,过来看看你。
哎哟,谢谢,谢谢!谢谢你来看我。没想到你还想着我,小慧知道了不会吃醋吧,哈哈哈哈……
他脑子转的够快,立即忽悠道:吃什么醋,还喝酱油呢!当年在歌舞团,你男朋友追小慧,你也摔过醋坛子?
沈媛媛听到这话楞了一下,瞪圆了眼睛急忙辩解道:你这是听谁胡唚的,没影子的事。当年我们歌舞团有规定的,不允许男女生谈恋爱,谁要是逾越了这根红线是要被开除的。当年我们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年纪,个个都是黄花大闺女呢。哪像现在的女孩子谈个恋爱那么随便。
那小慧当时就没个男朋友?
这句没头没脑的问话,让沈媛媛足足盯了他有三秒钟,她憋不住地“扑哧”笑了:哥,这话怎么问得有些探子的味道。小慧真就有男朋友,哪轮得到你啊!要个头没个头,要模样没模样,要钱没钱,纯正一个小公务员。小慧嫁给你,算你祖上积德烧高香了哈哈哈哈。
她连挖苦带嘲笑的玩笑话,让他颇感尴尬。他本想坐下来和她好好地谈谈,却让她不经意间把他想得到的信息都捅给了他。他觉得没必要再问什么了,就冲着她那张嘴,搞不好还要挨一顿抢白。
他胡乱应付了二句,起身告辞。
路上,他在想,那乔小慧到底是跟谁有了这孩子呢?脑子里乱哄哄的,没个头绪。
一进门,他一眼就看见乔小慧铁青着脸正怒视着自己。他预感到事情不妙,一定是沈媛媛一个电话把他给卖了。
她把孩子放到沙发上,“刷”地站起身,指着他骂道:张实在,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出去吃个饭,你去盯梢!你还不承认,你过马路时我同事跟你走个对面,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屁都不放一个只管低头走。你今天闲得难受又跑到媛媛那儿刨我的老底。你那破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结婚以来,他从未跟她吵过嘴,处处依顺着她,凡事都让她三分 。这并不是因为怕她,而是因为爱她,因为爱而包容呵护她。望着她气势汹汹的样子,反而激起他一腔怒火,所有的委屈和耻辱一涌而出。他突然咆哮道:你怎么不问问自己?你难道心里没数吗?
她打了楞怔,质问道:我怎么你了?你说!你说!
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因为激动,他满脸涨得彤红。
你说!你说!你说呀!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咱们就离婚。她歇斯底里地喊着,上来就揪住了她的衣领。他几乎丧失了理智,甩手给了他一耳光。
啊,你打我!女人“哇”地哭起来。
她二话没说,简单拾掇上几件衣服,甩门而出。
她回了娘家,一住就是半个月。张实在的娘几次催他,要他去老丈人家把她接回来,他就是犟着一股劲儿,说:由她去。
他把茶几上剩下的酒都干了。儿子也不哭闹了,仍旧蹲在地上玩他的小汽车玩具。他看上去醉得如滩烂泥,但心里还明白。这时,门响了,乔小慧推门走了进来。她着一身粉红色的时装,打扮的像个模特。小悦见到妈妈,跑过去搂着妈妈的腿,“哇”的委屈地哭起来:妈妈,爸爸刚才打我。
乔小慧瞪了他一眼:你拿孩子撒什么气,就这点出息。她哄小悦:别哭了,宝贝,等会儿妈妈带你去欢欢游乐园玩去。
她在另一边的沙发上坐来,盯着张实在,一会儿,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她心气平和地说:张实在,我们离婚可以,但你要让我离个明白,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对我。
他冲她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二声,借着酒劲,乜斜着醉眼说出心里的那个死结:我为什么?我问你,小悦的眼为什么是单眼皮?你给我解释。
她沉默了。沉默片刻,她走到桌前,打开抽屉,从一本相册里抽出一张相片,递给他,说:你看吧,这是我15岁时的照片,也是单眼皮。我在18岁时,进歌舞团之前割的双眼皮。对不起,我没早告诉你。
他仔细地看了看,那双单眼皮跟小悦的一模一样。
他其实并不在乎她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只是那颗碎落一地的心,是否还能复原。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