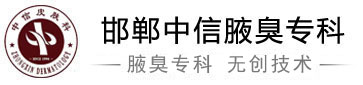小说:他被狐妖所截,却缕缕战败,同道中人意欲出手相救
马天成被七尾红狐的一句话,惊得目瞪口呆,没想到隐身法诀在这个时候突然失效了。此时的马天成全身上下,只有右脚显露了出来,那一窝妖狐嗤嗤直笑,红霞手一招,长袖一抖,一道半红半黑之气吐出,把天成身上的符箓吹得满天飞。
咳咳,这七尾红狐的狐臭还真是厉害,一下就把马天成身上的隐身法诀给破了。马天成抽出随身宝剑,正欲以死相拼,忽觉四肢无力,暗叫一声倒霉。这红狐妖女的狐臭,居然震散了他体内本就不多的灵气。
“咯咯~!”红霞嗤嗤一笑道:“我本以为斗天门徒有多么了不起,怎地你的修为这么差,连飞剑也不会?马天成,今晚你可跑不了了!”
马天成见这骚狐狸辱及师门,心里又羞又怒,脸上却嘻嘻笑道:“我马天成入斗天门才不过两年,修为浅薄,被仙狐姐姐笑话了,只是小子不知何时得罪过姐姐,劳烦姐姐变化作我娘的模样,兴师动众来抓我?”
红霞儿本就喜欢天成长得俊俏,又听他伶牙俐齿,心里更是荡漾,娇声道:“这事儿从头说来,也是你和我白灵儿妹妹有缘。一年前,我妹妹云游至此地,正逢凝结妖种、应对天劫的紧要关口,全身法力所剩无几,化作原形,差点就被马家庄的三个猎户所杀,是你这小修士,将我妹妹藏匿起来,才助她逃过此劫。”
一年前?天成暗自忖度了一会儿,才记起当时自己好像是救了一条白狐,扭头看了一眼娇憨动人的白灵儿,“你、、你就是那条小白狐?”
白灵儿走到天成身前,俯身下拜,“白灵儿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原来这白灵儿为了报恩,打探到县城周宅,见了周玉莲,变化作她的摸样,来马家吊唁。趁机把天成引入白狐洞中。
天成口称不敢,将白灵儿扶了起来。岂料那白灵儿为了报恩,竟然愿意以身相许。天成顿时头大,这类狗血桥段,在坊间市井,也有不少说书人讲过,三百年前就有一个姓许的书生,与一条修炼了一千八百年的白蛇做了夫妻。只不过。马天成不曾想自己也有此等‘艳福’。
“咋地,你不愿意!”见那马天成推脱不肯,红霞儿身上顿时妖气冲天,妖气之上有一圈红光笼罩,气场极为强横。
“你这臭小子,我妹妹想要嫁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居然推三阻四,如此不知好歹!也罢,本仙狐就把你吸成第四具干尸!”
红霞儿抛起一块血色手帕,默念法诀,手帕飞到半空,越变越大,罩在马天成的头顶上。这‘锁魂手帕’可是她刚刚炼制不久的法宝,已经吸干了三个男人的精血魂魄,等吸满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到时候不管是人是妖,是魔是道,只要被手帕的红芒罩住,便如同没了魂魄的人偶一般,任红霞儿摆布了。
天成身上的保命符箓,早被一阵狐臭妖风吹得七零八落,体内灵气又被那该死的狐臭震散,动弹不得,只觉这手镯罩在他的头顶上,眼前尽是裸女幻象,耳边奏响淫靡之音,其真实度极为逼真,马天成本就不牢固的道心,受到了严重挑战。
“红霞姐姐,莫要伤了他!”白灵儿见红霞儿起了邪心,心下大急,素手一指,袖口里飞起一道白绫,瞬间暴涨到百丈开外,把那锁魂手帕的红芒团团围住。
白灵儿手一收,白绫裹着锁魂手帕,卷进了袖口之中。红霞儿没能把天成吸成人干。恼恨白灵儿。“妹妹你好没良心,姐姐为你出头,你却用‘乾坤白绫’收了我的法宝!”
马天成没了锁魂手帕的束缚,回过神来。心中暗骂:红霞儿你个骚狐狸,我不娶你妹妹,关你什么事儿,我看你哪是为了替你妹妹出头?你分明就是想把老子吸成干尸!
心中虽然不忿,可这两个狐女的神通却让天成胆战心惊,这两个狐女妖法厉害,只怕师父来了,也不见得能收服他们。
就在马天成思索着如何躲过这场桃花劫之时,一声闷雷!不远处的天边滚着大团黑云,黑云之上,站着一个黄袍修士,看面貌五旬上下,头束高冠,手握拂尘,背插一口紫金飞剑,不怒自威。
黑云之下,隐有电闪雷鸣,十二名年轻一些的修士侍立在年长的黄袍修士的周围。
“师祖,前方不远处有两团妖气,一红一白,看起来是两个有些修为的妖怪,容金莲下去将它们收服,可好?”
见唯一的女徒孙开了口,黄袍修士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你这妮子口气不小,那两个妖怪都是炼成妖种的狐女,修为均在你之上。嘿嘿,三百年不上斗天峰,没想到苍松子门下,尽是这等贪恋狐媚,道心不坚的货色!”
这时,一个黑袍修士眯了眯眼,上前讨好道:“下面那个修为低微的小子,应该是斗天门的第三代弟子,嘿嘿,此次苍松子请师尊上斗天峰,论剑斗法,金莲是我徒儿,也是斗天门南宗的第三代,师尊何不传些道诀法宝给金莲,让她收了下面的两个狐妖,救了苍松子的徒孙。”
那年约二八的女修士娇笑道:“苍松子的徒孙如此不济,连两个妖狐都打不过,莲儿若能替师祖收了这群狐妖,救了苍松子的徒孙,岂不是说明师祖的道法修为,远胜于苍松子?”
黄袍修士听了哈哈大笑,从腰间解下一皮囊,取出一张符箓,五颗剑丸,交与金莲手中。“金莲儿所言甚好,甚好!附耳过来,我传你一道法诀,定能破了那两个狐女的手段。”
原来那黄袍修士,也是斗天门徒。五百年前,玄灵大陆的修真界出了一个千年一遇的绝代高手,此人一身道法精妙绝伦,制器、炼丹、画符等种种手段也是无人能及,因其在斗天峰上开宗立派,被世人尊称为‘斗天老祖’!
斗天老祖座下真传弟子,仅有五人,苍松子、赤金子、火龙子、水妙子、土玄子,五人各有所长,被天下同道尊称为‘斗天五子’!
这位黄袍修士,就是现如今斗天门掌教苍松子的小师弟,土玄子!
三百年前,斗天老祖在数百徒子徒孙面前,飞升永生界,成为玄灵大陆修真界,成功证道永生的第一人!
斗天剑派的声名威望,也因此更加显赫,为天下玄门道宗之首!而斗天剑派的镇派之宝-《斗天仙典》,也成为修真界中人梦寐以求的三大奇书之一。
本来,苍松子和土玄子是一对关系非常要好的师兄弟,但是有一天,当时身为斗天剑派藏经堂首座的土玄子,得知了惊天之秘,一切就都改变了。
原来《斗天仙典》只是斗天老祖留下的一个幌子,除了《斗天仙典》之外,斗天老祖还写下了一本《成神日记》!
这本《成神日记》,是斗天老祖用他自己的仙皮、道骨,祭炼而成的虚神级法宝,里面记载了斗天老祖成功避劫、齐天飞升的心法诀窍,只有具有大神通、或者身具大机缘之人,才能参透这本《成神日记》!
千万年来,玄灵大陆上的修士千千万万,其中少数天资纵横的修士,能修炼到道种、仙基的层次,而修炼到避劫这一层的修士,更是万中无一,天下罕有。
很多天资超绝。一身修为天下罕有的修士,都死在了无穷无尽的大天劫之下,但能避劫成功、齐天永生之人,只有斗天老祖一个!
与能够成功避劫、齐天永生的《成神日记》比起来,世人梦寐以求的、记载了斗天老祖一生所学的《斗天仙典》,又算得了什么?
可斗天老祖,瞒着其他弟子,只把《成神日记》传给了苍松子一人,土玄子当然不服!他的道法、修为都比大师兄苍松子略胜半筹,《成神日记》凭什么归苍松子一人所有?
人之心魔有三种:贪!嗔!痴!心魔一起,土玄子就有了独吞《成神日记》的念头。岂料苍松子早有察觉,联合师弟赤金子、火龙子、师妹水妙子,将土玄子打成重伤,逐出斗天门!
只可惜,苍松子在与土玄子的拼斗中,只抢回上半卷《成神日记》,下半卷《成神日记》,依然在土玄子手中!
土玄子被逐出师门之后,性格更加狂放不羁,干脆在岭南黄鹤谷自立门户,自称黄鹤真人,开创斗天南宗,与苍松子等人分庭抗礼两百年。那黄鹤真人道法精绝,天资、修为堪称斗天五子之首,两百年来,斗天南宗在修真界也算声名赫赫,频频与北宗争斗。南宗弟子虽少,但无时无刻不想把太白山上的北宗弟子压在身下,让黄鹤谷的斗天南宗成为斗天剑派的正宗!
此番,黄鹤真人重登太白山,皆因苍松子和他的修为,均到了避劫层,两人为了参透《成神日记》中躲避天劫的诀窍,于是决定在三月初七,南北二宗,太白山上,论剑斗法!胜者可获得对方手中的半卷《成神日记》,成为斗天剑派的正宗!
《沉默》的姐妹篇,人究竟在向神渴求着怎样的爱与救赎?
《死海之滨》为远藤周作继《沉默》结束七年后又一部探讨宗教与信仰、神性与人性进行的长篇小说。故事在双重时空下展开,由“朝圣”和“群像中人”两条叙事线索交替进行。现代的“我”在耶路撒冷追寻耶稣曾经的足迹,“新约”时代六个身份各异的人物见证耶稣的献身。从“母性的神”到“永远的同伴者”,一段追寻耶稣真实面貌的朝圣之旅,一部探寻爱与信仰的长篇力作。人们究竟在向神渴求着怎样的爱与救赎?神应该是用仪式和恐惧供奉起来的吗?
作者简介远藤周作(1923-1996),日本作家, 1955 年凭借短篇小说《白种人》获芥川奖。 1995 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与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等同为战后日本文坛的“第三代新人”。
远藤周作出生于东京,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法文系。幼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往中国大连,回国后受洗,战后前往法国里昂大学进修法国文学。 1955 年短篇小说《白种人》获芥川奖。 1966 年《沉默》获谷崎润一郎奖。 1995 年远藤周作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
他被称为日本信仰文学的先驱,致力于探讨日本的精神风土与基督教信仰问题,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罪与罚”的沉重思考。
译者简介田建国,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现任杉达学院日语系副主任、教授、上海民办高校日语协作组副主任,著有《日中俳句往来》《翻译家村上春树》,主要译作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形成》《罗马人的故事》《希腊人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忘れ難い歳月記者たちの見た中日両国関係》(中译日)等。
书籍摘录一 耶路撒冷(节选)
我在耶路撒冷市僻静街道的一个像仓库一样的饭店里等着户田。他是我学生时代的朋友,已经好久没见了。他如果收到了我从罗马寄出的明信片,应该知道我今天抵达了这个国度。
房间里铺的东西上到处都是磨破的洞,像是得了皮肤病。拧开浴室的热水龙头,便会传来汽车挂错挡般的声响,淌出锈黄色的温暾水。洗脸台上还粘着两三根前面客人留下的栗色毛发。打开西服柜,只见两只衣架空荡荡地挂在里面。望着这些,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空虚的午后,自己已经身处遥远的国度了。
我请刚才帮我搬运行李箱的阿拉伯年轻人送威士忌来,他却一副为难的样子摇头道:
“安息日!”
在以色列,根据犹太教的戒律,从星期五下午开始便是要严格遵守的休息日。他们告诉我,这时商店会歇业,也不能喝酒。酒是喝不成了,我把椅子放到窗户边坐下,抽起了皱巴巴的超淡型烟卷。离开日本时我带了一条这烟,现在也只剩两三根了。
窗户底下是一片满是石子的空地,对面有条路。这路似乎与希腊和意大利小城的路并没有多大差异。略显奇特的是,前面像花岗岩的建筑是用粉色石块堆砌而成的。
时而有人走过。虽说是四月,这里的气候已经跟日本的初夏差不多了。许是因此,男人都只穿长袖衬衣而未穿外衣。女人的衣服同我一路走来的罗马和巴黎等地相比,真是寒碜得太多。开过去的公共汽车也破旧不堪,也许是因为战时的缘故吧。但如果是在打仗,这又是哪门子的仗呢?两个小时以前,我从特拉维夫机场来耶路撒冷,沿途从车窗里看到,耀眼阳光下的橄榄地、白色的村落和把椅子搬到路上歇息的农民。那风景可是一派悠然,是我这个了解战争时期日本的人所想象不到的。
闲来无事,我把从收银台要来的市区地图在膝上摊开,愣愣地看着。地图上,耶路撒冷被分为耶路撒冷老城和新移居的以色列人建设的耶路撒冷新城,这家饭店的位置上标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箭头。可能是隔壁房间在放热水,隔墙传来了痉挛似的金属声响。午后炽烈的阳光照射在肮脏的墙壁上,我感到了困意,不知不觉做起梦来。
(肮脏的墙壁上有好多拍死蚊子的印迹,墙与墙之间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晾晒的衣物散发出馊味。房间面对着校园,那里传来学生练习拼刺刀的叫喊声。听着那声音,我在睡梦中模模糊糊地感到,啊,那是我自己毕业的大学的宿舍。在这所基督教学校里教我们的神父和修道士们那阴暗禁欲的面孔,跟狐臭味一起泛起。最后出现了一位戴着圆眼镜的学生,像户田却又不是户田。圆眼镜学生像要查找什么似的把我的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用窥视般的眼神说道:
“这所大学的神父虽说是同盟国的外国人,但不知道他们暗地里都在做什么。也许有间谍行为啊!”
出于软弱,我点头同意他的话。)
远处发出了摩擦的声音。那不是隔壁房间放热水的声音,而是电话响了起来。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听筒放在耳边。
“我是户田,现在就在这家饭店的楼下。”
我记得学生时代住四谷宿舍的时候,户田说话的口气没这么客气,有些咄咄逼人。那时,东京也同样处在战时,但却阴沉得同现在的耶路撒冷完全无法相比。我们从勤劳动员的工厂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一起喝杂煮粥,那是用配给的红薯和一点点米做成的稀汤。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放下听筒,脑子里忽然回忆起,我们过去的二十多年岁月,感觉就像在很久以后观看以前旅行过的国家的明信片一般。
在难以称得上是大堂的地方,前台后边有一张肮脏的椅子,户田微微驼着背,面朝里坐在上面。我没有马上靠近他,从远处偷偷望了他一会儿。他有点驼背,头顶中间已经严重谢顶。
尽管他头发已经稀疏,眼角长出皱纹,但转过头来时的表情却一点都没有变,就连头上紧绷的烫伤疤痕都会唤起我的记忆。那是他小时候被奶奶不小心打翻的开水烫伤后留下的。
“累了吧?”
“在飞机上已经睡够啦。”
我们见外地说了一会儿不痛不痒的话,相互试探着漫长岁月中对方已经改变的地方。我为了看清他递过来的名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眼镜,这时户田的面颊才浮出了不带隔阂的讽刺般的微笑。以前他就喜欢发出这种讽刺般的微笑。
“我们都老啦!”
拘束一下子消除了,两个人用往日的语气聊起那帮子同学和老师的消息。
“你还记得 A 吗?他在菲律宾战死了……”
“那家伙有怪才,每次我们饿瘪肚子的时候,他总能从哪里弄些个吃的东西来。”
两层宿舍那积满灰土的走廊、贴着“禁止使用”纸片的厕所和挂着洗过衣物的房间,那些形象伴着各自的气味在我的脑海中苏醒了。小伙子们住的房子里,到处都充溢着体臭。有时候,在这气味中还会出现外国神父那带着另类体臭的身影。那时,他们不断受到警察的监视,在校园和校舍里走路都是一脸阴沉,蹑手蹑脚……
在表情阴暗的神父中,有人在战后得到美国援助建立了基督教广播电台,还有人在战争末期去了广岛,遭遇原子弹爆炸,后来死掉了。在我和户田回忆同学们的时候,那些教授我们德语和哲学概论的神父们的面孔,也一张接一张地浮现在我的心头。
“大学时的那帮人里有人来过这里吗?”
“内田来过一趟,别的没了吧。他是跟视察基布兹的项目团队一起来的。我们只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没能好好聚一下。”
“他现在好像在大阪。我跟他也好久没联系了。”
我们谈话的措辞一点点地回到了往日亲密时的那样。
“以色列这国家,没啥事儿的话也没那么好玩。大家不会特意来……所以,你从罗马给我来信时,我还有点惊讶。可你是怎么会想到要来以色列的呢?”
户田的问题让我有点疑惑。我一开始的旅行计划中根本没有打算来这个国家。当时是打算与同行的电视台的人在伦敦、巴黎、马德里等地转一圈后,一起乘坐绕道北边的飞机回东京的。可是到了罗马,我突然起意,要跟一行人分手来耶路撒冷。可是,要同户田说清这些,就像让我用一句话说清楚自己过去的一切那样困难。
“我很长时间没有读到你写的东西啦,这里难得弄到日本杂志。”
户田这样说,并没有讽刺的意味,这反倒伤了我的自尊心。
“不读才好啊。让过去的朋友读,太难为情啦……为了赚生活费,最近写的尽是些无聊的东西。”
我最清楚自己的精神堕落。在郊外盖房、买车,写了几本不断再版的娱乐小说。这些都像是在证明自己的堕落,想起来常常会生自己的气。
“你来这里已经几年了?”
“九年。”
“学习怎样?”
“我搞的是希伯来语和《圣经》学,回到日本也没法改行。”
这说法貌似自暴自弃,却隐含着自信,听上去还有鄙视我这个写无聊小说之辈的味道。从二十多年前住在学生宿舍的时候起,户田就老是想教诲别人。尤其是那时他主动接受了洗礼,跟非信徒学生争论时,总是用鄙视的口气辩驳别人。
“我经常在考试前请你帮我弄外语呢。”
“是吗?”
“你从这个国家的研究所领着奖学金吧。”
“早就停了,”户田表情有点苦涩,“现在,在这里做点联合国的工作糊口。”
“没有回日本的想法吗?”
我突然想起听谁说过,他十多年前婚姻失败,同妻子分居了。在大堂窗户射进来的阳光里,他眨着眼睛摇了摇头。我自己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就开始回避与那所大学里的神父见面,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不再去教堂了。
有时候,我会在冬风穿堂吹过的车站站台上,从年末繁华的街上碰到的同学那里,听到些户田的消息。他在名古屋基督教会的女子大学教书,研究和我等毫无关系的《圣经》学。别人告诉我这些,我却只是有一种愧疚,并没有特别想见他。所以,要不是在巴黎听到一位做商社职员的同学说户田住在耶路撒冷,让他给我看了那本旧的同窗会名单,我也许就想不到在耶路撒冷找户田帮忙了。
“去哪里呢?不巧得很,今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这片地区连商店都关了门……”
出了饭店,他自顾自地朝停放在阳光照晒的人行道上的雷诺车走去。
“以色列这个国家太正经,不像贝鲁特,连个玩的地方都没有。”
“那种地方我可没兴趣啊,老啦!”
我说“老啦”的时候,户田的嘴微微一撇,露出浅浅的微笑。我还记得他的这种笑。学生时代,考试前我向他请教德语翻译时,只要我回答得不对,他就会经常露出这种苦笑。
“所以,整个以色列都一样。这耶路撒冷也只有两个方面可看,旧耶路撒冷和新耶路撒冷——也就是当代的以色列和《圣经》里的耶路撒冷。”
“新以色列?”
“就是正在打仗的以色列。基布兹和沙漠的开发、洛克菲勒财团,这是第一。第二……”
“你啊,一点都没变,”我忍不住苦笑道,“就跟过去一模一样。”
“怎么讲?”
“你以前讲话就是这个样子,非甲即乙,非乙即甲。我想起了你在宿舍经常跟别人争论是否存在神时的样子。你说,动者必有使其动者,若无使其动者则动者不动。所以,追溯最初的使其动者,神的存在便不可否定……”
“说过那种傻话吗,我?”户田故意把脑袋一歪,“可你不是也没变嘛。现在来这个国家干吗呢?”
我感到了和刚才一样的困惑,便不作声。的确,我也没怎么变。我与大学时才改宗的户田不一样,我是小的时候受的洗。我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而是由父母选的宗教。这在日后成了我的心头重负,竟数度欲弃。可是弃了之后自己会变得怎样?又能做什么?我没有自信,总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在罗马我会突然起意去耶路撒冷,也许是想这次解决这个矛盾的心态起了作用。
“上了年纪啦。因为上了年纪,心里才会想朝圣一下耶稣的足迹吧。”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内心,暧昧地回答了一句,“与其带我去看沙漠的开发,不如让你带我看看耶稣在世时的遗迹,这还容易懂一些……”
“你啊,还是放不下他吗?”
路两边可以看到放下了百叶门的女装店和钟表店。因为是犹太教的安息日,路上行人稀少。唯一开着的是一家电影院,广告牌上画着扮成骑兵的约翰·韦恩的大头像,有五六个犹太青年在售票处前排着队。
户田说“还放不下他吗”的时候,声音里有戏弄的语气。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从什么地方听说,我已经很久不去教堂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的信仰就像房檐上的雨水槽一样已经被腐蚀掉了,耶稣的形象不过像这块约翰·韦恩的广告画一样,成了俗气拙劣的摹写。
“怎么说呢?我自己也不清楚。”
户田又泛出了讽刺的微笑。我倏地想起了几年前开写,结果藏到抽屉深处的一份稿子。我原本是想写耶稣与他的一个爱耍小聪明、经常撒谎的懒惰门徒的故事,而那个门徒就是我自己的投影。写作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我感到我已经放弃了耶稣。
题图为电影《沉默》剧照,来自:豆瓣
小说:他留书逃婚,一心向道,却遇到一窝狐狸精,险些丢命
马天成方回家,便遭到老娘数落,他喃喃自语:“真是奇哉怪也,娘你不是晕死过去了么,怎么现在神采奕奕,对我越骂越精神了?”马天成怀疑老娘装病,诳自己回来成亲。他偷看周玉莲,周二小姐玉面飞红,低头不敢看他。
“逆子,想你亲娘早点死么?”张氏揪着马天成的耳朵,却不使劲,末了,她还在马天成的耳根处轻摸了一把。马天成大奇,母亲张氏向来庄重,虽然极是疼爱他这个独子,却从未有过这等亲热的举动,今天这是怎么了?
马天成望着张氏,就见她肤白胜雪,穿着一袭月白宫装长裙,领口斜斜的直抵胸前,雪肌隐现,一个碧玉环子为纽扣,在腰下裁开。瞧起来与两年前一般美貌,只不过,气质似有很大不同。
“张姨,你就别骂天成哥哥了嘛~!”周玉莲突然开口,替马天成求情。张氏咯咯笑道:“好,好,我且回房休息,你们聊。”张氏摇曳身姿,瞧起来风情万种,妖冶动人。在擦肩而过之时,马天成居然闻到一丝淡淡的怪味。
马天成胡思乱想,只听周玉莲柔声低语:“天成哥哥,你是不是在斗天剑派另有心上人了?”
“玉莲妹子别瞎猜,绝无此事!”马天成摆手否认。周玉莲双眉如画,眼波似水,朝马天成瞟来。“那天成哥哥为什么留书退亲?”
周玉莲上前逼问。天成心里有愧,连忙缩身后退,又觉有些丢人,心中定了定神,便把自己有志求仙问道,不愿耽误她一生的因由与周玉莲老实说了。说完马天成便低头不语,只想着任凭人家玉莲小姐打骂一通,也好还了些孽缘情债之后,回斗天剑派潜心修道。
半天不见动静,天成悄悄抬头,却见周玉莲媚眼如丝,一张俏脸离他的鼻孔只有寸许。酒窝深深,眼波仿佛要滴出水来,勾得天成道心动摇,凡心狂跳。
天成倒退两步,心中暗道:六欲红尘皆为苦,红颜祸水是骷髅。我一定要坚定道心,消弭妄念!
周玉莲笑望着天成,樱唇微启,齿如编贝,轻咬下丰盈鲜美的下唇,眼波轻轻一闪,发出银铃般的柔声软语:“天成哥哥,你说,我美不美?”
再美,百年之后你也会化作一具骷髅。这话天成可不敢明说,只能老实答道:“美,玉莲妹子美若天仙。”
“人们都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天成哥哥,我想做你媳妇儿,陪你过日子,这岂不比你上太白山当个小修士快活,你就、、你就依了小妹我吧。”
玉莲竟抱住了天成,一手抚着天成的后背,一手解下了云髻上的发簪,发丝一直垂到腰际,咬着红唇在天成的耳根呢喃低语。
天成口干舌燥,咽了一口口水,心中暗想:玉莲妹子乃是周敦颐老夫子之女,家教甚严,今日怎么如此大胆奔放?
如此细想之下,马天成灵台恢复一丝清明。心下又道:玉莲一个弱质千金,竟敢趁夜上山寻人,身边也没有马家庄的庄户相陪?还有,从百草谷到马家庄,我往日一人御空飞行,也要花半个时辰,今晚背着玉莲,却只花了一刻钟。
诸多疑点浮上脑海,让天成越想越心惊,还有母亲张氏的言行气质上,也有古怪。那身上的怪味,似乎是狐臭?
狐臭?狐狸精!
马天成吓了一跳,一把推开周玉莲。周玉莲哎哟一声,娇滴滴嗔道:“天成哥哥,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想跟奴家过日子吗?”
一口一个过日子,哪里像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马天成愈发觉得此女一身狐媚,不是真正的周二小姐,便冷着脸哄她道:“玉莲妹妹,你对我的心意,我心里明白。只不过我还要为父亲守孝三年,岂能与你、、你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那假玉莲这才脸色转暖,缓缓转过身,腰肢轻扭,姿态曼妙,莲步轻移。天成趁她不备,从囊中摸出一张黄纸,却是斗天剑派三代弟子的护身符箓。
所谓符箓,是指有一定修为的修士,耗费功力,将道法用禁制封印在符纸里。像马天成这样刚入门的小修士,道行浅薄,很多威力巨大的道法都未曾学过,他师父灵虚散人便耗费功力,制作了几张符箓,赠与他防身。有了这些符箓在身,天成只要牢记本门破除禁制的独门法诀,遇险时便能快速施展符箓里的精妙道法,多一分护身保命的希望。
天成轻轻一掌,将符箓贴在自己的额头,快速念了一通法诀,只见黄光一闪,符箓消失不见。马天成双眉之间,竟长了第三只眼,张开眼瞳,马天成瞧个分明,那假玉莲的双耳,又尖又长,双股...
六尾妖狐!妖狐精修三百年,方才多生一尾,这狐狸精多长了五条尾巴,那她就有一千五百年的道行!
马天成直冒冷汗,妖狐有一千五百年的功力,而且她已经化作人形,妖气内敛,这说明她已经重新锻炼了魂魄,修成了堪比道种的妖种!这等修为,远在马天成之上!
马天成使用的那道符箓,乃是斗天剑派独门的上阶道法:天眼真瞳!只有修炼《斗天仙典》到开窍层的修为,斗天门徒的天眼才会长出来。天眼真瞳,能见凡人之不能见,一切妖魔鬼怪,在天眼真瞳之下,都将现出原形!
趁那妖狐暂时不在身边,马天成用天眼真瞳,大略观察了下四周,才知道此处根本不是马家庄,乃是一所白狐洞,那些茶碗桌椅,乃是野草石头所化,那张大床则是妖狐用一具男尸所变。天成见那具男尸已经被妖狐吸成人干,心中更是后怕,心道:刚才我若道心动摇,现在恐怕也和这位仁兄一样,做了那妖狐身下的风流鬼了。
天成自知修为低微,不是那千年狐女的对手,又不想被她吸成人干,只好溜之大吉了。他又从囊中取出一道符箓,贴在头顶百会穴,念完破除禁制的法诀,才走出白狐洞。
这白狐洞外,竟还有十几个狐狸窝,几十个狐妖化作人形,在天成身边穿梭,竟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天成心中稍定。刚才他贴在头顶百汇穴的符箓,封印的是斗天剑派独门的中阶隐身法诀,一叶障目隐身法!这种木系的隐身法,极为管用,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还能用周围的草木之气,隐藏住马天成的气息,让天生嗅觉灵敏的狐妖,也闻不到天成身上的气味。
马天成逃出狐狸窝没多远,很快六尾妖狐就领着几十头狐狸精追杀过来。其中还有那假张氏,她居然是七尾红狐女,比那假玉莲的修为还要高!马天成怕得要死,山路不宽,他怕跟这群妖狐撞上,便闪躲至路旁的草丛中潜伏着。
只听那假张氏,娇声对那假玉莲道:“白灵儿妹妹,那小子肯定是有所察觉,使了个高明的隐身法逃掉了,我居然闻不到他身上的气味,真是可恨!”
原来那六尾白狐女名叫白灵儿。天成心中直咋舌:名字这么水灵灵的,心肠咋地如此狠辣,居然幻化成玉莲妹子的模样,引诱我行那苟且之事,还想把我吸成人干!
此时天眼真瞳的道法渐渐失效,那白灵儿又变成一个娇滴滴弱女子,白灵儿的人身,居然比玉莲还要娇艳三分。只见她美目流盼,唇如花开,对那假张氏埋怨道:“还不是红霞姐姐你刚才对他动手动脚的,他一定是闻到了你身上的狐臭味了。哪有母亲对儿子如你这般举止轻佻?”
那七尾红狐名叫红霞儿,此时她也懒得再变成张氏的模样,现出了她的人形,乃是一红发妖娆、年轻妩媚的花信少妇。闻言又羞又恼,笑骂道:“白灵儿妹妹,你我可都是母狐狸呀,就我有狐臭,难道你没有么?都怪妹妹你,偏偏要跟那姓马的小子成亲过日子,要换做是我,早就把他玩腻之后吸成人干,哪还有这么多麻烦!”
白灵儿摇头苦笑,柔声道:“红霞姐姐,你已经害了三条人命,若不知悔改,必遭天谴,也罢,我与那马天成终究是有缘无分,姐姐,我们速速离开此地,免得斗天门徒找上门来。”
七尾狐女红霞儿却吃吃笑道:“斗天门徒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姓马的小子确实有几分道心,不过修为却差得要命,我们的洞府离斗天峰有三四百里,凭那小子的修为,肯定逃不了多远,他一定是凭着那高明的隐身法躲在附近,没了本身的功力支撑,那隐身法持续不了多久的,等那姓马的的小子露出马脚,我一定把他抓住,他若是个知情识趣的,我们姐妹便共侍一夫,他若不依了你我,我定把他吸成人干,免得斗天门徒日后找你我姐妹的麻烦!”
那白灵儿还有几分善心灵性,这红霞却接连害了三个精壮汉子,已渐入魔道,她眼波一转,发现山道旁草丛空隙处,凭空多出一只男人的大脚,吃吃娇笑道:“马天成,你别藏着了,你的一只马脚已经露出来了。咯咯咯~!”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