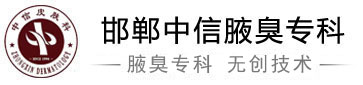唯一的夫妻叛徒 让红队遭受灭顶之灾 晚年悔改回国做慈善
凡是叛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对夫妻叛徒,他们直接让中央特科红队全军覆没,晚年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国做慈善。
盛忠亮和秦曼云
这对夫妻就是盛忠亮和秦曼云,这里先介绍一下秦曼云,他出身革命世家,兄长是著名的革命烈士秦茂轩,秦曼云的第一任丈夫我党早期军事领导人关向应。
五四运动爆发后,秦曼云积极响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她带领省立女中的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
1934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跟共产国际接头后,被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秦曼云同时也被逮捕。
盛忠亮和秦曼云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秦曼云跟李竹声被捕后立刻选择了叛变。他们随即供出了盛忠亮,他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无论怎么动刑,都宁死不屈。
就在徐恩曾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找到了顾顺章(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曾是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手中掌握着所有红色特工的绝密资料。
顾顺章就跟徐恩曾说了一句话:“盛忠亮这人我了解的,你这么问他肯定问不出的。但是他十分听他女朋友秦曼云的话,你可以从秦曼云身上做文章。”
顾顺章
果然不出所料,面对酷刑都不眨眼的盛忠亮,女友秦曼云一出马,就立马选择了叛变,他随即供出了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邝惠安的住所。
邝惠安是顾顺章之后,中央特科红队的负责人。手底下虽然只有30多个人,但都是红军时期排长级别以上的优秀战士,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制造炸药都不在话下,杀人于无形之中。
但就是因为盛忠亮的叛变,包括邝惠安在内的30多位红队成员全部被捕,他们的牺牲直接宣告了中央特科红队的灭亡。
盛忠亮、秦曼与蒋经国等合影
推广但凡腋下狐臭,不管遗传后天,牢记这个方法受用一生
解放战争过后,盛忠亮跟秦曼云逃到了台湾,后来因为不受国民党待见,于是又移民美国,在这里做起了生意。
1984年,盛忠亮受邀访问大陆。可千万别小看这件事,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破冰与融化,其实就是从他访问大陆开始的。
晚年盛忠亮也认识到了当年的罪行,于是从2000年开始设立“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资助石门贫困女子完成学业,前后总计花费50多万元人民币。
朱道来:贺子珍坚信他是毛岸红,身份成谜,毛泽东:把他交给组织
1932年10月上旬,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诞下一男婴,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
男婴的出生的消息让远在江西宁都的毛泽东十分高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结束后便立即赶往长汀。贺子珍产后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到长汀福音医院。
见到男婴的第一眼,毛泽东喜笑颜开,颇有些手忙脚乱地紧紧抱着他,好似害怕他会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一般。看着自己的孩子,毛泽东脸上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毛泽东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毛岸红”,“红”字透露出对他的殷切希望,毛泽东期盼他长大后能继承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为中华民族未来奋斗一生。
贺子珍生下毛岸红的过程很是顺利,但养育的过程却有些艰辛,贺子珍晚年常常说自己对毛岸红未尽到母亲的义务,颇有些亏欠。
那时贺子珍生下毛岸红后,不幸染上了疟疾,为避免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实在不便于亲自喂养母乳,所以便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不能亲自喂养孩子,这便成了贺子珍一生的遗憾。
好在,贺子珍虽不能亲自喂养毛岸红,可与长女毛金花未满月就被交由革命群众抚养并自此下落不明相比,毛岸红无疑是幸运的。
毛岸红出生时,我党面临的革命形势比较稳定,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稳中向好,因此毛泽东和贺子珍得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陪伴在毛岸红身边,看着他慢慢长大。
陪伴着毛岸红成长的那些岁月,是毛泽东那几年中最为高兴的一段时间。
每当毛泽东有烦心事时,还在蹒跚学步且甚是可爱的毛岸红,他总是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用颇有些不流畅的话说:“爸爸,陪毛毛(毛岸红小名)玩!”
每当这时,毛泽东的烦恼总会瞬间一扫而光,开心地抱着毛岸红打闹起来,好不开心。
毛岸红年纪虽年幼可却很懂事,从小就懂得孝顺父母。
毛岸红2岁时,每当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会站在门口等着爸爸毛泽东回来,有时候毛泽东忙于公务要很晚才能回来,毛岸红这时就会一直等着。
哪怕肚子再饿也不去吃饭,一定要等着毛泽东回来才吃。
这时,贺子珍害怕孩子饿着,总会告诉他爸爸要很晚才回来,让他先去吃饭,可是毛岸红每次都不愿意,总是摇头说道:“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有时,毛岸红会跟着战士一起去山上采杨梅,采摘杨梅时他总会把杨梅装在自己的口袋里。战士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毛岸红回答:“妈妈最爱吃杨梅,我要把杨梅拿回去给妈妈吃。”
这样其乐融融的生活,让人很是羡慕,任谁见到,都不会想到这么幸福的一家三口会在日后面临着骨肉分离,此生不复相见的悲痛局面。
然而,有时候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出人意料,让人猝不及防。
1934年,毛岸红2岁多的时候,我党面临的革命形势变得日渐严峻起来,由于王明、博古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地推行冒险的进攻战略,用红军不具优势的阵地战代替红军更具优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致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之中。
10月,鉴于革命形势日渐不利于我党,我党经慎重商议,决定长征。
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尽管长征路上需要面临着各种凶险万分的情况,可却丝毫不惧,当即便收拾妥当,随时准备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贺子珍临出发前,心里最牵挂的就是儿子毛岸红,起初贺子珍是想带着毛岸红一起长征的。
但是因为长征路上异常凶险,不但要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追前堵,还要承受着长征路上艰苦的生存环境,所以当时党中央便决定红军的孩子就地留下,交由留守的红军或是当地拥护我党的革命群众暂时抚养。
纵然有千般不舍,但为了毛岸红的安全考虑,毛泽东和贺子珍固然很是不舍,但还是决定将毛岸红留在中央苏区,交由留守苏区的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照顾。
临别前夕,贺子珍眼含热泪,双手颤抖地将自己的一件灰色军装剪开,就着微弱的烛光,亲手一针一线将从邻居那里讨来的棉花给缝进被剪开的灰军装中,制成一件小棉袄。
小棉袄缝好后,贺子珍还特意将毛岸红叫了起来,将其穿在毛岸红的身上,看看是否合身。
小棉袄很是合身,毛岸红穿着新衣服很是高兴,开心地跳了好几下,连说我有新衣服咯!
看着毛岸红穿着小棉袄的可爱模样,贺子珍想起即将与儿子分离,她的泪水便再次不自觉地夺眶而出,泪流满面。
看着妈妈哭泣的模样,毛岸红好似明白了什么,向来懂事的他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贺子珍见毛岸红大哭更是痛彻心扉,她急忙紧紧抱住毛岸红,连声安慰。
在妈妈贺子珍的安慰下,大哭许久的毛岸红渐渐有些累,不久便缓缓地睡了过去。
临别前的一夜,毛泽东和贺子珍都难以入睡,他们都想这一刻能永远停下,能永远留在毛岸红的身边,陪着他直到长大成人的那一刻,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毛泽东的房里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声响,可谁都知道此时毛泽东的心里并不平静,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更是无法体会到的。
第二天清晨,当警卫员给毛泽东收拾书桌时发现,书桌上有两张被泪水打湿的纸,其中一张纸上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岸英、岸青、岸龙、岸红。”
毛泽东清楚记得四个孩子的出生时间,可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现在就连毛岸红都要从自己的身边离开,这让毛泽东很是悲痛。
天下最不幸之事,莫过于骨肉分离。
临别前,当毛岸红得知爸爸妈妈即将与自己分离,嚎啕大哭起来,哭喊着不要离开爸爸妈妈,自己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见此场景,毛泽东的眼睛逐渐湿润了起来,贺子珍更是泪流满面,两人眼中都是满脸不舍。可是,无论如何不舍,终有分离的时候,眼见部队即将开拔,他们分离的时候也随之临近。
此时,贺子珍仍满脸不舍,很不想离开自己的孩子。
见贺子珍十分不舍,毛泽东便安慰道:
“子珍,我们进行战略转移,天天行军打仗,毛毛跟我们走会很危险的。毛毛留在三弟和你妹妹贺怡身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来接毛毛回家。”
贺子珍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听到丈夫毛泽东这么说,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选择暂时放下亲情,跟随部队长征。
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踏上了长征之路,毛岸红则交由毛泽覃和贺怡夫妇照顾。
任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会是毛泽东、贺子珍与毛岸红的“永别”。
长征开始后不久,瑞金和中央苏区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毛泽覃所面临的形势也愈发凶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此时,为了毛岸红的安全,也为了在之后的战斗中能够心无旁骛,毛泽覃决定将毛岸红秘密转移到瑞金乡下一个拥护红军的革命群众家里。
为免消息泄露,毛泽覃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毛岸红去了哪里,更未提及是被哪个群众收养的。
毛泽覃选择独自一人守住这个秘密,这样是没有错的,毕竟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没有人知道,毛岸红自然也就更加安全。
然而不幸的是,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冲出包围圈,毛泽覃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毛泽覃牺牲后,毛岸红的去向也就成为了一个谜。
毛岸红失踪后,党组织和毛泽东、贺子珍、贺怡等人从未放弃寻找过毛岸红的下落。
时间转瞬即逝,转眼来到了1953年。
这一年,党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寻找红军长征时失散孩子的工作,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也接到党中央指示其在江西境内开展寻找红军失散孩子的工作,并特别叮嘱希望他能帮忙找到毛泽东之前失散的儿子毛岸红。
不久,远在上海的贺子珍也给邵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贺子珍也请求邵式平能帮忙寻找长征时失散的儿子毛岸红的下落。
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和贺子珍的委托后,邵式平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展开寻找红军长征时失散孩子的工作,并指派江西省民政厅优抚处干部王家珍专门赶往瑞金负责寻找毛岸红一事。
王家珍接到任务后,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收拾行李便乘车赶往瑞金。
来到瑞金后,他顾不上舟车劳顿,当即投入到了寻找毛岸红的紧张工作当中,在当地县委的帮助下,王家珍将当地的老红军都聚集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希望能从老红军的口中获悉一些有关毛岸红下落的线索。
然而,当地的老红军都说不知道有关毛岸红的情况,别说是知道毛岸红在哪里,就连毛岸红什么时候被毛泽覃送养的都不知道。
见从老红军的口中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王家珍又去查阅《瑞金县志》,寄望于能从这里找到一点有关毛岸红的线索,可仍然毫无所获。
几日的忙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多少让王家珍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
为了能找到毛岸红,王家珍走访了很多老红军,也查询了很多的资料,见这些方法都没能找到有关毛岸红的一丝线索,王家珍便想到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那就是挨家挨户走访调查,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一家一家地问,直到能找到有关毛岸红的线索为止。
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王家珍的努力终于是没有白费。
一日,王家珍像往日一般来到一个叫叶坪乡的乡村走访,挨家挨户询问户主有没有收养过一个红军小孩或是村子里有没有听过哪户人家收养过红军小孩。
与往日一样,王家珍询问了好几户人家都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眼见已近傍晚,王家珍便想着明日再找。
就在这时,王家珍走到一块田地时,见田地上有两位农民劳作,本能上前询问附近有没有收养过红军小孩的人家。
王家珍起初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只是寻常询问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举动,让王家珍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王家珍从两位农民口中得知附近一个叫朱坊村的村庄有一个叫朱盛苔的农民,早年间曾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且农民还着重强调这个孩子的父亲据说是当时红军的一位高级干部。
听到这个消息,王家珍很是兴奋,当即决定第二天就去朱盛苔家看一看。
次日一大早,王家珍便乘车赶往朱坊村朱盛苔家。
见到朱盛苔和他的妻子黄月英后,王家珍没有过多的含蓄,当即问他们是否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朱盛苔和黄月英听到王家珍问起红军孩子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过多隐瞒,当即说到他们的确收养过一个红军小男孩,现在他已经22岁了,叫朱道来。
据朱盛苔说,朱道来是他在1934年农历九月底从二个红军的手中接过来的,他们当时跟他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红军高级干部的儿子,现在还不到2岁,因为红军需要转移的关系,只能暂时请他帮忙抚养,待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来接这个孩子并一定会好好报答他们的。
朱盛苔本来就是一个坚决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群众,见这个孩子是红军干部的后代,他没有任何迟疑,当即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等红军来接他。
这个红军小孩来到朱盛苔家后,为了孩子的安全,他对外声称这个孩子是黄月英亲生的,并给他取名“朱道来”,意为“半道而来”。
听到朱盛苔的描述,王家珍虽然不确定朱道来是否就是毛岸红,但是从他被收养的时间、地点和被收养的经历来看,他有很大可能就是毛岸红。
心中有了初步的判断后,王家珍便想见一见朱道来,想看看他是否跟毛泽东或是贺子珍相像,然而从朱盛苔口中说出的答案却给了王家珍当头一棒,原来此时的朱道来已经不在家里,早在2个多月前,被一位叫“朱月倩”的红军遗孀给接到了南京。
2个多月前,朱月倩带着南京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来到了朱盛苔和黄月英家中,与他们说朱道来是她和烈士霍步青(曾任中共宁清归特委书记,兼福建军区第三分区政委)的孩子,希望他们能让朱道来跟自己走。
朱盛苔和黄月英见她有组织的介绍信,丈夫又曾是红军高级干部,便没再说什么,当即就告诉朱道来说他的亲生母亲来接他了,然后就让他跟着朱月倩一起回了南京。
王家珍听到这个消息,既为烈士遗孀能找到失散的孩子而高兴,但也失落于好不容易找到有关毛岸红的线索可能就此中断。
不过,鉴于事关重大,王家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他问朱盛苔拿来了一张朱道来现在模样的照片,希望能从照片中找到一丝有关毛岸红的线索。
看到照片一刹那,王家珍顿时有些失神起来,因为朱道来的面相真的跟毛泽东很像,那宽阔的额头,脸部的轮廓都与毛泽东极为相似,仿佛就像是一个印子刻出来一般。
鉴于事关重大,王家珍向邵式平汇报了此事并将朱道来的照片交予他。邵式平获悉此事后,也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将朱道来的照片和关于此事的详细报告向中组部作出了汇报。
中组部接到汇报后,立即将照片、报告等资料送到了贺子珍处,看着朱道来的照片和相关报告,贺子珍心中顿时一紧,泪水不自觉地涌了出来。
她从朱道来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毛岸红小时候,随后她便向组织反映:“朱道来好像我的毛毛。”并恳求组织能够让朱道来亲自来上海一趟。
中组部经慎重商议,同意将朱道来接到上海,交由贺子珍亲自辨认。
邵式平收到中组部的电报后,当即指示王家珍,让他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前往上海。
1953年6月,在贺子珍哥哥贺学敏的安排下,王家珍、朱道来和贺子珍来到贺子珍的住所。
看到朱道来的第一眼,贺子珍便断定他就是自己的毛毛,因为他跟毛泽东真的长得太像了。之后,经过更进一步的调查,朱道来是毛岸红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朱道来即将被确定就是毛岸红时,此前已经认定朱道来是自己儿子的朱月倩赶来北京(当时朱道来被贺子珍认定有很大可能就是自己的孩子时,他便被接到了北京进一步确认),向组织陈述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霍小青,不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
朱月倩的到来,让整个事件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毕竟当时没有那么先进的DNA检测技术,虽然有多个证据指向朱道来就是毛岸红,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他就是毛岸红,况且朱月倩也很肯定朱道来就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儿子霍小青,因此谁也不能断定朱道来到底是谁?
就在这件事陷入胶着,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时,毛泽东站了出来,一锤定音道:“不管他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为了不同时伤害到贺子珍和朱月倩两位母亲的心,毛泽东做出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决定,将朱道来交给组织抚养,并认定他就是革命的后代。
之后,中组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朱道来既不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上海贺子珍身边,而是留在北京,交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照顾。
后来,朱道来从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朱道来被分配到了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
朱道来到底是不是毛岸红,现如今已经无从知晓,可以说永远成为了一个谜。
但是,唯一肯定的是不管朱道来是谁的孩子,他是革命后代,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革命年代,多少革命功臣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忍痛丢下自己的下一代,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功臣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失子之痛,他们可能直到晚年才找到自己的孩子,甚至有很多革命功臣一辈子都再也没机会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他们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真的付出,也失去了很多,他们的功绩必将被华夏儿女永世铭记。
入伍进藏即将54周年,我们丰都老兵都聊起当年入伍时的故事…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
在线上听丰都老兵聊故事
李伟
上周末,秦文祥战友与我在微信私聊时提议,今年底我们入伍进藏快54个年头了,能不能利用战友群这个平台,组织大家聊聊咱自己的故事。
前排左起刘中建、秦文祥;后排左起赵祥光、曹承孝、谭俊
好啊!你这个提议我赞同。聊得出彩的话,我还可以搜集整理出来,推荐给雪域老兵吧的主编茂戈老师,让更多的战友们分享咱丰都老兵的故事。
聊些啥呢?思索片刻我俩一致同意就从当年参军入伍,离开家乡的话题聊起。
谁来打头阵?他问道。
当然是你噻,你是群主嘛,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我戏谑地回应道。
秦文祥,这个肩上扛过“二毛三”从军33年,并曾在部队,地方人武部门等多个领导岗位历练过的老兵,如今虽已年逾古稀,但身板硬朗,精力充沛,脸色红润,妥妥的一匹老帅哥。在我俩私聊不久,他就率先在战友群里发出了帖子。
他在帖子里叙述道:
1970年冬,我被批准光荣入伍,参加人民解放军。冬季征兵接近尾声,入伍的青年也开始换发被装。
由于我所在的十直公社距树仁区公所的住地有15公里,而换发军装要统一去区里,那时没有公路又不通车,到区里只能走乡村小道。12月31日,轮到我们换装。一大早我就邀约本村及邻村的代春明、梁福银,李长武一路同行直奔区公所。
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各抒感想,由于换装心切,15公里的山路不到3小时,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公社武装部长范全明,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他虽然个子矮小,但做事雷厉风行,办事干脆利落。那天他先期到达,把我们16个人的被装都领了出来,按被子、鞋子、服装、脸盆依顺序摆放整齐,到一个发一个,发一个换一个,不合体的相互调换。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穿上崭新的军装,一下子让人变了个样。
我大姐时任树仁公社副社长,也来到发放现场,协助范部长发服装。被装发放完后,范部长又手把手教我们打背包、着装戴帽。他先示范,我们后操练。待大家的背包打得有模有样后,为了在天黑前都赶回家去,范部长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就叫我们回家去,处理好家务,作好入伍起程准备。
仁合公社新兵合影:前排左起李昌兴,徐龙志,李正祥。中排左起孙德顺(部长)李云昌,湛以普。后排左起陈民海,楊如华,王从华,陈定华,李万发。
那天,我身着绿军装,头戴毡绒帽,背起背包,手提脸盆,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
随着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心里五味杂陈,既为自己终于实现了当兵的愿望而庆幸,又割舍不下我年迈的母亲。在家里我是惟一的男孩,父亲在我6岁那年因病逝世,是母亲将我和两个姐姐拉扯大的。两个姐姐成年后相继出嫁,我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心里很清楚,母亲为我们这个家吃尽了不少苦头,常常是忙完地里的农活,又操持起家务,在那个靠挣工分维持生计的日子里,我们娘俩艰难度日。
记得离家的头天晚上,老母亲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反复地嘱咐我在部队要听领导的话,注意身体,要多给家里写信。我默默地听着,不断地点头。那晚,我们母子俩一直聊到了深夜。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母亲早已起床为我收拾好了行装,煮好了荷包蛋,我望着母亲过早佝偻的背影和花白的头发,眼泪叭哒叭哒地掉进了碗里。
到了该离家的时候了,我穿上军装,挨家挨户与生产队的父老乡亲们一一道別。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带着锣鼓队,敲锣打鼓送我和邻居代春明到公社报到集中。随着锣鼓声响,队里的乡亲们都赶来为我送行。
到了公社大门前坝子,挤满了欢送的群众和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持小红旗,静等欢送离乡新兵。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老父老母围着儿子唠叨的,有新婚妻子牵着男人的手交谈的,也有初恋女友偎依在男友怀里,恋恋不舍耳鬓厮磨的。而我的老母亲则在两个姐姐陪伴下,一直站在送行的队伍里,她那慈爱的目光追随着我,此刻,我心里一阵酸楚,“自古忠孝两难全”母亲,儿子再也不能在您膝下尽孝了,在我走后的日子里,您一定要多保重啊!
八点整,入伍新兵随着范部长“集合”的口令,背上背包,提着行礼,整整齐齐列队两行。十直完小16名少先队员拥向队伍,分别给我们戴上了胸花,公社书记发表了欢送词。范部长给我们编了临时班组,指定了班(组)长,明确了行进路线和注意事项。一声“出发”的口令,鞭炮齐鸣,锣鼓宣天,欢送队伍喊着热烈欢送的口号,一直送我们到场口,久久不愿散去,场面十分动人,催人泪目。我转过头去,向我的母亲,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向欢送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挥手告别,然后步行前往丰都县城。
经过近7个多小时,在连续拔涉了30公里后,我们提前到达了统一的指定地点,县城后垻广场。当时,除飞龙区较远新兵们尚未到达外,其他区的新兵们都已前后在此汇合。
在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后,飞龙区的新兵们终于赶到。见所有的新兵都己到齐,接兵营长李范杰带着参谋曹玉祥,大步流星地走到我们面前,曹参谋手持扩音器下达“各区成四路纵队集合”的指令,对9个区的800余名新兵进行了编队,同时安排了食宿地点,明确了当晚和第二天的任务。
为欢送全县的入伍新兵们,县革委当晚在大会场举行了隆重欢送会,县领导发表了欢送词,蒋崇生战友代表全县进藏的800余名新兵作了表态发言。会后,县川剧团为我们演出了移植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艺术家们在台上的精彩演出,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让我们在离开家乡前夕美美享受了一顿文化大餐。
次日下午3点多,全县新兵在后坝集合列队,准备到码头乘船启程。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在锣鼓队、舞蹈队、腰鼓队和送行群众的簇拥下,新兵成四路纵队,从后坝出发,沿商业街向长航码头浩浩荡荡地进发。
当我们到达上船码头后,还不到上船时点,新兵们在河垻沿岸坡上,以排为单位,成行成排站着、坐着,等候上船,周围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亲人和看热闹的群众。
图为当年运送我们新兵的人民号5号登陆舰驳船。
傍晚,运送新兵的人民号拖驳船,缓慢地驶入了丰都港。随着曹参谋的一声号令,我们起身整队出发,按顺序依次走上了趸船的跳板。在即将走进船仓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汉代刘向的一首古诗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再见了丰都!再见了我的父老乡亲们!
秦文祥战友刚在群里发出帖子,另一位战友也紧跟发帖。
他,就是李云昌战友,原11师侦察连的业务骨干,擒拿格斗样样在行。尽管也是年逾七旬,但身手不减当年,平时最喜欢戴顶军帽,穿迷彩体恤,俨然保持着军人的形象。
他在自己的帖子里,回顾了当年颇有戏剧性的参军经历。
记得70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去王庙拐县人民医院,看望老家一个病人,刚进大门就看见悬挂在外墙上方的一条横幅标语,参军光荣四个字格外惹人注目。经询问路人我才晓得,是我们仁合公社武装部孙部长带领十多个应征青年去参加体检。
当时我非常好奇的凑上前去看热闹,边看心里边想,要是我也能去参军,我老汉就再不会被人当走资派揪斗了(文革时期我父亲曾任县水电局负责人)因为我们家就是“军属"了噻。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壮起胆子上前询问孙部长:“像我这种“走资派”的儿子能不能报名参军呀?”孙部长扭过头来将我上下打量了个遍,爽快地回答我说,“只要你愿意来,当然可以的呀。”当即我心里一阵狂喜,忙不叠地连声道谢。
孙部长与我父母都熟悉,也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他关切地询问我,“你父母同意吗?”我赶忙回答说,“同意呀,他们早就想我离开丰都出去闯一闯了。”孙部长看我决心已定,面露喜悦地让我跟在他们后面去试检。
理明公社新兵合影:前排左起张光成,彭天于,曾召全,王国华,罗炳成。中排左起古坤世,罗顺发,杨学顺、古作成,古兆金。后排左起彭胜文(武装部长)徐成伟,彭洪全,余治国(武装助理)郭长生(接兵干部)
我记得一个军医把我们参加体检的青年都叫到屋子里,然后那个军医叫我们脱光衣服。当时我尴尬极了,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只听主检医生呵斥道,“你还磨蹭什么,赶快脱衣服。”幸亏在这大冷天屋子里还有一盆炭火,要不然准冻得哆哆嗦嗦地。见我们全脱了衣服,那个负责体检的军医转过身来,示意我们走圈圈,主检医生站在中间,仔细地查看有无石脚板,有无狐臭的,如有则被拉出列。最好笑的是让我们双手抱头离地跳远,好像一个个裸露的青蛙,让我忍不住的笑出了声。听见笑声那个军医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叫我出列单独跳一次。我憋足了劲,鼓起勇气双腿并拢纵身一跳,至少跳出一米七八,比在场所有的人都远。
经过五关斩六将的全面试检,当即淘汰了几个人,剩下合格的刚好十人。所幸的是我也合格了。体检完毕后,孙部长让我们回家等候消息。
在等通知的那几天,我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害怕被漏掉。就在我焦虑不安时,终于接到了去公社换军装的消息,我激动得一蹦三尺高,一路小跑地领回了衣服裤子鞋子盆子杯子掛包等。
我回到农村的老屋,迫不及待地穿上军装,然后又兴高采烈地跑回县城水电局机关宿舍楼家中给父母报喜。在路上,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们没想到的是,昨天还是个土里巴叽的乡下人,今天咋就成为了个军人。
父母下班回家见到我,脸上露出了又惊又喜的表情,争着问我,当兵这么大的事怎么也瞒着他们,我兴奋的对父亲说:“老汉,现在我们是“军属”了再没人敢揪斗您了。”父亲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后又关切地问我,“是去那里啊。”我给父亲茶盅里续满了热开水后回答道,“听接兵干部说去的是西藏。”哦!父亲沉默片刻,轻声地嘱咐我道,“西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也很冷,你去了要注意身体,我和你妈都不在你身边,天冷了要添衣服。”“什么时候走啊。”父亲又问我。”我说,“就这两三天吧。”
那晚,我们俩爷子打开了话匣子,聊得很多也很晚。
终于捱到了临别那天,我早早起来换上军装,背好背包拎着脸盆和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妹妹挥身告别。那一刻我眼眶里噙满泪水,甚至不敢回过头去看他们,我怕眼泪会掉下来。
71年1月6日,这是我成为一名军人走进部队的日子。午饭后,我们公社应征入伍的10个新兵,在孙部长的率领下,列队到县城后坝集中。在地方政府正式向部队交兵后,我们800余名丰都新兵,井然有序地排列成行,在鞭炮齐鸣,锣鼓声喧天,人潮湧动的欢送队伍的簇拥下,向长航码头走去。
大约晚上9点后,人民号驳船缓缓地驶入了丰都港,我们在父老乡亲们充满殷切期望的目光中,蹬上了驳船,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驳船逆流而上……
秦文祥战友和李云昌战友的两则帖子,犹如在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了两颗石子,荡漾起一圈又一圈涟漪,那些平时喜欢“潜水”的战友们,也一个个浮出水面,热议着自己当年报名参军的那一幕,不少战友纷纷跟帖,使原本冷清的战友群,霎那间似油锅般沸腾起来。
蒋崇生,这位曾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并在当年代表所有新兵,上台讲话的战友,在跟帖上这样说。
在即将迎来入伍进藏54周年之际,几位战友深情回顾了各自参军入伍,离别家乡的经历。读后让我感慨万千,当年的-幕幕仿佛就在昨天。我可以自豪地说,丰都的800男儿,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挥撒在了西藏高原。我们不负韶华,为红军师的军旗添了彩,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增了光,我们无愧为高原卫士、丰都骄子!
付体龙老兵也在跟帖上说,文祥战友和云昌战友的回忆文章,写得真实,值得我们慢慢去回味当年的入伍过程。
原31团的白家鲜,秦远久,曾庆伟,黄廷富,付廷权。32团的速官银,湛朝军。33团的谭正华,阮兴刚,付鸽平,隆永发等战友们也纷纷跟帖,分别述说了各自的参军经历,以及离开家乡奔赴西藏的心路历程。
甘在荣和冉啟祥俩位战友,还在群里晒出了珍藏几十年的入伍通知书。
图四为甘在荣,冉啟祥的入伍通知书
原33团特务连秦芝祥战友,在浏览完战友们的精彩帖子后,激动得随即赋诗一首:
难忘青葱岁月,立志保家卫国。
穿上绿色戎装,奔赴雪域高原。
而今迟暮之年,仍要发挥余热。
祖国若有召唤,挥戈上阵杀敌。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李伟:重庆丰都人,1971年元月入伍,曾在西藏军区陆军11师31团9连服役,1978年3月退伍。爱好诗歌,摄影,美术,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亦诗亦歌网》等网络平台。
作者:李伟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 上一篇:灵狐臭散(狐臭灵喷剂)
- 下一篇:手臂内有狐臭(手臂上有狐臭味)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