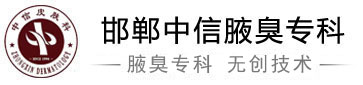小说:皇后处处虐待她,她替嫁离宫之时,略使小技让皇后染上狐臭
啊~啊~她们无声的叫着,除了张着嘴什么也做不了。
她们想死,却痛不欲生。她们后悔了,她们知错了,请公主饶了她们吧,她们再也不敢了呀!
每一下都避过要害却打在痛点,隐约间她们似乎还听到了骨裂的声音,多么可怕,多么恐怖的感觉啊。
最后,安云希一棒下去,打在了二人的膝盖骨上,那骨头应声而碎,没了骨头的支撑,二人齐齐倒地,依旧整齐的着装,但脸上的血肉模糊,腿上的血流不止说明了她们经历过怎样的一场惨剧。
第三日,有宫人在离冷宫不远不近处发现了此二人,周身爬满了蚂蚁,尤其是脸上,看着相当的恶心,此时的她们一息尚存,可也仅限于此了,膝盖骨被人打碎,不可能医治了,再加上已经毁了容貌,在宫里像这样的人,只有等死的份。
这等的小事在这皇宫算是常见,人们只会认为是得罪了某位贵人而惨遭报复,除了做事更加小心点,其他并无异样。
出嫁的日子到了,皇宫里只是门面上扎着红绸,可那红绸的质地却差强人意啊,一般人家用的红布也不过如此,可谁又敢说什么呢。这是皇后的命令。那看上去一百来抬的嫁妆,也只是表面上的,底下的全换成了石头。
“女儿啊,母后舍不得你啊。”皇后摸了摸根本没有任何东西的眼颊。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作戏呢,出嫁的人根本不是东灵儿。
皇后工夫做足,不得不忍着心中那股的作呕之太,假意的抱着盖着双喜盖着的安云希。
安云希不知不觉的抽出金针,待她又手张开抱过来之时,借着宽喜服就这么深深一刺,又快速收回,极速的出手并未让皇后有一丁点的察觉。
说起金针,倒也奇怪,放在了原主睡的床脚,若非细心,她也是发现不了的,想来这是那个母亲留下的吧。
“女儿,你在那边要好好的。”皇后在安云希耳边警告着说道,不管这个傻子能不能听懂。
“放心,我安云希,一定会再回来的。”安云希亦冷声的回应道,安嬷嬷的仇可不能就此罢手,出了宫还在再进宫的那日。
呃?
皇后顿了顿,这,这是怎么回事?她,竟然会说话了,那话中的敌意十足。还未等她回过神,安云希便由着嬷嬷扶出了宫门。
哼,回来?只怕有命去,没命回,皇后恨恨,还从未有人威胁过她呢。
想到此处,安云希嘴角微扬,轻轻的擦试着雪白的身体,享受着热水的浸泡。
只怕此时的皇后正无比的烦恼着,想想那雍容华贵,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皇后,每日臭气熏天的活着,日子越长臭味越重,算是为金碧辉煌皇宫添了一份特色吧。
“臭味皇后”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恼人。
那一身的狐臭之味用任何香粉都掩盖不住的,安云希很满意。她似乎都能听见皇后每日每夜的尖叫之声,就让这声音祭奠惨死的安嬷嬷吧。
对于敌人,不是将她一刀杀死,而是慢慢的消磨她的意志,让她亲自体会她以为最重要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离她而去。
想必皇上不会宠爱一个浑身狐臭的女人吧,哪怕那个女人是尊贵的皇后,在后宫之中,什么对后宫女人最重要,那便是皇帝的宠爱。
萧王府,坐落在北城繁华之地,占地面积极大,院外粉墙环护,绿柳周垂,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院中异香扑鼻,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牵藤引蔓,累垂可爱,奇草仙藤的穿石绕檐,努力向上生长。
“哟,我倒这是谁呢,原来是我们萧王府的冒牌王妃呀?”一个不和谐的声音闯入,最后几个字咬得特别重。
紧接着便是银铃般咯咯的笑声。
“轻浅姑娘。”碧桃上前问安。这个安姑娘明显的是不被王爷看中,倒不如轻浅,没准以后还能做上姨娘呢。
看着碧桃主动上前问安,轻浅笑容更深了,碧桃是个有眼界的,知道良禽择木而栖。也难怪了,王爷将她从青楼带回来,虽然没名没份,好歹也是第一个从外头带进来的不是。
“公主,这是要去哪里啊?这府中上上下下,轻浅倒还是知道的。想看景,问梅园是个好去处,想听曲,倚风阁不错。想喝茶嘛,秦管家泡的也还将就了。”
轻浅如女主人一般介绍着府中的一切,言里言外无不透着:萧王府,我比你熟。
安云希对于碧桃的作为,她不作评论,毕竟不是她的人,何必计较,只是她不喜欢噪呱的女人,特别是这种卖弄,自以为是的女人,她更加讨厌。转身,回去。
小说:官太太有狐臭,找王妃医治,王妃听了立马要拿刀划她胳肢窝
狐臭是由于人体腋下的汗腺分泌汗液较为发达,又迅速被腋下细菌分解,这才会产生特殊的臭味。
只需要将其发达的汗腺进行部分切除,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日常中,只需要保持腋下干净清爽就行。
凤芊羽满脸严谨,先用手术刀将她腋下切开了一个小口,慢慢的将切口的皮肤进行剥离。
紧接着,她一点点的将皮下组织以及大汗腺切除。
两只手都需要进行相同的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屏风外,云锦瑟等人紧张的等待着。
云锦瑟好几次忍不住想探头看,但还是忍住了,她虽然性子跳脱,但也知道轻重。
一个时辰后,凤芊羽将洪夫人腋下的伤口进行缝合清创和消毒,在纱布上抹了一些药膏,将其腋下包裹,这才呼出了一口气。
凤芊羽将白大褂手套等物,单独拿出了一个袋子装好,又拿出了一个袋子,将皮肉汗腺这些组织装起来。
最后将工具全部收好,回去在进行彻底消毒。
真是悲催,在现代的时候,以她的身份,手术完哪里还需要做这种善后工作,啧。
一切收拾妥当后,她这才转身:“屏风可以撤了。”
云锦瑟等人立马围了过来。
“风道长,我姑姑治的怎么样了?”
“夫人怎么还不醒啊。”
凤芊羽皱眉:“都退开,不要挤在一块。”
卫升立马将人全部拦了下来,卫秋十分有眼力劲的倒了一杯水递给凤芊羽。
她喝了水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瓶透明的药液,扒开了塞子,将液体给洪夫人灌了进去。
麻醉剂是麻痹神经,让人没有痛觉,这药剂则是刺激神经,让人提前醒过来。
几分钟后,洪夫人悠悠的睁开眼,感知恢复,手臂处的疼痛感立马传了过来。
“嘶,好痛。”
云锦瑟等人满脸担忧。
凤芊羽不紧不慢的道:“夫人,贫道的医治已经结束,您感觉到疼是正常的,这种疼痛会持续好几天,痛感会一天比一天减弱。”
“在此期间,您最好不要到处走动,以免伤口恢复不良。”
“手臂不要碰水,纱布更不能取下来,洗澡的话,暂时就停了吧,可以让丫鬟们给你擦一擦。”
凤芊羽拿出了一张纸:“这几天,吃食上面一定要注意,注意事项都在上面,希望严格执行。”
洪夫人忍不住问道:“风道长,我,我这病……”
她示意对方稍安勿躁:“贫道之前就说了,夫人这是小毛病,可以治,治疗很成功。”
“您的身体再也不会散发异味,您屋子里的那些熏香,都可以撤了。”
云锦瑟等人听了大喜过望。
洪夫人也激动的说不出话来,甚至高兴地一下子都感觉不到疼了。
“风道长,太感谢您了,真的太谢谢您了,您不知道,这个病对我是怎样的折磨,我,我甚至都有不想活了的念头……”
她哽咽的说着,泪如雨下。
这个毛病从小到大带给她的折磨和苦楚,其中艰辛,真的不是外人能了解的。
她能忍受到如今,真的很不容易。
“姑姑,你说什么傻话呢,以后不许这样想了。”
“是啊夫人,这病好了,以后啊,您好日子在后头呢。”
洪夫人大力的点头,又哭又笑。
凤芊羽看的也挺感慨的。
“风道长,酬金我已经准备好了,我……”
她抬手打断了洪夫人的话:“我七天后会在过来一趟,看看夫人的恢复情况,还要拆线,酬劳到时候在给也不迟。”
洪夫人又是一番千恩万谢,凤芊羽带着卫升卫秋离开了洪府。
过两天后,云锦瑟去六王府找了凤芊羽,请她在京都最好的酒楼,点了最贵的一桌菜,狠狠出了回血。
京都再次热闹了起来,因为再过半个月,端阳节就要到了。
端阳节的习俗要吃粽子,佩香囊,香囊内放置朱砂,雄黄,香酒等物,用丝布包裹,闻着清香四溢。
端口用亲手编织的五彩绳进行束封。
年轻女子,还能以此物相赠,对心仪男子表达情谊。
除此之外,最值得一提的一个节日喜事,就是赛龙舟。
只要风调雨顺,国家无灾无难,端阳节当日,各地都会进行划龙舟的盛事,京城也不例外。
京城的赛龙舟,地点在皇家园林内的一处玉湖内举行,届时,天元帝会亲自到场观赛。
朝中五品以上官员的府邸都必须参加,五品以下的官员,也可参加。
最后的胜出方,天元帝会给予赏赐。
这对于众多人来说,是一次在皇帝面前露脸的机会,自然全力以赴,劲头十足。
许多府邸,在一两个月前,就开始设计制作龙舟了,并且早早的训练了一批水上好手,到时候一展雄风。
六王府内。
东方璟也不知...
凤芊羽倒是无所谓,反正有这家伙在,她的早膳种类都要丰富多了,有好吃的,不吃白不吃。
“王爷,咱们王府也要参与龙舟比赛么?”
“嗯。”
“王府的龙舟做好了么?”
“嗯。”
“什么时候做好的,做的怎么样?威不威风?我能看看么?”
这朝代的节日跟现代的基本一样,习俗也大差不差,这让凤芊羽也有种过节氛围感。
现代的端午节,也有地方的龙舟比赛,但她读书后,一直都忙着学业,忙着研究,很少关注其他的事。
来了这儿倒是能闲下来。
东方璟瞥了她一眼,慢条斯理的将食物吞下去,缓缓地道:“食不言,寝不语,有问题吃完饭再说。”
凤芊羽:“……”
她翻了个白眼,嘀咕道:“这里又没别人,吃个饭而已,想怎么吃怎么吃,还那么讲究,切。”
东方璟放下筷子,抿了一口茶,看着她:“讲究自有讲究的道理。”
“吃饭时不宜开口,尤其嘴里有食物时,稍不注意,饭菜会喷出来,你觉得妥当么?”
凤芊羽嘴角抽了抽,她当然知道嘴里有饭菜不说话的规矩。
但现在没外人,这是她的地盘,她自然怎么舒服怎么来。
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 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 上一篇:破烂葱味狐臭(破烂葱味狐臭真恶心)
- 下一篇:狐臭能根除的吗(狐臭可以除根吗)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