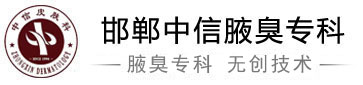安康县婚假习俗
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嫁要“六礼告成”。
一为“纳采”:男女双方在十六岁以后开始提亲,最初多为女性充当媒人,与男女两家说话,俗称“掏内火”,介绍双方家庭状况,但特别拒绝有“门户”(狐臭)者。
二为“问名”:即取“口八字”。经双方家长同意后,始由男方正式请媒(红叶),须是男性,由原“掏内火”之丈夫充当,另请一有声望或公认的正派人物为“陪红”。正式说亲,选黄道吉日取“口八字”(指女的年月日时生辰,以红纸书写),取回后,先在神龛香炉下放三日,以家庭平安无事或是否“进财”验证女方之命运,然后请“算命先生”“合婚”。
三为“纳吉”。算命合婚后,再请“红叶”商量日期,正式取“红八字”订亲,男方备金银首饰、布匹、衣物、点心、猪羊腿、鸡、鸭等作聘礼,女方答以衣帽、针线(刺绣品),多寡随意,从无争执。
四为“纳征”。取八字后至婚前一段时间,有一次礼节性的联谊,俗称“走头回”,同样由男方送衣物给女方,女方回礼。每次均是“红叶”坐首席,故有“是媒不是媒,嘴上抹三回”之说。
五为“请期”,俗称“通讯”。相隔一段时间后,男方再请“红叶”约定结婚日期,双方各自准备并备办酒席。亲友则为出嫁女子送首饰、衣物、器皿或钱财,谓之“添箱”。
六为“迎娶”。婚前一日,男方“行盒”(盒以点心扎成),抬食盒(读洛音)到女家,回来抬女方妆奁(出嫁姑娘必须给妆奁)。富者箱柜、被褥、衣服、各种器具,应有尽有,还有银钱;贫者仅衣箱一口或软包袱。旧时,“男一半,女一角”,姑娘出嫁父母以其财产的四分之一陪嫁,故有许多妆奁。往返由乐队奏乐吹打热闹。从提亲、订婚直到结婚前的过程中,婚配的男女当事人,不能见面,不得参与意见。“行盒”“迎陪嫁”的晚上,“令上的”在新房奏乐,谓之“哄床”,以全命人(指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儿女者)二人在新房睡觉,象征新人全命。迎娶前一天,姑娘家母女分别前要哭,一是多年母女情感,临别生悲;二是未卜以后日子是否好过,心中忐忑不安;三是母嘱其女过门后要侍奉公婆,体贴丈夫,好好过日子。但迷信者旨在“哭煞气”。迎娶日黎明前,男方点燃灯笼火把(含寓抢亲古俗),抬空花轿上路,沿途吹吹打打。到女家门,乐奏三通。女家开门,只见新娘头梳倒抓结,身披赁衣,顶盖头,袜套鞋上,由其兄(弟)背上花轿。至男家门,打醋炭(以醋浇燃烧着的炭火,喷出酸味)后,由两个接亲的妇女扶新娘出轿,走红地毯,新郎揭盖头,接着端迎门盅者走;也有的直至堂屋,拜天地、敬家神,在“拜堂”入洞房后才揭盖头。新郎抱“车马头”上供“红鸾天喜之神位”入房。新娘梳头、照镜、修面,脱去赁衣,换上新装,全家吃“和气汤”后,始为贺喜人“双拜”。夜间有好事者还要打趣“闹房”,热闹一番。
第二天或第三天“回门”,由女家备办酒席,宴请新郎及亲友。第四天新娘入厨切“试刀面”。八天后再回娘家,谓“熬八天”。
民国二十几年,城市提倡“文明结婚”。新郎穿制服,新娘穿旗袍顶罗纱,双方胸前带红花,不坐花轿坐亮轿。举行婚礼时,请地方知名人士证婚,双方家长主婚,“红叶”改称介绍人。亲友来宾即席祝贺,证婚人填发结婚证。婚礼时有乐队伴奏,然后宴请宾客。这种“文明结婚”在民国后期城镇已经普遍。农村仍有沿旧习者,但仪式较前简略。
建国后,1952年颁布《新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结婚仪式简化。领结婚证后,即安排糖果,请来贺者吃喜糖,入洞房即成夫妇。婚期一般安排在节假日举行,农村多选择双日子。男方不要嫁妆,女方不要财礼,但传统习惯女方多少总有几件奁妆。“文化大革命”期间,妆奁上摆四本《毛泽东选集》作点缀,以示“政治挂帅”。1978年后一些旧习渐起。农村兴“看家”,即选择吉日,姑娘由多人陪同到男家作客,男家摆酒席,给“启发”,陪同人也有一份,花费颇多。婚礼要男家买“三转一响”(三转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指收音机),富者更甚。1981年后,讲排场要价日高,“三转一响”变成更高档品,有收录两用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原由女方陪嫁家具,改为由男方配置,并由大衣柜、沙发、五斗柜,发展为“组合家具”。迎亲要乘坐汽车,以录音机代替乐队招摇过市。农村则用拖拉机、卡车迎亲,且滥放鞭炮,大摆酒席,铺张浪费相当严重。又有“旅行结婚”者,有的回家后仍收礼待客。
旧时夫妻离弃,主要因家庭经济纠纷所致,也有男方嫌女方不育或因生女而受虐待,或某一方道德败坏,喜新厌旧所致。女方父兄因离弃不平而至男家闹事,若女方自杀,即酿成血案,经官诉讼,甚至倾家荡产。建国后,离弃多因感情不合,或因社会职业改变,嫌对方土俗、无知,也有道德情操低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因“政治问题”也造成夫妻被迫拆离。近年经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有所增加。
阴山奇案——乱世情爱中的仇恨火种
微信公众号“大发小苑” 作者 础青
大母猪对武大郎说:“你早早离开以后......”
武大郎觉得她这样对着自己说话,把专员撇在一边是本末倒置,便呵责道:“挑主要的说,看着太君说话!”然后退到了专员的身后。其实他也是害怕专员的那双眼睛,不敢正视。
专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武大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放缓语气对大母猪说:“你说,武田太郎早早离开?后来呢?不要害怕,慢慢地,仔细说。”
见老鬼子的目光中没有了煞气,大母猪也放松了下来。
“昨天,翻译官早早地离开了醉春阁。田中太君好像很喜欢山樱桃花,他吃着狗肉喝着酒,絮絮聒聒地念叨起他家乡的樱花树和他的女人凉子,后来又唱起了日本歌曲,还让我和他一起唱,我听都听不懂,哪里会唱?幸亏我女儿元宝解围。”
打扮得像个大学生似的小母猪,鱼肚白的旗袍装上衣勾勒出丰乳蜂腰,下身搭配着藏青色的长裙,金黄色的头发扎成两条齐肩小辫,头顶上还插着一小枝山樱桃花,略施粉黛的脸上,洋溢着青春气息,整个人显得端庄秀雅。大母猪都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学会的那首叫《樱花》的日本歌曲,而且还会边唱边跳。
小母猪一反常态的逢迎,转眼就把田中从乡愁的悲戚中拯救出来,两个人站起来手拉手唱歌跳舞,坐下来搂抱着喝酒吃肉。田中一会儿叫她元宝、小猪猪,一会儿叫她凉子。
根厚收拾好赌桌赌具,从西厢房出来,在院里经过正房东屋的大窗户时,看见屋里这两个快活得忘乎所以的人,气得站在那里攥着拳头咬牙跺脚,大母猪见状急忙把他推进了东厢房。
一进屋,大母猪就让根厚脱裤子,不脱,就把他推到炕沿边坐下,然后揭开他撕烂的裤子,像个母亲一样,小心翼翼地往他大腿上抹獾油。嘴里唠叨着,这獾油治烧伤可是最好的,疼不疼?忍着点儿,一会儿就好。根厚本就话少,此时头歪向一侧低着,呼呼喘着粗气,两只手攥紧伸开又攥紧,手指骨节发出嘎嘣嘎嘣的声响。大母猪见他后脖颈通红,以为是害羞,说,你和元宝那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我都快成你妈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着话,她侧身探过头想看看根厚的表情,根厚的头却更低了。又嗔怪道,上次在自己的胳膊上扎了一刀,这回又拿火炭烧大腿,你大该教你个别的法子,应对那些耍横的赌鬼。
根厚比元宝大两岁,今年十七。五岁那年,亲生父亲下窑挖煤时,被顶板冒落的石块砸烂脑袋,当时就死了。父亲一死,家里就断了粮,母亲带着他苦熬了一年,眼看着娘俩都要饿死了。一个下雨天,母亲把他推进了醉春阁院里,让他去房檐下避雨,说是给他找吃的去,走后再无音信。后来听一个煤贩子说,母亲跟着一个拉骆驼的人走了。
母亲走了,原来住的草棚子也被风吹散了架。骨瘦如柴的根厚白天在街上流浪,讨不到饭就捡垃圾充饥,天黑了就去醉春阁的房檐下睡,刘老板忙不过来时,他还能帮忙打个下手、跑个腿。
这孩子肯吃苦,嘴上不爱说话,眼里却有活。慢慢地,他在醉春阁能干的活越来越多。有几次,刘老板有意在他饿得饥肠咕咕的时候,让他往西厢房的赌桌上送点心,并在暗中观察,发现他从不偷吃,便有了收作义子的想法。
也是山樱桃花开的季节,那天刘老板摆了酒席,请来乔掌柜、赵掌柜、樊先生、铁匠等人,正式认了根厚为儿子,并给他改了姓名叫刘根厚。从此根厚改口叫刘老板“大”——大发本地人把父亲叫“大”。
刘老板教他识字算术,也把一身的好武艺传给了他。在富足的醉春阁院里,衣着体面的根厚像春天里疯长的野草,十来年的功夫就长成了一颗粗壮的大树,比刘老板还高出半头。铁匠说,这身材是随了他死去的亲大。他亲大就是身高马大,力气大得无人能比,活着的时候每天从煤窑底下背上来的大碳,都比别的窑工多。
大发街人都知道,根厚对刘老板像狗一样忠实。
元宝跟母亲来到醉春阁那年,根厚十二岁,已经能写会算,一套形意拳打得虎啸生风,上房翻墙如履平地。青梅竹马的两个孩子上山逮蚂蚱、下河摸泥鳅,焦不离孟。随着年龄渐长,自然生了爱意。元宝一直不接客,也是在为根厚守玉。所幸俩人的爱情得到了刘老板的默许,虽然嘴上没有承认,心里打算着过几年,他们再大些就给成亲。大母猪巴不得早日成就这桩好事,自己就成了醉春阁的半个东家,后半生有了着落,可就在她做着美梦时,鬼子田中来到了大发街。
田中在醉春阁院子里,大白亮天、众目睽睽之下糟蹋元宝时,根厚正好去了街上的缸房买酒。当他挑着两坛酒回到醉春阁时,元宝正在西厢房往房梁上扔绳子,多亏房梁高她够不着,否则就上吊死了。而当时,大母猪和刘老板正被刺刀顶着,在厨房给这帮日本人做饭呢,见根厚回来,刘老板马上接过酒坛子,给他使眼色,让他赶快出去找元宝。
刘老板知道根厚的性子,他打开一坛酒招呼日本兵用碗舀着喝,乘机跑进西厢房,摁住了正要往出冲,眼珠子要滴出血来的根厚,压着声音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照看好元宝。今天你要出来,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根厚被刘老板擒得动弹不得,从喉咙深处突然暴发出一声狼嚎一样撕心裂肺的吼声,这吼声让刘老板都不禁寒毛卓竖,也吼醒了元宝,她丢开紧紧攥在手里的绳子,扑过去,跪在地上死命地抱住了根厚的双腿。
根厚知道元宝天生带着狐臭的毛病,但他并不在乎,自己什么脏的地方没睡过,什么臭的东西没吃过?更何况她能弹会唱、识字读书,这样的姑娘寻遍大发街也没几个。
大母猪给根厚包扎好伤口后,就回去招呼喝酒的人们去了。
西屋里大母猪嬉笑招呼,东屋里小母猪陪酒陪唱,两间屋一边一个女人,不偏不倚。刘老板得了空,来到东厢房看儿子。
“伤的怎样?”
“烫了几个燎泡,甚事没有。”根厚气鼓鼓地说,“如果你答应的话,杀田中那个牲口也不在话下!”
刘老板连忙捂住他的嘴,附在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安抚他躺下后,才又回正房忙乎去了。
田中在小母猪的顾盼巧笑轻歌曼舞中,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不知喝了多少酒,还破天荒地往小母猪怀里塞了一块银元。
灯油即将燃尽的时候,小母猪醉得晕晕乎乎睡倒了。刘老板扶着一步三晃的田中出了门,在院里又给他指了指那棵山樱桃树的位置。接着,西屋喝酒的人们也都出来了。见翟先生深一脚浅一脚醉得走不稳路,刘老板就叫起了东厢房里睡觉的根厚,让他送翟先生回家。转过身来又对楞大头、侯雯他们几个说,今天各位没尽兴,我陪几位爷玩儿几局,咱们换个新法——轮流坐庄。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大把明晃晃的银元,这正中了赌汉们的下怀。
因为刘老板从不亲自上赌桌,也勾起了几位掌柜的们的兴趣,便一窝蜂地都涌进了西厢房。
这一夜的掏宝桌上,可谓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后半夜时刘老板面前的银元、钞票已经翻了倍,而参赌的人竟没有一个彻底输干退场的。仿佛每个人都有翻本的希望,但桌上的钱转来转去却都停在刘老板面前。他打了个哈欠说,老啦,实在熬不住了。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众人的反对:
“不能赢了钱就走哇?”
“天还没亮啊!”
“再玩一会儿吧。”
刘老板拱手道,我去把根厚叫起来陪各位。钱,一分不带走。实在是困得不行,我要去睡觉了。
“快去、快去把根厚喊起来。”赌徒们当然高兴,心想赢不了老的,还赢不了小的?
最终是武大郎在山樱桃树下的三声枪响,才惊散这场赌局。
下集预告:
《土匪“请财神”,日军剿匪》
张崩楼带人闯进了杂货店,因为没搜出多少钱财,临走时绑了乔掌柜的老婆,留下话,拿二百大洋到香柏林沟去赎。第三天,乔掌柜还没凑够钱,晚上就有人把他老婆的一只耳朵扔进了院里,包耳朵的麻纸上写着‘二百五十大洋’的血字。最后,乔掌柜花了三百大洋赎回了只剩下一只耳朵的老婆,那女人回到家时,已经被糟蹋的不成人样了。
小说:少年不懂事惹上恶鬼,父亲请人帮忙,居然想要以鬼治鬼
丁子拿着杀猪刀一砍。
一个小鬼被拦腰砍断了,冒出一蓬乌黑的血渍。
他杀得眼睛都红了,冲我吼道:“小子,把东西给我交出来,要不然我今天一定弄死你。”
二丫尖叫着,她跳到丁子脖子上。
她一伸手,就捂着他的眼睛。
鬼遮眼?
丁子看不到了,就拿着杀猪刀,胡乱砍着。我看二丫难受的样子,估计是受不住杀猪的身上的煞气。
我急忙说道:“你们把我扶起来。”
两个小鬼抓着胳膊,传来一股阴寒的触感。我忍着不适,从地上捡起一根长棍子。
你个王八蛋,让你害我。
我眼睛通红,就朝他裤裆里用力一插。这家伙痛的发出惨叫,把杀猪刀丢了,伸手去捂着裤裆。
“你个小崽子啊。”他叫的难受。
我还要戳,他抓着竹竿,我的力气比不过他,被他给挑翻了。二丫忽然跑过来,扒着我的小腿,把血给喝了。
她的身上变得更冷了,眼珠里冒出红光,浑身的气势都变得不一样了。
二丫又变起来一块石头,这下子直接砸中丁子的脑门。他转了两圈,就昏倒在地上。我叫道:“二丫,你快说,地窖里有啥?”
几个小鬼哇哇大哭。
阴风阵阵,冻得我浑身哆嗦。
好可怜。
“瓜娃,帮帮我们,帮帮我们。”
二丫要说话,忽然露出痛苦的模样。
“瓜娃,你快跑,村里有人要害你。”
我也不害怕了,急急抓着她:“你跟我一起走。”
“他在念咒,要把我们喊回去。”
这些小孩勉强抵挡了下,眼珠子变得浑噩,又爬进了坟头里。那么小的一个坟,不知道怎么会钻进去这么多?
我撑着竹竿,一蹦一跳地回家,现在只有爷爷有法子了。
因为太心急,结果摔进个泥坑里。
腿上的剧痛让我眼前发黑,怎么都爬不起来了。嗷的一声,我就扯着嗓子就哭了起来,声音那么大。
委屈透了。
一个温暖的手掌抚摸着脑袋。
是青袍人。
他不知道啥时候来地,静静地看着我。
我又羞又气,捡起一块石头,就朝他丢去。这人也不躲,石头径直穿过他的身子。我一个哆嗦,他不是人!
“瓜娃,你受苦了。”
我恼怒道:“你不是说我爹找你帮忙吗?你死哪儿去了?我的腿都被打断了。”
他跳下坑,捏着我的腿。
真奇怪,腿不疼了,比吃了灵丹妙药还要灵验。
“你是不是也想要我家的玉?”我紧张兮兮地问道。他笑了下,没有回答我,反而道,“这些天我就待在村里,打听了下从前的事情,算是有了些眉目。”
打听?
当年的人都死光了,他找鬼去问啊?
一想到他也是个鬼,我急忙闭着嘴。
“走吧,去你家,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我摇头:“你会吓着我爷爷。”
青袍人也乐了,拍拍我的头:“真是个傻小子。”
他搀着我,走不远,前头出现一个茅草屋。
有个妇人走出来,低头叫:“过路地,口渴了吧,到我家来喝口茶再走。”被她一说,我真的觉得嗓子冒烟儿。
青袍人打量她几眼,笑呵呵道:“我也渴了。”
进了屋。
女人勤快地端茶出来。
清亮的茶汤,氤氲的香气,勾的肚子里馋虫都坐不住了。还没到嘴,青袍人一把夺过去,把两杯喝了个干净。
“茶不错,还有吗?”
“你是来捣乱地。”她的声音变得又阴又冷。
我一个哆嗦,这才发现女人只有眼白,没有瞳孔。往她脚下看,居然是没有影子地。我吞了口唾沫,干巴巴道:“谢谢你的茶,我不渴了,我们走吧。”
女人尖叫:“吃了茶,要给钱。”
我哪有钱?
青袍人慢条斯理道:“本来该给钱,可你这茶里有害人的东西,我还要拉你去见官呢。”
女人像是要笑,结果脸上的肉就掉了下来。
“知道茶有问题,你还敢喝?倒,倒,给我倒。”她跟念咒语一样,我觉得头晕,青袍人却是若无其事。
“怎么可能?”女人终于慌了。
“你是不是在喊这个小东西。”
青袍人张开嘴,先是手,然后是整条手臂,一整个塞进了肚子里。他搅了两下,提着一条黑乎乎的毛虫子出来。
女的见势不妙,立马吼道:“当家地,有人来捣乱。”
哗啦啦,屋子里腾地冒出七八个男人,凶神恶煞地打量我们。
我瞪了青袍人一眼。
知道有问题,你还进屋?这下好了,咱们都走不了了。
“别呀,婶子,我也是无归村的人。咱们说不定从前还认识,都是乡里乡亲地,你就高抬贵手好吗?”打打感情牌,说不定能活命。
女的一声厉笑:“呸,老娘以前在家好好地,被人拐到你们村,嫁了个孬汉子。吃苦受累倒罢了,...
真是不讲理。
别人害你,你去找别人,害我干吗?
“怎么办?”我求助地看着青袍人。
他倒是一点不急,呵呵道:“人都到齐了?早就听说这附近有个恶婆娘,抓了七八个男鬼养着,做起了女大王。我不去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了。”
女的估计觉察到不对,立马一声尖叫。
“贼汉子们,还等什么?谁撕了这两个,今晚我就让谁上老娘的床。”
男鬼跟吃了兴奋剂一样,嗷嗷叫着,一股脑儿冲来。青袍人把我提到后头,他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黄色符纸,掐着指头,喝道:“定,定,定,全都给我定住。”
女的和一群男人立马僵住了。
我一捅,她立马跌了个滚地葫芦。
“哎呦,真灵验。”
想到她害我,我用力打了两下。
青袍人在人群里挑来挑去,托着下巴,啧啧有声:“这个胖了点,这个太丑,这个还行,唔,居然有狐臭?不要。”
“你干嘛呢?”
把鬼都定住了,还不快跑?
“挑一个身体。”
我胡乱指了个,说:“这个最好。”
他嗯了声,拍拍那个鬼男人的脸,说,“哥们儿,把你的身体借我用一用,回头我给你烧纸钱。嗯,你不说话,那是不是答应了?果然是个乐于助人的好鬼。”
我无语了。
“出去,等我。”
他一拍我,我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猛地跌出屋子。
外头月光正亮堂着,哪有什么屋子?刚才的一切仿佛是幻觉。
劈啪,地表裂开一条缝儿,一个手臂弹出来,然后爬出个人。
是刚才的男人。
他活动下筋骨,说道:“还好,这人没死多久,身体没有腐烂掉。”
“是你吗?”
“还能有谁?走,我背你回家。”
我趴在他肩头,想到这是一个死人,一阵渗人。虽说还没腐烂,但这身体已经散发出一股异味。
“要是难受,就叫出来,我不笑你。”
我立马把嘴抿的紧紧地。
到了我家门口。
烛光亮堂着,爷爷还没有睡?
“呵呵,还有人抢在我前头啊?”青袍人笑了声。
我叫了声爷爷,门立刻开了。爷爷一脸惊喜地看着我,然后又惊悚起来:“你,你不是谢家的老二吗?去年跟女人乱搞,得了花柳病死掉了吗?”
青袍人的背脊立马僵住了。
我大叫不好。
他恼火地转身,捏着我的脸颊,道:“这是最好的?”
我一直在外头读书,哪知道谢家老二是怎么死地?见我朝他裤裆看,他的脸色更黑了,揪的我哎呦叫唤。
屋里头冲出来两个人,叫道:“大爷,快进来。这是一个借尸还魂的老鬼,他要来害你们全家呢。”
青袍人把我放下,郑重道。
“正式介绍下,我叫叶牧,受胡莽父亲的委托,来帮你们解决这件麻烦事。”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