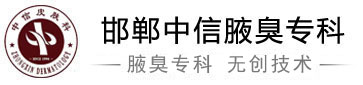二战后,为何苏联女兵纷纷都向日本战俘表达爱意?
二战之后,苏联作为战胜方,俘虏了约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一时间,如何处理这些战俘成为了一个问题。思来想去,战后同样元气大伤的苏军决定将其中身体尚强健的日本战俘输送到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劳动。
硝烟落地,日本战俘和苏联士兵之间的政治隔阂依旧存在,但是文化观念上的融汇和碰撞令苦寒之地独具人情,最使人纳罕的是,当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劳作之时,居然出现了不少苏联女兵向其“示爱”的情形?
回溯长河,走近历史,一探内里究竟。
1945年8月9日,苏联远东地区150万名红军向着东北的关东军发动了闪袭,原本就斗志消散的日军不堪一击,60多万关东军转瞬间沦为了苏军的战俘。
彼时,苏联虽是军力强盛的战胜国,但是在二战中男性军人依旧死伤惨重,因为兵源不足,在短时间内甚至招募了大量女兵,这些飒爽佳人将最好的青春投身于战场,在坦克手、飞行员、狙击手、专业间谍等岗位上颇为出彩。
二战一结束,苏联内部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男性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1945年俘获了这一批关东军战俘后,苏联方只考虑了片刻,就决定利用这一批日本劳力,去开拓艰苦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
纵然百般厌恶仇恨,但较之坑杀毒害等有损国际声誉的做法,征为苦力显然更为“仁慈”——至少大多数关东军战俘一伊始存有这种侥幸心理。他们被塞进了“闷罐”火车,先从西伯利亚出发,到达了莫斯科东南400公里处的的118战俘所。
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有资格去“建设”苏联国家的,在此之前,需要对这群“罪恶的战犯”进行劳改和遴选。
这所位于坦波夫城的战俘所同样寒冷刺骨,进入各个劳改所之前,劳改所所长首先要对关东军战俘门进行为期三周的检疫隔离。每一个战俘都有自己独属的序号,凭此序号去吃饭、洗澡。
浴室就在宽敞的院子里,战俘们需要将腋毛、头发、腿毛、胡须等毛发全部剔除干净,将衣服放入干燥炉内杀菌消毒,才可以迈入浴室洗澡。如果战俘们度过检疫隔离期(只要没有传染病,一般都会安全度过),就要接受苏联方的“劳动前审讯”。
审讯的内容多为个人思想关,即本人有无反苏反共的黑历史,有没有强烈的“反动”意识,一旦在审讯过程中发现战俘参加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名战俘就会被立刻移送到惩罚收容所接受严刑惩戒。
如果在陈述个人过往经历时,审讯官没有发现反苏反共的劣迹,那么战俘们将直接被投放至劳动环节。
战俘营会将这些俘虏当作劳工,派遣到各个企业中去,一句当地各类企业团体的需求,将战俘营的俘虏当作劳役,各个企业团体依照苏联劳动规定计算薪资,这些薪资先交给战俘营,待到将战俘的照明、瓦斯和燃料费、餐费都扣除以后,剩下的才会发给俘虏们。
这些战俘在西伯利亚大多从事采矿业工作,可大多数厂矿企业并没有为安置这一批数量庞大的战俘而事先准备,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群人曾是军人,必然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于是将他们扔到了荒野地带,只督管他们上工。
至于这群关东军战俘的应对之法,也只好是挤在帐篷、窝棚,或者是腆着脸去一些简易农房里面借住。关东军战俘们平日里需要完成矿上的任务,细碎的闲暇时间还要聚在一起修建住所、厕所和厨房等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当年成为苏军战俘,后来又被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多年后终于公开回忆了初到西伯利亚的情形:“我们住的是窝棚——半地下式的,从1946年的1月一直住到了8月,这些窝棚用原木修建,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很有些年头了。”
苏联方当时刚刚结束战争,国内经济依旧处于疲乏不堪的境况,本国的平民尚且难以过冬,能分给这批日军战俘的,只有棉袄和毡疙瘩,这摸起来尚算厚实的装备要一直穿到第二年的春天。
清水芳夫仍记得那一段极其恶劣的日子:“西伯利亚的冬季常有暴风雪,厚实的冬衣在外面走一天,棉袄湿透了,毡疙瘩上面业满是雪花,我们的装备是独一套的,绝没有多一套欢喜的,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排着队去干燥室烘干衣服。”
彼时,战俘们最羡慕的就是从事伐木的工人,因为当他们收工之时,每个人可以扛一根高壮的白桦树,回家劈柴取暖。饶是如此,一个冬天过去,依旧有不少本就身体虚弱的战俘被饿死、冻死、病死。
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关押了将近1500人,但是1946年的冬天过去,500多人死于极寒和疾病。
因为死亡人数过多,使得原本储备的劳力损失,于是原本担任战俘所所长的苏联军官也被送进了劳改营。
然而,这一个冬天过去,到底有多少日本战俘死在了西伯利亚呢?这是一个尚不确定的数字,苏联官方1946年给出的数据是5.5万人次,但后世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都认为这个数字大为保守,所有经历过那个冬天,且最终活下来,得以遣返回日的军官都称那是“地狱”。
二战之后,因为男性军人死伤惨重,于是女性开始活跃在军政和重要岗位上,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也是如此,女性军人、丧偶少妇、丧父孤女的数量是当地存活的男性军人的两倍有余。
于是乎,60万男性日本战俘接洽的苏军长官尤以女性为主。一开始,苏联的女兵们极度厌恶这些战俘,军人本就具有强烈的荣辱羞耻观,日日受到姿容秀丽的苏联女兵们轻蔑的嘲讽,常有战俘忍到拳青硬,脸庞通红,也不敢吭一声。
苏联女兵们闲暇时会聚到一起讨论各国的战俘。“德国的那群俘虏心眼最多,眼珠子滴溜溜的,一有机会就逃跑。”“意大利的那一群不也是,花言巧语、嬉皮笑脸,一直和我们套近乎。”“那群日本人倒是装聋作哑的。”
在押送途中,欧洲战俘们大多语言相通,因而会特意和苏联女兵们拉近关系,以期女兵们对其放宽管制,伺机逃跑。相反,黄皮肤、小眼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却从来不逃跑,这“安分”的日本战俘很快就吸引了女兵们的注意,将其定义为“听话的战俘”。
直到日本天皇生日,平日里闷不吭声的关东军战俘常有举刀剖腹自尽的。对此,苏联女兵们敬佩其高傲者有之,但更多的是为其血腥残忍的“献祭”举动而皱眉。
1945年11月,当第一批日本战俘被押送到坦波夫市前两日,列车内负责巡视工作的苏联女兵瞅见了日本人带的羽毛枕头、毛垫、厚实的棉裤棉袄、暖和的棉质睡衣等等物品,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但终究是好意提醒道:“好好享受你们的东西,不久就用不上了。”
日本战俘们不知所云,从女兵的表情和体态语勉强可以判断出大意,但多数人误以为是到达坦波夫市将收检他们的私人物品,对视一眼,没有作声。
然而,令日本战俘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列车们一打开,苏联市民,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市民们便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住了日本战俘们。
正当不少日本战俘们或面红耳赤地用日语婉言推拒、或稍稍诧异后便热情回抱之时,少部分人发现,他们身旁地大包小包被车站的孩子们大摇大摆地拎走了!彩照、颜料、画笔、调味料、枕头、毛垫通通不见踪影。
等到他们迷糊糊地从身材高挑的女市民怀抱中抬起头、解放身体后,这才发现,他们几乎脸裤子都不剩了。在整个车站的大笑声中,纵然恼怒,竟也无从发作,再加之多数人不懂俄语和英语,更是鸡同鸭讲。
然而,在劳作中,日本战俘们就不再像押送过程中那般老实沉默了,不少日本战俘喜欢同会说会笑的苏联女军官嬉戏,更别说期间还有懂得俄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凭借和苏联女军官言嬉之谊,可以干轻松的活,吃精细的面包,在温暖的小木屋里面喝上两口伏特加。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原本木讷的日本战俘也“开窍”了,会请求泥煤场附近的小男孩帮忙,送小礼物、阿谀奉承,美名其曰,搞好苏日“友好关系”。
等到了夏天,少数日本战俘们更是荒唐,眼见着监管、看守的军官都是女兵,就借口天气炎热,光着身子,在矿口乱跑,彼时15岁的看守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曾回忆道:“他们像小孩一样,手脚并用,在矿上互相戏弄,经常吓得我们的女孩子捂着眼睛尖叫。”
在苏联女兵中,甚至有传言,这群荒唐的日本战俘的行李箱里面藏有橡胶娃娃,即用来自慰的性偶,但是这些东西在车站被一抢而空,所以才惹得他们成日里总喜撩拨苏联女兵们。
在这些单方面的撩拨中,也有一些苏联女兵,尤其是女看守在成日的相处中,和其中学识、品貌都较为出色的日久生情,从而大胆示爱这些战俘。
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曾回忆自己当女看守那段时间,一天,一个日军少校找到了他,请求他和战俘营中另一名女看守——维拉调换一下夜班。维拉身材高挑匀称,皮肤透白,金发碧眼,笑起来却别具东方含蓄韵味。
鲍里斯·斯维里多夫虽然才15岁,就已经明白了一些男女之间的小密事。他一开始表示了拒绝,因为随意换班被上头知道了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推拒道:“这是不被允许的。”仿佛在说换班一事,又好似在劝诫他们的爱情。
可那个日本少校恳切地望着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求求您了,让我和维拉在一起吧,她已经同意和我结婚了。”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明白,维拉早前就有意这名日军少校,他突然就可怜起了两人:这毕竟也是爱情啊。
于是他同意了,可谁知第二天,满脸郁色的日军少佐就将维拉送了回来,并且骂了一句脏话。此后,这个日军少佐就再也没有纠缠过维拉了,并开始在战俘营里恶劣地传播流言:欧洲女人不适合日本男人。
自然,这其中又有着被德国战俘嘲笑身材矮小、眼睛短窄的缘故。然而,虽然日本战俘被德国战俘嘲讽“配不上高挑的欧洲女人”。
但是在整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年代,苏联女军官比起成日里和寡妇厮混的法国战俘,喜好十几岁女看守的德国战俘,她们对日本战俘勉强算是观感稍好。
一些十几岁就进入军营,且至1946年左右已有三十多岁,仍未婚配的苏联女军官平日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这群战俘,偶尔有一二男性同事,也多成家立业,有儿有女。军营枯寂,再加之一些日军战俘有意为之,不少苏联女军官会暗示日军战俘,可以共存一段露水姻缘。
何谓日军战俘“有意为之”?一方面,日军战俘和德军战俘多数有意较量,德军战俘喜欢和年轻娇美的女看守厮混,并借此对日军战俘上身到人身攻击,嘲讽其身高、外貌等等不讨苏联女人欢心。
在这种变态的异化环境中,不少日军战俘会有意在执掌实权的苏联女军官面前显露自己:身强体壮、通晓俄语、头脑聪明……以此来博得一位在战俘营中有地位的女军官情人,从而使其在日军战俘、德军战俘中拥有实在话语权。
另一方面,从1946年12月起,苏联开始分批遣返日本战俘,头两年遣返的日本战俘数量较少,所有的日本战俘挤破了头想要从苏联女军官那里开到一张证明,好早日回到日本和家人团聚。
怎样才能开到证明?很显然,能够遣返回国的那批人,必定不是挖煤挖的最认真的那几个,要想从苏联女军官,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女军官那里开到遣返证明,要学会讨女军官欢心。
苏联女兵在世界上都赫赫有名,二战中,苏联共有89万妇女参加了红军,其中更是有一半到了前线服役,许多部队更是清一色的“娘子军”,甚至还有三分之一的女红军配备了迫击炮、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等武器。
虽是战俘,但是同为军人,二者虽此间地位天差地别,但终有话可聊。苏联女兵中有30万妇女在防空部队服役,担任对空防御任务,妇女们甚至还参加了游击队,负责扰乱敌人的后方、切断补给线,是真正的战士。
对于热情开放的俄罗斯民族而言,夜晚时分,召一个日军战俘到小屋里喝喝烈酒,聊一聊过往,袒露一下从军以来担任坦克和飞机驾驶员的艰难和趣事,夸赞女军官的英雄勋章,调融气氛,再干柴烈火地睡上一觉,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但对于日本战俘来说,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伺候”好了苏联女军官,就可以顺利回国。
虽然苏联彼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但是女军官多的是可以挑选的余地,在二战中,苏联空军有三个飞行团有妇女组成,其中587轰炸机团、586战斗机飞行团、588夜间轰炸机团等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兵飞行团大大提高了苏联女兵,乃至苏联女性的社会地位。
作风顽强的苏联女兵之所以选择和战俘欢爱,更是喜爱那一种“钱货两讫”的爽利感,毕竟饶是苏俄,对于女性的桎梏仍然存在,女军官亦是如此。
而在战俘营管理局下面同样设立了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的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政治部主人1名、劳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管理人员中也不乏女性,她们负责战俘的劳动培训、劳动分配、生活起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等。
因而,能和劳改所内的女军官打好关系正是这群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能够生存舒适的基本保障,给主管劳动分配的女军官送点巧克力,就可以去温暖的室内工作,或从事农务工作。如果庄稼长得好,还可以收成马铃薯,获得食物。
当然,最好的工作是前往军官家中,帮他们丢废弃结冻的生活废水,这个工作轻松且较体面,还可以从军官夫人那里获得食物。
给生活起居的女军官一些进口的小物件,可以分到相对干净温暖的住所,在碰上不顺意的舍友时,还以为请她调换,这期间的油润关系自是大有讲究。
更不提战俘的劳动薪资微薄,扣除高昂的餐费和其他费用后所剩不多,只有一部分具有特殊技能(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的战俘,才能够真正领到劳动薪资。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军战俘成日里抽好烟、喝好酒,不用怀疑,他在军中一定有一个背景良好的女军官情人。
- 任俊.《1945中国记忆 日俘日侨大遣返》[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 潘晓.《二战风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美军性虐女战俘 美军俘虏一万名日本“女俘”,做一件事不打不骂
苏联是如何对待日本战俘的? 剃光男性体毛,羞辱30岁以下女性!
苏联红军进入山海关后,将男华侨关押在火车站附近的城内,准备运往满洲里集中关押。 同样,数百名日本女性侨民也被关押在私人住宅内。
这些特殊的女战俘的经历实在是太悲惨了。 说完女战俘,我们再来说说男战俘。 在苏联人眼中,这些战俘是填补国内劳动力短缺的宝贵资源。
日本战俘被分批押送到苏联内地。 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分配到远东和东西伯利亚。 还有少量被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罗斯托夫和南高加索的索顿河流域。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利用这些战俘,苏联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战俘管理制度。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被拘留者事务管理总局。 总局下辖多个战俘管理办公室。 还有很多劳改营。
日本战俘进入劳教所后,第一个程序就是接受隔离和政治审查。 隔离期间,战俘不仅要洗澡消毒,头发、腋毛等毛发也被全部剃光,衣服也放入烘干箱中消毒灭菌。
身体隔离结束后,还要进行思想隔离,检查他们是否有反苏罪行。 如果是的话,他们将立即被转移到特殊的战俘惩罚营接受惩罚。
当代,许多中国人民对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铭记在心。 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是最令人痛恨的。 日本女兵也被美军俘虏。 这些女兵受到美军的待遇如何?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对很多国家发起了征战,其中就包括当时实力比较强大的美国。 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报复美国未能提供石油。 这场意想不到的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珍珠港战役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因此美国人的回应是正式对日宣战。
战争期间,日本遭受了巨大的人员消耗。 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男子越来越少,甚至开始招募女兵。 战争期间,中美等国家用人道主义精神对女兵施以怜悯,但日本女兵在战场上却十分英勇,对敌人毫不留情。 日本女兵有不同的用途。 有的年轻漂亮。 经过训练,他们成为间谍,窃取情报,刺杀敌人。 有些被日本天皇用作炮灰,并赠送给其他国家。 在与美国的战争中,许多妇女被日本天皇毒死,与许多美国士兵一起死在战场上。
美军对这一恶招极为愤怒,在随后的战斗中俘虏了近万名女兵。 有人认为,当时美国宪兵的管理极其严格,没有人敢侮辱他们。 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不如把她们送给当地的土著人当妻子。 这样的话,原住民不会对美国的战争更加怨恨,反而会感激他们。 可想而知,这些女兵交给当地原住民后,她们的生活如何。 这些土著人民与外界隔绝,这些女兵也无法逃脱。 从此,他们将开始语言不通的尴尬生活……
您认为这种待遇与日本人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相比如何?
越战故事:光腚战神(下)
陈栓柱对受教育最多又退化最快的军医刘少明一直表示不敬。陈栓柱和刘少明住在相邻的两个洞里,来往也比较密切。他们这一带的洞口极小。陈栓柱身材瘦小,进出自如,刘少明身体稍胖,进洞必须头朝外先卧倒,腿脚先进洞,再抬进屁股,再上身,再头,最后才是双手。陈栓柱常常见刘少明来了,就在里面恭候,等刘少明屁股进来的时候,就用树枝戳他的屁股。洞内多蛇,时不时还能见到白尾梢的大蝎子,这下屁股上来这么一下子,刘少明吃惊不小,他打个激灵,“嗖”地一下子又窜出洞外,摸摸屁股,看看有什么损失,发现没有被蛇或蝎子啃咬过的痕迹后,就向洞里喊:“哪个?”
不管是“哪个”,刘少明也奈何他不得,因为他进洞困难,骂狠了你进洞时,就有人挠你的脚底和软肋,叫你进不能,出不得,活受罪。刘少明胆小,这事在他身上屡试屡中,百无一失。有时,待他进了洞,陈栓柱一把抓住他的大胡子,说:“你敢动!”这时,刘少明就马上求饶。每逢这个时候,陈栓柱就会“教训”刘少明:“叫你光屁股蛋儿。”
刘少明拿陈栓柱没法,用他的话说,陈栓柱是“油盐不进”。他绞尽脑汁从生理角度和医学角度向陈栓柱宣传不穿裤头的好处,但陈栓柱就是不听他那一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些首长们为啥还穿着裤头?你怎么不对他们说去?”刘少明无语。
刘少明没有感动陈栓柱,陈栓柱是被他自己打败的。
洞内缺水,常常发生洗裤头还是喝到肚子里去的痛苦决策。裆里捂出痱子,奇痒难挠,要屁股还是要面子的事情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其他战友好办,先上到阵地,大家一起脱,彼此彼此,大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陈栓柱不行,这个阵地他来得较晚。来晚了就来晚了,他还到处取笑那些光屁股蛋儿的人,他的这些战友们对陈栓柱“同仇敌忾”,倒要看看他陈栓柱能坚持多久,更要看看它去掉裤头后,要害部门与大家有何不同之处。陈栓柱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可说到底还是要屁股和要面子的问题。
直到有一次,陈栓柱看到一个和他信仰相同的不光屁股者,患了烂裆,裤头粘连在皮肉上,当裤头脱下来时,一层烂皮也随着掉了下来,既没有保住面子,也没有保住那地方。只这一下,陈栓柱就狠下心将裤头褪了下来,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尽管心里发虚。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拿他打趣,更不要说嘲笑他了,只是他们有些小小的遗憾:看不到穿裤头的人就像看不到珍稀动物。
陈栓柱终于加入到了光屁股蛋儿的行列,也加入了大家的思想体系。现在他才明白,外在的东西,大家都差不多。自从加入到光屁股蛋儿的行列后,安全系数也提高了好几倍。越军的观察哨到处捕捉狙击手,而狙击手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光着屁股蛋儿东奔西忙。对于越南人,他们最恨的就是狙击手,一旦发现,不光打枪,而且还赏赐迫击炮弹。对于光屁股的人,他们也打枪,但很少用迫击炮打。陈栓柱也是如此,在他的狙击战果中,虽然有一定比例的裸体军人,但据战后调查表明,他所击毙的穿着军装和裤头的几乎都是越军军官,于是,他在狙击时,会优先考虑赏几粒子弹给那些穿着军装和裤头的越军。对于越军女兵,他却例外,女兵很少裸身光屁股,但是洗澡、上茅坑,她们全不遮挡,有时洗完澡还赤条条地向中国兵摇摇手中的毛巾。
不久,陈栓柱所在的连队换防了,换到一个离敌人更近的地方。陈栓柱所在的阵地夜里情况特别多,树叶哗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开始的时候,战士们犯紧张,一听到响声就嘟嘟嘟、砰砰砰打枪,咣咣咣、嗵嗵嗵地扔手榴弹,第二天又是如此,天亮后派人下去看,没有人的脚印。后来终于发现是猴子吃垃圾。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
后来,这些猴子和光屁股兵混熟了,常来做客,与战士们同吃同玩,玩够了,一声唿哨,自顾自地开路。可是,人是人,猴是猴,又各不干扰。这些猴子和人接触多了,猴子们学会了抽烟,握手。这些光屁股兵都是年轻人,好玩逗乐是他们的天性。有时候猴子来了,他们就使坏,给猴子吃大蒜,猴子吃了,辣的不行,双手捂住腮,又是蹦又是跳,还不停“吱吱”地叫唤,以后见到大蒜,就不再吃了,却从来没有怀疑是这些人在捉弄它们。
和猴子处的时间长了,光屁股兵们发现人身上的毛越来越长,有的说,这是长时间呆在洞里捂出来的;有的说,是长时间不穿衣服的缘故;还有的说,人身上的毛是猴给传染的。但这句话说出来反驳的人最多,理由是,人身上只有七毛:眉毛、睫毛、腋毛、阴毛、肛毛、鼻毛、胸毛,而猴子却有八毛,比人多身上的那一毛就是身上的猴毛,两码事。不管几码子事,光屁股兵开发新节目,与猴子比毛的长短,有的地方是人的毛长,有的地方是猴的毛长,各有优势。会抽烟的猴子还是猴,它不会是人;长毛的光屁股兵还是人,他不会成为猴。
艰苦的山洞,猴子是不会进去的,猴子也怕苦,当然更怕蛇。猴子不进洞的占多数,因为里面的日子难以想象。
陈栓柱的猫耳洞离敌人的洞口只有五六米远,中间隔着一块大石头,看得见越军的哨位洞口。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敢抽烟,因为对方通过那一点点小小的火苗,就会打来一枪,弄不好会丢了小命,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们抽烟的时候,就在烟上套一只罐头盒。越军的洞口大,人可以猫着腰进去,陈栓柱所在的洞口小,需要爬进爬出。陈栓柱和战友们在洞里和越军互相敲洞壁,一敲就能听见,听见了就向他们喊话:“缴枪不杀!”用越语喊。越军也喊,学中国士兵的腔调。越军很浪漫,没事的时候弹吉他,弹我们中国当时最流行的“十五的月亮”,弹得挺好。有时,敌我双方跟着吉他的节奏放声歌唱,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是敌我双方拼命厮杀的战场,还是中越两国士兵的演唱会。有时候中国兵探出头去,越军也探出头来,但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就不约而同地缩了回去。
通过观察,陈栓柱发现,越军只有三个士兵,越军的头发比我们的长多了,而且和中国士兵一样,都光着屁股。此时,正值雨季,人在洞里呆着,沤的骨头缝都是疼的。陈栓柱受不了,便爬出去晒太阳,有个越军也爬出来晒。从洞口爬出来,陈栓柱没有带枪,想扔手榴弹,保准一扔一个准,但敌我双方谁也钻不进去。两个洞口的石台都不大,也没法搏斗,下面就是悬崖。
陈栓柱喊老越一声,想把他吓回去自己好美美地晒上一晒,那个越南兵根本不理,光着个屁股在那儿看书,看都不看陈栓柱一眼。陈栓柱以为他看书入了迷,又喊,那越军听见了,还是不理,索性岔开两条褪晒裆,陈栓柱也学他。这样,陈栓柱和越军相距不到六米,谁也不理谁,各晒各的裆,说不出的舒服受用。晒够了,越军一钻就进洞了,还向陈栓柱打手势。陈栓柱不敢怠慢,也急忙进洞。进洞迟了或者慢了,说不定对方就会飞来一粒子弹——大家都这么想。
敌人开始进攻了。洞口用编织袋堆成的公事被越军的枪炮打的千疮百孔,哨位前的那颗相思树,被敌人的子弹打得像蜂子窝一样,树皮都剥光了。前沿布满了弹片、弹壳,工事内满地都是手榴弹拉火环、弹壳。
陈栓柱已是第三次负伤了。当他撂倒第七个敌人时,敌人已扑到跟前,他迅速换了支冲锋枪,冲锋枪的枪管打红了,抛下,换一支再打。
突然,敌人的弹片溅到他的脸上,他用手抠出来,没有停止射击。接着,又一块手榴弹碎片飞进他的大腿,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端起了枪。现在,已经有2000发子弹和两箱手榴弹被陈栓柱送给了越南兵。
雨开始哗哗地下了起来,雨水冲刷着山梁,和着那些被炮火炸的变得松散的泥土一起向洞里涌来。陈栓柱一边堵水,一边注视着敌情变化。他和战友赤裸裸的身上,都裹满了泥浆,泥浆中夹杂着细小的弹片······
敌人又一轮进攻开始了。突然,正在激烈射击的陈栓柱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陈栓柱,陈栓柱,你来压子弹,我来射击!”
不用看,陈栓柱就知道是刘少明。这个家伙,来这里发脾寒药,正好遇上这场战争。陈栓柱没有理他,只是用手指了指散落在地上的弹匣。刘少明收拾起一大推弹匣,到里面压子弹去了。
“轰”的一声,敌人投进来一颗手榴弹,在陈栓柱身边爆炸了。正在压子弹的刘少明听到这个很近的爆炸声,接着听到了陈栓柱的声音:“老刘,我的腿断了······”
刘少明转身扑过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颗手榴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了,陈栓柱用身躯挡住了那无数飞溅的弹片。
两个血肉身躯倒下了。
刘少明从血泊中爬起来,发现自己的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猛地把肠子往肚子里一塞,左手捂住肚子,右手操起冲锋枪,向敌人投弹的方向猛烈扫射。
敌人被打退了,刘少明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他看到了陈栓柱,掏出急救用的三角巾,想为陈栓柱包扎,可陈栓柱身上到处是伤,刘少明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
陈栓柱听到了刘少明的呼唤,睁开眼,动了动嘴唇。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好渴。”
刘少明摘下军用水壶,壶上布满了弹孔,水早就漏空了,洞里的水全是泥浆······
陈栓柱躺在刘少明的怀里,“小陈,小陈——”刘少明千呼万唤,陈栓柱的脸上再也没有一点反应。
雨住了,战斗结束了。刘少明昏昏沉沉听到了排长的呼唤。他醒了,看着陈栓柱,他哭着喊:“小陈,我对不起你啊!我不该让你射击,我独自一人进洞压子弹。我没有把你照顾好,没想到,你死得这么惨。”
陈栓柱前身被炸开了,到处是伤口,伤口里钻进的弹片数也数不清,刚刚长了十九年的身子,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么多弹片,每块弹片都会夺走人的生命,而这些弹片竟是在那一瞬间同时钻进了这个可爱的狙击兵的身躯。
战友们洗掉陈栓柱身上的泥浆,然后小心地给他穿上衣服。这个在老山前线光着打过无数仗,击毙过无数越军的光屁股蛋儿英雄,终于穿上了衣服。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