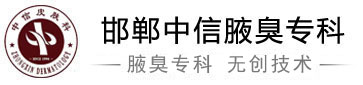喝酒的男人,有多少都是酒腻子?
太阳红彤彤的,好几片晚霞围绕着,它不舍得下山,好像看着我熟睡的样子,没够。
我正在睡梦中,驾着一辆新买的福特野马,在人烟稀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驰骋,天上有几只雄鹰,盘旋着,嘎嘎地叫,那声音好像刚出生的雏鸭,特别动听。
天渐渐黑了下去,我在等待着一个人,和她约好了的,一起去露宿,拍夜空里的星星,她想要看看星星的轨迹,我告诉她,要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就可以。
我正等着她的电话。电话铃声响起,我踩住刹车,车辆停了下来,四处寻找手机,却不见手机在哪里,铃声不停地响,我开始焦躁不安,怀疑是不是车开得太快,手机自己飞了出去。
可是那铃声持续不断,我大急,骂了一声,谁特么拿了我的手机?忽然就醒了,手机就在床边,兀自响着,我出了一口气,谁特么打扰我的好梦?
拿起来一看,是老松。
老松约我吃饭,说要介绍一笔生意给我。
我本不想去,他坚持说是一笔大生意,联系了很久,错过了可惜。
在老李家羊蝎子店,老松拎着一瓶牛栏山二锅头,对我说;“酒厂专供,十五年老曲。”
一股酸腐的臭味儿飘来,像馊了豆浆,地窖里的烂白菜,狐臭的混和气体。比第一次喝老北京豆汁儿还要恶心。老松坐在我对面,一嘴的口臭,熏得也睁不开眼,却不敢皱眉头,他很介意别人嫌弃他的口臭。但是每次他都自重,偏爱往人脸前凑。
老松把脑袋贴近我,我感觉整个饭店都是他的口臭味儿。羊肉的骚竟被盖了下去,这真是一门绝活。
他悄悄地对我说,这家的羊蝎子味道特棒,不是熟人,吃不到上好的。“我有关系,我跟这老板熟悉,你今天就请好吧,包准让你吃上美味儿。”老松对我挤眉弄眼。
服务过来后,他拿出一幅北京爷的派头:“认识我吗?你们老板在不在?今儿我有贵客,给我上一盆脖子,不要掺假!”
服务员是位姑娘,干净利落,很礼貌地笑了笑:您放心,我们这里的肉错不了。
菜没上来,老松拿起二锅头,拧开,倒了二杯,推一杯给我:一人半斤,慢慢喝。
我惦记生意的事情,迫不及待地问。
老松摇了摇头,故作神秘:别急。
一大盆羊脖子上来,老松把火力开到最大,一会儿就咕嘟起来。他拿起筷子,把肉都扒拉开,均匀地沾上汤,先嚼了一个芝麻饼,看看肉已经烂透,便夹起一块放到自己的盘子里,用筷子指了指锅:你也来一块,别等了,尝尝,绝对震了你!
我端起酒杯:松哥,来,敬你一个。
“哈哈哈,兄弟,今儿咱们来个痛快!”
一仰脖儿,一杯干了下去,我给他倒上,他扒拉着羊蝎子,嘴里满满的,不住地吧唧。
三杯之后,老松的额头冒了汗,鼻子下方的人中里,聚集了一滩稀稀的粘液,被灯光一晃,闪闪发亮。
他来了兴致,滔滔不绝,说得都是些单位里的烂事,情到浓时,站了起来,一只手支着桌子,一只手冲我摇晃着,嘴里的肉渣渣和唾沫像浴房里的花洒,绕过羊肉锅,直喷到我的脸上。
这简单比口臭更令人恶心。
我胃里翻江倒海,忍了几忍。
“松哥,生意的事儿?”
“着什么急,没看我正说事吗,你咋就没点儿耐心,告诉你,兄弟,做大事,要有耐心,不能急,你看我,啥时候急过?”
十一点多的时候,老松已经喝了他自己带的十块钱的二锅头,以及我又饭店里要的一瓶板城烧锅。
饭店里的客人陆陆续续走了,只剩下我们俩。
服务员已经把周围的桌椅都收拾干净,面露焦急地看着我们。
我忍受了老松一晚上的口臭和唾沫,这个时候,已经麻木,看了看表,对他说:松哥,天不早了,今儿就这样吧。
“别介,兄哒,兄哒,不是哥哥吹,在这个饭店,咱不走,没人敢往外撵,你听我说呀,谁特么敢,我收拾他个啥比——他的比字还没落地,一坨东西从嘴里喷出,直往我脸上袭来,我一闪,“啪”一声摔在了地上。
“草,我牙,我牙,我的牙——”老松呼喊着。
一个50多岁的服务员走过来,从地上捡起他的牙,递过去。
老松接过来,迅速放进嘴里:“兄哒,哥哥喝多了,让你见笑,今儿我结帐,服务员,多钱,给优惠点儿!”
到了前台,他拿出手机,捯饬了半天,没有网,打不开付款码。他在那里磨磨叽叽,我早已经结完。
他见我拿了发票,很不高兴。
“兄哒,咋能让你结帐,你不够意思。这发票给我,我单位能报,我帮你报,等报完,我给你微信红包,你一定要收,你要是不收,以后咱哥俩算完!”
出了门,我帮他叫了一辆车。
他把住车门不上,非要给人打电话。
他拿起手机,放到耳边,等了半分钟,开始说道:老崔呀,你丫不够意思,今天我的贵客等了你好久,说好的生意,你咋没来?你这不是叫我丢面子吗?下次,记住,下次别再叫我没面子!
……
后面的话我都没听,我只知道,打从他拿起手机放到耳边起,那手机的屏幕就一直没有亮过。
那年在非洲安哥拉参加黑人聚会时烤肉 我在非洲安哥拉的日子193
2014年跳槽后在嘎妈妈区诺阿伟达小区办公时,每天周末隔壁的黑人同志们都会举办晚会、烧烤。弄个大音响叮叮咚咚放上半宿,虽然他们也热情地邀请了我们几次,但是总觉得参加他们的舞会有一些尴尬,所以一直就没有去,想知道就老远地用相机上的200镜头看看异国他乡的人是怎么过周末的就行了。
有一次和我们在同一栋大楼上班的一个当地的官员得知我们住在诺阿伟达,高兴地对我们说他也在那住。并邀请我们周六晚上过去玩,当时也是为了礼貌就答应了。
我们住的与这个黑人官员家离得并不远,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前面就是贫民窟,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不到500米,我们还没有没有开车,带着保安溜溜达达着就过去了。见我们过去了黑人太热情了,只是一些乱七八糟风俗受不了,而我也不会跳舞这种高难度的活动,再加上年龄大了再把腰扭了不值当的就坐在一边品着据说是法国的葡萄酒,喝了两口感觉也就那么回事,没有花生米配牛栏山的畅快、少了一份酣畅淋漓、少了一份喝酒的洒脱、多了一份想要个拍黄瓜的冲动。
音乐放得很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DJ,只听到音箱里传来一个黑人女人撕心裂肺地叫喊,黑人们跳着当地的舞蹈,好家伙,昏暗的灯光下几件白衣服与大白牙来回跑,太刺激了。我可没敢拍相片,闪光灯一打这帮黑人还不把我给扒老皮?
在我看来,那么大的音乐声、一堆人挤在一起太影响身体健康了。更要命的是不流通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香水味混合着狐臭的味道刺激着鼻腔,可是要了亲命了,这洗洗再出来玩不好吗?我觉的还是离远点以那狐臭免传染到我,其实我不知道狐臭是不传染,只是不习惯闻这个味罢了。
于是就坐在椅子上大口小口地喝着葡萄酒看着他们,观摩着、学习着,体会异国他乡的人文、感触着大西洋海风带来的凉意,没有拍黄瓜的桌子让我越发显得酒不好喝了。
当我看有个黑人在一边支起了架子在烤肉,笨手笨脚的手法比较粗糙,一时手痒(主要是闲着看别人很尴尬,再加上我需要点下酒菜什么的)我就可去帮忙了。一上手才发现他们调料中除了盐没有其它的,可怜的非洲人呀。
得,打电话让司机把我们烤串的那些东西送了过来,包括刷子、扇子、孜然粉、胡椒粉、辣椒什么的东西全给我拿了过来。
结果黑人同志一看这些东西,觉的我是在配中药,问我是不是要制作药品,我心里说:拉倒吧,瞧这没有见过世面的嘴脸。烤串这一门高深的学问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告诉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好东西,吃了可以活很多年,我都差点说是中国耶稣教的我们了。
他们的肉是放在一个铁丝网上烤的,边上扔着一只羊,割几块扔在上面就行了,下面是一个大油筒(汽油筒没有顶)我就在那一边刷油一边翻,不好烤,块太大了,后我就我切了小块,让黑人帮我切的,一条一条的,我就用摄子来回翻,撒上少量的的辣椒、孜然、胡椒什么的。烤到5分熟时就放在一边让它焖会,然后再烤其它的。来回折腾了半天,才烤出外焦内嫩,香味十足的肉。
再次撒上大大的辣椒、孜然、胡椒什么的,磕吧磕吧,就喊他们过来吃,其实也不用我喊,他们早就闻着味说母一杜蹦了,只不过是没有过来守着我罢了。吃得很快,我觉的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就全吃完了,然后有黑人人说下周还来烤,可拉倒吧。
也许是我习惯了我中华美食,总感觉其它国家吃食不是那么回事。
别人总以为我身处在遍地金银异国他乡享受着荣华富贵驱使着无数佣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谁能想到五十多岁的我午夜在AK枪声中惊醒后藏在墙角像个柔弱的、受了委屈的孩子瑟瑟发抖。本来以为经历多了就到处炫耀并能彰显自己人生的厚重,谁料到生活在给予我阅历的同时让我遍体鳞伤。加油,兄弟。狐仙2021.6.24
北京这两个地名,你都不好意思喊出来
趣说北京地名
今个儿小编就和大家说一说北京的地名
初到北京的人一定对北京的地名感到奇怪
甚至老北京都不知这些地名的由来
比如北京有很多村很多屯
最著名的就是中关村和三里屯
不知道的外地人
可能还以为北京是个大农村呢
小编工作的地方就在魏公村附近
我可要强调一下不是农村哟
甚至有朋友曾经在八王坟工作?
还有许多以数字命名的地名,比如说一亩园,二里庄,三里屯,四道口,五棵松,六里桥,七棵树,八王坟,九龙山,十里河,东四十条,东四,西四,百花深处,千福巷,万泉河……从一到十,个十百千万全都有,可以说,巧记北京地名,小孩的数学一定不会差。
动物的名字也不少,马甸桥,骡马市,亮马河,牛栏山,学会这些地名,认识家畜不成问题了。
当然小编今天要说的是两个最不忍直视的名字!
如果你正好要去那儿
你都不好意思和朋友说
这个两个地名是——骚子营和奶子房
咋一听名字是不是感到很粗鄙?
北京市千年古都
这名字也取得太俗了吧?
但北京人就是这么任性!
骚子营
位于海淀区
在北京市圆明园西侧
这个词的来源和元朝有关
当时汉人称呼蒙古族人的时候不好叫
统一称为鞑靼(dádá)
在鞑靼入侵之前
老百姓只是听说过他们
没有过身体接触
后来元朝建立之后
大批的鞑靼和汉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
汉人发现这帮人有狐臭
于是就在从前的称谓之前加了一个“骚”
变成了“骚鞑靼”
可老百姓总觉得这么说不顺嘴
还容易让蒙古族人听出来是在骂他们
渐渐就演化成了“骚鞑子”
由于当时圆明园曾驻扎大量蒙古兵军营
改朝换代之后
老百姓就叫这里为骚鞑子营
久而久之
变成了现在的骚子营
如果你正好从市里
乘坐公交车前往颐和园
在路上还可以看到骚子营的公交车站呢
奶子房
再说奶子房
骚子营在西北边
奶子房就则在北京城的东北边
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
相传还和成吉思汗有关系
公元1204年的寒冬
成吉思汗被仇敌篾古真追杀
一路流亡到该地
断粮断水之际
被一少妇用奶水所救
后来建立蒙古帝国后为感恩该女子
成吉思汗建立了奶子房
之后“奶子房”成了多数蒙古贵族欣然向往的养马饮奶地
(相当于现在的VIP俱乐部场所)
随着蒙古铁骑的西征
“奶子房”也先后在西方各地设立了无数处分点
但到明朝
在北京奶子房就消失了
直到清朝建国后
与大清爱新觉罗家族联姻的蒙古博王向皇太祖申请建议重建“奶子房”得到允许
“奶子房”才重见于历史
且覆盖范围有所扩大
至清朝末年
该地人口已近7万
怎么样?
看过了这两个地名
是不是大跌眼镜?
北京市怎么不把这些名字改一改?
其实也有代表曾经建议规划部门邀请专家对地名进行改造
但也有北京史学专家认为
违反当地人文特征的地名理应修改
但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叫得响的、当地群众认可的地名
是“北京城市的记忆”
不能抹杀
你觉得要不要改呢?
其实小编觉得
地名作为北京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有必要进行保护和研究
从而使人们更广泛地了解北京
认识北京
热爱北京
今天这个主题
小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好
小编下回继续接着讲
留言为我打call哟!
如果你还知道哪些奇怪的地名
欢迎在下方留言说出来
京彩台湾,给你精彩!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号 bjstb2017)
长按识别二维码 关注京彩台湾
京彩台湾 给你精彩
京彩台湾
微信号 : bjstb2017
文字:谭 青
美编:杜舒扬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