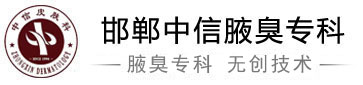戈壁上的车站
一
16岁时,父母允许我独自回故乡。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远行。
出发前,打听到油田一辆小车去柳园接领导,想搭个便车。那司机看我带着五个包,便立马拉着脸,勉强让我上了车。车上坐着一个搭便车的漂亮女人,她与司机一路上聊得火热,都不理我。不一会,我发现自己憋着一泡尿,他们俩每笑一次,我都会被尿憋得打个颤抖。年少羞涩,我不敢给司机说停车撒尿。经过漫长的两个多小时,车到柳园时,我都快憋疯了,背着扛着几个包,匆匆跑进人满为患的候车室,却发现里面没有厕所。没办法,把五个包扔在地上,先去解决燃眉之急。在广场西侧的厕所撒完尿,听见街上书店的喇叭里放着一首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费翔唱的,满街人都能听到。想到即将面临的枯燥旅途,琢磨是不是买本书路上看。反正是兜里有钱,可以自由支配了。出了书店,又觉得肚子饿了。想进小饭馆吃饭,又怕扔在候车室的几包东西丢了,自己跟自己不停地打赌:东西丢了?东西没有丢?假如丢了,就骗父母全部带到了。在车站外晃荡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候车室,发现除一个工作人员在扫地,人全走了,我的五个包完好如初地躺在地上。
那是坐火车的淡季,顺利买了一张硬座票,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但每人都躺着,各占一排位子,谁都不让座。我想找个空位,拎着五个包走过若干个车厢,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两个中年妇人坐着。没有退路,没有商量,我一屁股就坐下了。总算消停下来,望着窗外快速移动的戈壁,我的心已经飞向远方幻想中的大城市。
一个月后回到柳园,已是下午,拉原油的车都走完了,没法搭便车。身上仅剩几枚硬币,走投无路时,想起在敦煌读中学时的同学建国、建利,他俩是双胞胎兄弟,家在柳园,便去找他们。他们家在西藏商贸公司驻柳园货场里的一排平房,父母年龄很大,说一口陕北话,咳嗽不停地着接待我。在弥漫着中药味道的屋里吃了丰盛的晚饭。晚上与建国、建利两兄弟睡在他家的炕上。建国话很少,总是在看书学习。建利善谈,与他聊得很晚。夜里总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火车驶过的声音,每次建利会卖弄着告诉我:这是70次去北京火车;这是54次去上海的火车;这个嘛,是一列货车……
临睡前,又听到火车声,问他这是到哪里的火车。他迷迷糊糊说,这是一列往东开的油罐车。不知他是在蒙我,还是真能听出来,反正挺佩服他。
第二天,两兄弟留我玩一天。柳园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带我去戈壁滩,抓蝈蝈。柳园的蝈蝈与其他地方的蝈蝈不一样,母蝈蝈长着一把日本刀形状的尾巴,是产卵器,公的蝈蝈没有。柳园的戈壁滩草很少,但长着一种草当地独有,我们叫它箭草——拔出草根,直直的,硬硬的,乳白的,根的底部像一个箭头模样,也不是很尖,像显微镜下男人精子头的造型。
三人一路走了很远,到了铁路边,玩他们儿时的游戏,在铁轨上走平衡。
还有一个惊险的游戏是听火车。我们趴下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火车驶来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看到火车头一点点接近,让火车司机发现,有的便来一声尖利的汽笛声,有的会紧急刹车,有的也仿佛没有看到我们一样,反而加速。总是到火车逼近的最后时刻,我们才起身逃离铁轨,狂笑着飞跑起来。玩了几次觉得无聊,建利又有了新花样,问我想不想要把刀?我说如何得到,他便拿出一根半尺长的铁钉,放在铁轨上,不一会火车开了过来,几分钟后,铁钉被压成了锋利的铁片。我拿出了一个硬币,如法炮制,被压成了薄铝纸。回去后,建利给那铁片安了一个木把,真成了一把刀,送给了我。我发现他家里大大小小这种刀很多,有用的和不用的。
高中毕业,建国考上了清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鼓励我当一名优秀的石油工人。建利考到北京的一所民航系统的学校,他们父母退休搬回老家,此后我与两兄弟失去联络。
此后,再过柳园,便没有可找的朋友了。
二
我当了石油工人后,有一年冬天,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赶到柳园。卖火车票的窗口已关,候车室改为凭票进入。
要等第二天才能买票,我到哪里过夜呢?瞎转悠一阵,花一块二,买了瓶小角楼牌的白酒,准备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两口取暖。走进托运行李的房子,门和窗户都没安装,雪花都飘了进去,里面与外面一样冷。地上整整齐齐地睡着一排藏族人,像无生命一样悄声无息。窗台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藏族男人,极像佛像中人物,嘴里默念着经文,手里不停地摇动着经轮。我仔细观察他的脸庞以及服饰,他当我不存在,压根都没有瞄我一眼。不一会儿,隐隐约约听到有小孩的哭声。只见这男人挪动了一下身子,右手伸进胸前,从藏袍里摸出一瓶酒,放在了窗台上;接着又摸出一条羊腿,放在了窗台上;再摸,竟然提出一个光溜溜、黑乎乎的小孩,也一把放在了窗台上,那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又摸,摸出一把屎,直接扔了出去。然后,他再按照顺序把孩子、羊腿、酒依次放进象百宝箱似的胸口,小孩便不再哭了。
车站外非常寒冷,溜达一会就冻透了身子。广场上已经被飘飘洒洒的雪染白了,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只狗狂叫了两声,飞快地跑过,广场对面录像厅喇叭里的武打声音却很响亮。
我犹豫是找小旅社住下,还是去录像厅看个通宵录像,最后还是决定看录像——看录像两块钱,比住旅社便宜两块。
录像厅老板是个老头,嘴里镶着一颗金牙,满脸皱纹里写着“烟酒”二字。交钱买票,拎着酒走进放映厅,烟雾腾腾,看不清前面的录像画面。一股热浪扑面撞来,刺鼻的煤烟味,搅和着脚臭、屁臭、狐臭、莫合烟味,差点把我熏倒,不过没到一分钟就适应了。放映厅里几乎坐满了人,墙上贴着周润发头像画,旁边隐隐约约写着“禁止脱鞋”。仔细打量四周,看录像的人长得都很奇特,有的面目狰狞,有的胡子拉喳,有的像街头乞丐,全都不像这个地界上的人。或许他们是附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或许是与我一样赶火车的过客,无从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摸索着到第二排,找了个空位坐下,搓搓冻僵了的手,侧目看了一眼,邻座是相拥的一对男女,男人将手从女人毛衣领放进她胸口。猛然感觉这女人真好,用胸为男人暖手,我要有这样一个女人就好了,可又一想,他妈的放映厅里很暖和。
电视机里播放着《陈真》,以前看过的连续剧,陈真与日本浪人在比武,正打得欢实。霍元甲与陈真,是80年代人们最熟悉的武林高手。
点上支烟,拧开白酒喝了两口,身子渐渐暖和起来,困意随之袭来,没多久竟迷迷糊糊睡着了。长条木椅睡着不舒服,不知道过了多久,睡得脖子疼,起身出去撒泡尿,活动一下筋骨。外面雪下得很大,厕所太远,大街上没人,就地解决,用热尿在雪地上刺,画出一颗大树。
返回录像厅,在满脸烟酒的老板那买了包瓜子,回到座位,发现那瓶酒没有了。我站起来大声问:“谁拿了我的酒?!”没人吭声,没有办法,只好算了。
又囫囵看了一集,一大片人都睡了。大约夜里3点钟,突然,一个看似很凶恶的人在人群中站了起来,呼喊录像厅老板:“停!”他让暂停放映,要撒尿。第一次知道录像厅还能这样,可以暂停,集体去撒尿。灯亮了,录像停了。歪七八糟看录像的人一下子精神了,聊天的、骂娘的、吃东西的、抽烟的、出出进进的,屋里乌烟瘴气。直到那个喊暂停的牛人回来,老板才继续播放。没几分钟那人又大声喊叫:“放点好看的!”老板磨叽一会儿,真换了磁带,播了一部毛片。所有人顿时瞪圆了眼睛,精神头来了,吞咽着吐沫目不转睛,侧目看到邻座的男人,已经把手放到那女人的裤裆里暖和去了。
不到一小时,看得正酣,录像突然停了,又开始播放《陈真》。老板嘟嘟囔囔地说看看就行了,公安查得紧,查到就会把他和大家全都抓起来。
熬到早晨,我挤上一列东去的绿皮火车走了。
三
柳园坐火车,人多票少,碰到出行高峰期,买票极难。我去重庆上学那年,暑期到柳园坐火车,不光是买不上票,有票的都上不去车,有的火车只让下不让上,有的火车连车门都不开。
那次,在柳园晃悠了两天也买不到火车票。晚上打发时间,溜跶到东边铁路局家属院,碰到俱乐部正在举办交谊舞会。我幻想着能有场艳遇,认识一个铁路上的女人,以后帮着买车票。这么寻思着,进了舞厅,邀请几个女人跳舞。可一旦说出意图后,她们对我这个过客马上就没了兴趣。
第二天,继续在火车站溜跶,遇到一个从外地归来的朋友刚下火车,与他寒暄一会,得知小学同学小东在油田柳园库工作,于是马上就去找小东。我和小东多年没见面了,他非常热情地请我吃饭喝酒,聊小时候的事,很开心。到了晚上,安排我住他的宿舍,他与别人去挤着睡。他的宿舍是我见过最简陋的宿舍,中间放着一张麻将桌,靠里是一张小床,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喝得有些晕头晕脑,就倒头睡下了。
一觉醒来,发现屋里挤满很多人,围着麻将桌观战。我起身去看了看,小东把我介绍给大家。他们都很客气地邀我打麻将,我还是头晕,推辞后继续睡觉。其实也睡不实了,到了半夜,这些人压低了话音,他们声音越低,我越是感兴趣地听。大概听明白了,他们分工,要去偷一个库房里的物资。一两点的时候,灯关了,人都散了,我才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小东推着一辆自行车进了屋,其他人也陆陆续续来了。他们先是看看我还在睡,就压低声音说话,大概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偷上想要的东西,只弄回一辆自行车。
早上,小东叫我起来去吃早饭,他用偷来的自行车驮着我,去柳园繁华的火车站对面大街吃羊肉粉汤。路上,我想给他说点什么,但又没法开口。
吃完羊肉粉汤,我急着要走,小东找到火车站的朋友,还真弄上了中午出发的车票。他回去上班,我们就此分手。
那一年,寒假没回来。第二年的暑假我才回来,到柳园去找小东。到他宿舍门口,门被一把大锁锁着,问了几个人才知道,他们那些年轻人都因盗窃都被判刑了,有判十几年的,有判两三年的,小东被判了五年。我非常惊讶,内疚好长时间,后悔当初应该劝劝他就好了。
几年后,我在油田一线的电视台工作,在大街上偶遇小东。我很激动,他却面目冷漠,眼神不敢直视我,他变了。听别人说他在牢里被人干了,脑子受了刺激,刑满释放后,回油田二次就业了,三十多岁也没有成个家,此后在也没有见过他。这么多年,不知道他过得如何,是否娶妻生子。
四
到柳园坐火车,自己买票难,帮人买票更难,往往要托关系搞票。
有一年,单位电视台领导给我交代一个任务,去柳园帮他买张卧铺票。临行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到了火车站,直接去找站长,给过信就能拿到批条,买到卧铺票。
我搭便车赶到柳园,找到一位胖胖的站长。结果那胖站长看完信后,当着我的面,把那信撕扯得粉碎,往地上一撒,说声没有票,转身就走。
任务完不成没法交差。就给领导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领导不说交信的事,只训斥我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要我想办法,就是连夜排队也得买到,买不到卧铺票就别回来。我只好去售票窗口排队,哪知道那天排队人太多,多数都是票贩子,排队也买不上。没法,我只好与一个票贩子联络,买一张票要加100元钱。
这个票贩子看起来文绉绉的,夜里,我绞尽脑汁与他聊天,聊社会、聊国际、聊历史、聊生活、聊女人,使尽力气聊。半夜,还给他买方便面、火腿肠、榨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终于开窗卖票了,卧铺买上了。那票贩子给了我票,说不收那多加的100元钱了,可以和我交个朋友,以后想买票都可以找他。我们互留了地址和电话,记得他叫张光。后来我与张光真成为了朋友,他帮过我好多次,我也请他到了七里镇的家里喝过酒。
五
到了90年代,柳园火车站变了,更名为敦煌站。盖了新的候车室,行李托运房也安装上了门窗,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过往旅游的、出差的人越来越多了,火车票却更难买了。
我与单位老王去成都出差,到了柳园,老王想尽办法也搞不到车票。无奈之时,老王突然想起学校有个教音乐的孙老师说过,火车站派出所有个陈所长,曾经跟他学过钢琴。老王是老江湖,能说会道,有这点线索,很快就找到陈所长。陈所长外表挺拔,一副刑警队长的气质,当知道我们是孙老师介绍来的朋友后,当即联系车站买票,可的确没有票了。他让我们放心,说直接送我们上车。
火车来了,人多得挤不动,陈所长开辟一条专用通道,送我们上车,还安排小警察买了一箱啤酒送给我们。接洽上乘警长老张和乘警休林后,两人立即安排我们去软卧包房。相互介绍没几句话,四人就开始喝酒,一箱啤酒喝完,我和老王与他们都拉熟了。到了饭点,餐车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吃完旅客才能开餐。休林酒量大,很健谈,个头不高,非常健壮,眼睛毒辣,感觉一眼能看穿别人。我说他非常像电影《最后的疯狂》里的警察,他很开心。乘警长老张却很文弱,酒量也小。晚上接着喝,一瓶白酒见底后,休林出去走了一趟,没有多久,就捧着一堆酒瓶回来了。那些是从硬座车厢没收来几个半瓶酒,有伊力特曲、有金徽、有陇南春什么的。几个人聊得开心,都喝大了,让我们锁门睡觉。
到了半夜,软卧包房门被女列车长打开了,我们被赶了出来,说我们不买票,混吃他们餐车饭,还睡软卧,太过分了。她还给了点面子,让我们坐软卧车厢过道座位,然后锁上软卧包房门就走了。没多久,休林来了,打开包房门继续让我们睡觉。他与女列车长闹翻了,才知道列车乘警是铁路局临时随机派遣来执勤的,与女列车长他们不是一伙的,相互管不了。闹腾一下,此后女列车长就再也不管我们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餐车吃大餐,在包房里喝大酒,他们讲他们多年来火车上的奇遇,我们讲我们传统的石油故事,与女列车长相安无事。
晚上火车翻越秦岭时,他俩忙碌了,说是甘肃的、陕西的、四川的小偷在这里要汇集了。休林身手敏捷,抓了十几个小偷,手铐都用完了,有两个小偷是背过手,用鞋带绑着大拇指的,让我们帮忙看着。乘警长老张在餐车负责做笔录,小偷跪在地上接受询问。
小偷们经受不了,都招了。老张忙着写案卷,小偷不停地按手印,他们要在到达成都前,把所有案卷与小偷都移交沿线铁路派出所。临近终点,终于忙完了,两人一个劲地给我们说抱歉,没有陪好我们。
到了成都,因为没有买票,他们把我们送出火车站。大家互留通信地址,相约以后火车上在聚。望着他俩的背影淹没在人群中,有些难舍。这是一趟幸福之旅,感慨教音乐的孙老师、派出所陈所长、乘警长老张、乘警休林,都是人生中遇到的好人。
六
那一回出差,在成都呆了20多天,办完公事,老王有别的事,我独自返回柳园。
这是趟加班火车,走走停停,磨叽了一个晚上,天亮才到广元。到站后,车厢下了一大半人,总算轻松点,有了座位。火车开出广元没多久,车箱里就有传过来一股好熟悉的酒香味,真提神。一个音色较高的声音也与酒香一起飘过来,仰头一看,车厢中部,有一个老头好像是在演说。慢慢移动过去,坐在他斜对面,想听他说什么,打发这无聊的行程。
这老头精瘦,脸庞黑红,一直红到脖子上,脖子上也暴涨一根筋。他演说一会,就吃口菜,再喝口酒。喝酒的时候,端起杯来,仰脖子倒进嘴里,猛吸一下,发出“嗞——”地一声响,很刺激人。我假装没事,悄悄观察。
他说话听着很悬,有说书人的感觉,一惊一乍,抑扬顿挫。听的人是越聚越多,对面的听客肯定是上车才认识的。
记得他说:当今社会,高手云集,大多武林侠士都隐藏于民间,没准我们身边就有武林高手。
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前一段时间在成都,我亲眼所见,一小女子把一个壮警察轻轻一拍,那壮警察就倒地昏死过去……
听他讲了很多,我想这人神经有毛病。
火车开到秦岭附近,临时停车,老头也讲累了,也停嘴了。
我点了支烟。
车停的时间很长,烟抽完了。我用两个手指把烟头往地上一弹,很随意,可那烟头在地上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翻滚几个跟头后,竟然站立在那里,还冒着青烟。
这一幕让老先生看到了,他瞪大眼睛盯着我看了一阵,再看看地上的烟头,又抬头看看我。
之后,他突然双拳一抱,冲我行礼:小兄弟原来是武林高手呀,看似这么年轻,就身怀绝技!
他拉我坐到他的身边,不待解释,倒酒双手相敬。我这人是喝酒从来都不会劝别人,但我又经不起别人劝,喝吧,怎么办。
我反复说自己没有功夫,他哪听得进。他说,越谦虚的人,说明功夫是越深呀,我就是他寻找多年的武林高手。他很虔诚的样子,拿出好多好吃的请我吃。特别是他带的臭鸡蛋,臭到极处就是香,我不吃就是不礼貌。又拿出白酒请我喝。吃吧,喝吧,几杯之后,我就把自己真当成了武林高手了,这段路途不再寂寞了。
他竟然与我是同路,他去新疆,我到柳园,可算是有个伴了。到了宝鸡要转车,人太多,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就挤散了,试图找他好几圈,也没找到。
总是忘不了这爱说武林高手的老头,特别是那脖子的那根青筋,也许他永远活在他的武林世界里。
七
这趟回程是出入柳园最艰难的一次。我从宝鸡登上过境到兰州的火车,站了一夜才到兰州。还没出站,就发现对面到乌鲁木齐的绿皮火车停在那里,于是跟着人群往车上挤。我上去的时候,脚都沾不着地了,顺着人流被抬了进去,快被挤扁了。我挤到乘务室门口站着,腰都也直不起来,火车开起来后,晃荡晃荡,才感觉好点。
我站立在乘务室旁边,本来就拥挤,身后有人故意挤我。开始我怀疑是个小偷,后来发现不对劲,那人用下体顶着我的屁股。扭头一看,却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他离开我了一点,没过一会又贴上来了,还用鼻子闻我的头发。我狠狠地蹶了他一屁股。
乘务员过来了,是个漂亮的女孩,长得高中生模样。我侧身,她挤进乘务室,没有关门。我眼前有了舒服的空间,开始试探着与她聊天。她是铁路技校的实习生,为套近乎,我说我是石油技校的实习生。她说她想去敦煌玩,我说我一定带她去爬鸣沙山。我拿出成都的豆腐干给她吃,她给了我一颗水果糖。一来二往,就被她请进了乘务室就坐,真不容易。站立在外面的人堆和小白脸,看着我这样待遇,羡慕得都快流口水了。那个女孩叫李小莉,郑州铁路局的子弟,与我们“油二代”很相似,都是老国企,体制都差不多,很快我们就聊熟悉了。我大胆地告诉她,我在兰州上车,还没有买票,柳园站是个全国先进火车站,票查得很紧,没票出不了站。她出了个主意,快到柳园时,她去给我补张票,这样省钱。
夜里,我几乎把我所知道的笑话搜肠刮肚,都讲给李小莉听,逗得她很开心。小小乘务室里,充满了我们俩的荷尔蒙,相互吸引着,又相互克制着。
车到柳园之前,她被列车长找去开会,没等到她回来,我就下车了。我孤独地站在站台上,望着西去的绿皮火车,站了好一阵,算是在给李小莉的告别。她真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可惜之后再也没遇见过她。
出站的人都走完了,车站工作人员过来,问我干吗的。我说是等火车出发的,对方就不再管了。半个小时后,他们都放松了警惕,我就从出站口西侧的工作人员通道溜出站了。
过了几年,敦煌通火车了,有了名正言顺的敦煌站,柳园火车站把名字又改了回来。渐渐去柳园的机会越来越少,交通出行的方式变了,坐绿皮火车成了过去的回忆。
结婚后,我再也没回过故乡。后来我离开油田到北京工作,家也搬到北京,儿子却把石油小镇七里镇当成了他的故乡。
再没有去过柳园,但是它在我心中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 完 ——
题图为80年代的柳园火车站。梁泽祥摄。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李炯,60年代末生于甘肃戈壁石油小镇,辗转于青海柴达木、上海、北京工作,学过绘画、电影,当过石油钻工,扛过摄像机,拍过纪录片,结交三教九流,能饮善讲,装着一肚子故事。现居北京,在一家行业媒体工作。
我在伊拉克的180天(六)祖国的伟大,只有出国才有最深的体会
我在伊拉克工作的180天里,有很多很多的趣事儿和烦心事儿,但是出国的人都知道,身处异国他乡最想念的家乡的温暖,那怕是一碗面、一袋榨菜、一根油条都很知足。这是我写的第六篇关于我在伊拉克的一些小事儿,也是最后一篇,我想记录一下在伊拉克遇到的关于祖国的事儿,2021年都过得不顺利,六篇文章也寓意希望这能让大家还有我顺顺利利地度过2022年。
在伊拉克我们有配车,虽然是几个人一辆车,但是也会好过去挤大巴车。因为身处荒漠,再好的车也难逃厄运,我们的车就是,连续一个月四个轮胎轮流爆胎,无奈之下只能自己换下备胎,然后去汽修店修理。汽修店是伊拉克人开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你好!China?”我们回答“yes”他说“China no good”我们急忙问“why?China very good”他就笑笑没再说话。随后我们的轮胎接连爆胎,无奈只能继续去汽修店修理,我们也帮忙卸轮胎,装轮胎,不知是因为这些还是因为第一次我们怼了他,后来的几次当我们修完车后,他总会给我们竖一个大拇指说“China good”。虽然事情很小,但是很暖心,能从不好变成好,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所作所为,而是整个国家的强大。
第二件事发生在2019年国庆,那时刚开完早班会,有一个中国工人突然上前说到“今天是国庆节,我提议大家一起共唱国歌”,当时大多数人听到后和我感觉一样,今天的安排上没有这一环节呀,很明显是他自己的想法,后来大家很认真的跟着唱了国歌,我对他也有个很深的印象。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观看阅兵,有伊拉克人、印度人、孟加拉人一起观看,其中第一环节便是唱国歌,这一次的国歌是我从出生到现在唱过最感动的国歌,想起来至今会起鸡皮疙瘩,几百人唱出了中国的风采,那些伊拉克人,印度人经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神,甚至有的印度人因为我吃了一包榨菜看到上面的财神,以为那是中国人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神。经过这次国歌,在场的所有外国人都明白了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的信仰全部都包含在了那一首国歌当中,响彻房屋的国歌,震耳欲聋的国歌,最好听的国歌。紧接着我们就观看了2019年的阅兵式,外国人对中国的国力军力感到很吃惊,一开始还在说中国的饭菜不错,嘻嘻哈哈,越往后便越不说话。我想有时候站在他们的角度,国家有难,国土破碎,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最后一件事儿是我回国的时候,那时候伊拉克的暴乱也刚停止,项目外面上百辆车和数不清的摩托车还有人在等招聘,想要一份工作。项目上的安保人员也增加了,那条老狗则不知去向,换成了数十名含有杀气的老兵,那杆Ak枪管磨的锃亮,老兵的眼神已经不是我刚开始遇到的那几个士兵的慵懒状态,一看就是真正经过战争洗礼的老兵。后来就正式往机场出发了,一路上司机开得飞快,到纳杰夫的时候天刚黄昏,路上的行人车辆也很多,我也见到了与来时不一样的景象,小朋友在废墟前的空地踢足球,大人在商铺前讨价还价,路灯也逐渐亮起。但到机场高速后,实际情况告诉我事情并没有缓和,几公里的高速路,路两边每隔两米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手里的枪支也和营地内的不一样,装备更加齐全,一直延伸到机场的候机厅,也是很壮观。
经历完这些,我也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在飞机上看着夜幕下的伊拉克,我想来过一次,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了,伊拉克曾经很繁华,那些车辆,废墟依旧还能看到曾经繁华的痕迹,但是再繁华也扛不住战争的侵害,没有铁拳头,就得挨别人的揍,我想这种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出过国才能感受祖国的伟大,经历过生死才能藐视一切困难,我很庆幸我在23岁的时候去过这个地方。我在伊拉克的180天的生活暂且记录这些吧,再次感谢您的阅读,请多多批评指正。
我在伊拉克的180天(一)6000公里的旅程就此开始
我在伊拉克的180天(二)高温和狐臭外加漂移,艰难之旅
我在伊拉克的180天(三)卖惨成了国际通用套路
我在伊拉克的180天(四)长短棉衣之争?长款棉衣是女性的专属
我在伊拉克的180天(五)“我出国挣钱,然后雇人在家种地”
卫毅 X 郭玉洁:我从故乡归来 | 正午·夜谈
戈壁上的车站
文 | 李炯
小时候,我跟着当石油工人的父亲,居住在七里镇。这个油城小镇,在敦煌以西七公里的地方,建在一片戈壁滩上,是石油单位生活基地。镇上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开口南腔北调,每到年底,他们总是背着大包小包,拉着孩子小手,搭乘拉原油的便车,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柳园火车站,坐上绿皮火车回故乡。
柳园原是不毛之地,附近有个地方叫红柳园,地下水滋生一片红柳,在戈壁沙漠很显眼,柳园火车站得名由此借来。
1950年代,兰新铁路建成后,是当年离西藏最近的铁路线。为了把军事、民用物资运往西藏,彭德怀摊开地图,看了半天,在上面画了个圈,便诞生了柳园。这个小站担负起铁路、公路物资转运仓储集散的任务,有人戏称柳园是“火车拉来的小镇”。
这个名不转经传的小站也曾繁荣过。八十年代,敦煌兴起旅游热,但不通火车,游客乘火车要必经柳园下车,再转公路。后来铁路以北的黑山里发现很多矿藏,金矿尤其引人,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赶来这里,都以柳园为开矿基地。
柳园是兰新铁路甘肃境内的最西的一站,附近铁路和公路呈“土”字形状。上一横是甘新省道,下一横是兰新铁路,一竖就是通往七里镇的那条公路,柳园就坐落在下一横铁路和一坚公路的交叉点上。
离柳园五公里处的公路边,我见过有一张指路牌,十字交叉,前方柳园,左边西去哈密290公里,右边东往瓜州71公里。
岁月流转,柳园成为七里镇连接远方世界的起始点,成了人们的心理坐标。那个年代,车少,路不好,每次出入都非常费劲,为了搭便车,常常不得不提前走。到了柳园,买火车票又成了最头痛的事,运气不好就要等几天才买到票。那会儿,很羡慕住在柳园的人,看着火车驶过,或者听到火车汽笛声,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一晃多年,来来去去,记不清过往柳园多少趟,但买票、候车、上车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有意思的人,至今历历在目。
一
16岁时,父母允许我独自回故乡。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远行。
出发前,打听到油田一辆小车去柳园接领导,想搭个便车。那司机看我带着五个包,便立马拉着脸,勉强让我上了车。车上坐着一个搭便车的漂亮女人,她与司机一路上聊得火热,都不理我。不一会,我发现自己憋着一泡尿,他们俩每笑一次,我都会被尿憋得打个颤抖。年少羞涩,我不敢给司机说停车撒尿。经过漫长的两个多小时,车到柳园时,我都快憋疯了,背着扛着几个包,匆匆跑进人满为患的候车室,却发现里面没有厕所。没办法,把五个包扔在地上,先去解决燃眉之急。在广场西侧的厕所撒完尿,听见街上书店的喇叭里放着一首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费翔唱的,满街人都能听到。想到即将面临的枯燥旅途,琢磨是不是买本书路上看。反正是兜里有钱,可以自由支配了。出了书店,又觉得肚子饿了。想进小饭馆吃饭,又怕扔在候车室的几包东西丢了,自己跟自己不停地打赌:东西丢了?东西没有丢?假如丢了,就骗父母全部带到了。在车站外晃荡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候车室,发现除一个工作人员在扫地,人全走了,我的五个包完好如初地躺在地上。
那是坐火车的淡季,顺利买了一张硬座票,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但每人都躺着,各占一排位子,谁都不让座。我想找个空位,拎着五个包走过若干个车厢,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两个中年妇人坐着。没有退路,没有商量,我一屁股就坐下了。总算消停下来,望着窗外快速移动的戈壁,我的心已经飞向远方幻想中的大城市。
一个月后回到柳园,已是下午,拉原油的车都走完了,没法搭便车。身上仅剩几枚硬币,走投无路时,想起在敦煌读中学时的同学建国、建利,他俩是双胞胎兄弟,家在柳园,便去找他们。他们家在西藏商贸公司驻柳园货场里的一排平房,父母年龄很大,说一口陕北话,咳嗽不停地着接待我。在弥漫着中药味道的屋里吃了丰盛的晚饭。晚上与建国、建利两兄弟睡在他家的炕上。建国话很少,总是在看书学习。建利善谈,与他聊得很晚。夜里总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火车驶过的声音,每次建利会卖弄着告诉我:这是70次去北京火车;这是54次去上海的火车;这个嘛,是一列货车……
临睡前,又听到火车声,问他这是到哪里的火车。他迷迷糊糊说,这是一列往东开的油罐车。不知他是在蒙我,还是真能听出来,反正挺佩服他。
第二天,两兄弟留我玩一天。柳园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带我去戈壁滩,抓蝈蝈。柳园的蝈蝈与其他地方的蝈蝈不一样,母蝈蝈长着一把日本刀形状的尾巴,是产卵器,公的蝈蝈没有。柳园的戈壁滩草很少,但长着一种草当地独有,我们叫它箭草——拔出草根,直直的,硬硬的,乳白的,根的底部像一个箭头模样,也不是很尖,像显微镜下男人精子头的造型。
三人一路走了很远,到了铁路边,玩他们儿时的游戏,在铁轨上走平衡。
多年后,发现过一张名叫《黄昏时寻找平衡的少年》的油画,与当时情景一模一样。这幅画的作者是王岩。
还有一个惊险的游戏是听火车。我们趴下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火车驶来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看到火车头一点点接近,让火车司机发现,有的便来一声尖利的汽笛声,有的会紧急刹车,有的也仿佛没有看到我们一样,反而加速。总是到火车逼近的最后时刻,我们才起身逃离铁轨,狂笑着飞跑起来。玩了几次觉得无聊,建利又有了新花样,问我想不想要把刀?我说如何得到,他便拿出一根半尺长的铁钉,放在铁轨上,不一会火车开了过来,几分钟后,铁钉被压成了锋利的铁片。我拿出了一个硬币,如法炮制,被压成了薄铝纸。回去后,建利给那铁片安了一个木把,真成了一把刀,送给了我。我发现他家里大大小小这种刀很多,有用的和不用的。
高中毕业,建国考上了清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鼓励我当一名优秀的石油工人。建利考到北京的一所民航系统的学校,他们父母退休搬回老家,此后我与两兄弟失去联络。
此后,再过柳园,便没有可找的朋友了。
二
我当了石油工人后,有一年冬天,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赶到柳园。卖火车票的窗口已关,候车室改为凭票进入。
要等第二天才能买票,我到哪里过夜呢?瞎转悠一阵,花一块二,买了瓶小角楼牌的白酒,准备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两口取暖。走进托运行李的房子,门和窗户都没安装,雪花都飘了进去,里面与外面一样冷。地上整整齐齐地睡着一排藏族人,像无生命一样悄声无息。窗台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藏族男人,极像佛像中人物,嘴里默念着经文,手里不停地摇动着经轮。我仔细观察他的脸庞以及服饰,他当我不存在,压根都没有瞄我一眼。不一会儿,隐隐约约听到有小孩的哭声。只见这男人挪动了一下身子,右手伸进胸前,从藏袍里摸出一瓶酒,放在了窗台上;接着又摸出一条羊腿,放在了窗台上;再摸,竟然提出一个光溜溜、黑乎乎的小孩,也一把放在了窗台上,那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又摸,摸出一把屎,直接扔了出去。然后,他再按照顺序把孩子、羊腿、酒依次放进象百宝箱似的胸口,小孩便不再哭了。
车站外非常寒冷,溜达一会就冻透了身子。广场上已经被飘飘洒洒的雪染白了,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只狗狂叫了两声,飞快地跑过,广场对面录像厅喇叭里的武打声音却很响亮。
我犹豫是找小旅社住下,还是去录像厅看个通宵录像,最后还是决定看录像——看录像两块钱,比住旅社便宜两块。
录像厅老板是个老头,嘴里镶着一颗金牙,满脸皱纹里写着“烟酒”二字。交钱买票,拎着酒走进放映厅,烟雾腾腾,看不清前面的录像画面。一股热浪扑面撞来,刺鼻的煤烟味,搅和着脚臭、屁臭、狐臭、莫合烟味,差点把我熏倒,不过没到一分钟就适应了。放映厅里几乎坐满了人,墙上贴着周润发头像画,旁边隐隐约约写着“禁止脱鞋”。仔细打量四周,看录像的人长得都很奇特,有的面目狰狞,有的胡子拉喳,有的像街头乞丐,全都不像这个地界上的人。或许他们是附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或许是与我一样赶火车的过客,无从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摸索着到第二排,找了个空位坐下,搓搓冻僵了的手,侧目看了一眼,邻座是相拥的一对男女,男人将手从女人毛衣领放进她胸口。猛然感觉这女人真好,用胸为男人暖手,我要有这样一个女人就好了,可又一想,他妈的放映厅里很暖和。
电视机里播放着《陈真》,以前看过的连续剧,陈真与日本浪人在比武,正打得欢实。霍元甲与陈真,是80年代人们最熟悉的武林高手。
点上支烟,拧开白酒喝了两口,身子渐渐暖和起来,困意随之袭来,没多久竟迷迷糊糊睡着了。长条木椅睡着不舒服,不知道过了多久,睡得脖子疼,起身出去撒泡尿,活动一下筋骨。外面雪下得很大,厕所太远,大街上没人,就地解决,用热尿在雪地上刺,画出一颗大树。
返回录像厅,在满脸烟酒的老板那买了包瓜子,回到座位,发现那瓶酒没有了。我站起来大声问:“谁拿了我的酒?!”没人吭声,没有办法,只好算了。
又囫囵看了一集,一大片人都睡了。大约夜里3点钟,突然,一个看似很凶恶的人在人群中站了起来,呼喊录像厅老板:“停!”他让暂停放映,要撒尿。第一次知道录像厅还能这样,可以暂停,集体去撒尿。灯亮了,录像停了。歪七八糟看录像的人一下子精神了,聊天的、骂娘的、吃东西的、抽烟的、出出进进的,屋里乌烟瘴气。直到那个喊暂停的牛人回来,老板才继续播放。没几分钟那人又大声喊叫:“放点好看的!”老板磨叽一会儿,真换了磁带,播了一部毛片。所有人顿时瞪圆了眼睛,精神头来了,吞咽着吐沫目不转睛,侧目看到邻座的男人,已经把手放到那女人的裤裆里暖和去了。
不到一小时,看得正酣,录像突然停了,又开始播放《陈真》。老板嘟嘟囔囔地说看看就行了,公安查得紧,查到就会把他和大家全都抓起来。
熬到早晨,我挤上一列东去的绿皮火车走了。
三
柳园坐火车,人多票少,碰到出行高峰期,买票极难。我去重庆上学那年,暑期到柳园坐火车,不光是买不上票,有票的都上不去车,有的火车只让下不让上,有的火车连车门都不开。
那次,在柳园晃悠了两天也买不到火车票。晚上打发时间,溜跶到东边铁路局家属院,碰到俱乐部正在举办交谊舞会。我幻想着能有场艳遇,认识一个铁路上的女人,以后帮着买车票。这么寻思着,进了舞厅,邀请几个女人跳舞。可一旦说出意图后,她们对我这个过客马上就没了兴趣。
第二天,继续在火车站溜跶,遇到一个从外地归来的朋友刚下火车,与他寒暄一会,得知小学同学小东在油田柳园库工作,于是马上就去找小东。我和小东多年没见面了,他非常热情地请我吃饭喝酒,聊小时候的事,很开心。到了晚上,安排我住他的宿舍,他与别人去挤着睡。他的宿舍是我见过最简陋的宿舍,中间放着一张麻将桌,靠里是一张小床,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喝得有些晕头晕脑,就倒头睡下了。
一觉醒来,发现屋里挤满很多人,围着麻将桌观战。我起身去看了看,小东把我介绍给大家。他们都很客气地邀我打麻将,我还是头晕,推辞后继续睡觉。其实也睡不实了,到了半夜,这些人压低了话音,他们声音越低,我越是感兴趣地听。大概听明白了,他们分工,要去偷一个库房里的物资。一两点的时候,灯关了,人都散了,我才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小东推着一辆自行车进了屋,其他人也陆陆续续来了。他们先是看看我还在睡,就压低声音说话,大概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偷上想要的东西,只弄回一辆自行车。
早上,小东叫我起来去吃早饭,他用偷来的自行车驮着我,去柳园繁华的火车站对面大街吃羊肉粉汤。路上,我想给他说点什么,但又没法开口。
吃完羊肉粉汤,我急着要走,小东找到火车站的朋友,还真弄上了中午出发的车票。他回去上班,我们就此分手。
那一年,寒假没回来。第二年的暑假我才回来,到柳园去找小东。到他宿舍门口,门被一把大锁锁着,问了几个人才知道,他们那些年轻人都因盗窃都被判刑了,有判十几年的,有判两三年的,小东被判了五年。我非常惊讶,内疚好长时间,后悔当初应该劝劝他就好了。
几年后,我在油田一线的电视台工作,在大街上偶遇小东。我很激动,他却面目冷漠,眼神不敢直视我,他变了。听别人说他在牢里被人干了,脑子受了刺激,刑满释放后,回油田二次就业了,三十多岁也没有成个家,此后在也没有见过他。这么多年,不知道他过得如何,是否娶妻生子。
四
到柳园坐火车,自己买票难,帮人买票更难,往往要托关系搞票。
有一年,单位电视台领导给我交代一个任务,去柳园帮他买张卧铺票。临行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到了火车站,直接去找站长,给过信就能拿到批条,买到卧铺票。
我搭便车赶到柳园,找到一位胖胖的站长。结果那胖站长看完信后,当着我的面,把那信撕扯得粉碎,往地上一撒,说声没有票,转身就走。
任务完不成没法交差。就给领导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领导不说交信的事,只训斥我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要我想办法,就是连夜排队也得买到,买不到卧铺票就别回来。我只好去售票窗口排队,哪知道那天排队人太多,多数都是票贩子,排队也买不上。没法,我只好与一个票贩子联络,买一张票要加100元钱。
这个票贩子看起来文绉绉的,夜里,我绞尽脑汁与他聊天,聊社会、聊国际、聊历史、聊生活、聊女人,使尽力气聊。半夜,还给他买方便面、火腿肠、榨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终于开窗卖票了,卧铺买上了。那票贩子给了我票,说不收那多加的100元钱了,可以和我交个朋友,以后想买票都可以找他。我们互留了地址和电话,记得他叫张光。后来我与张光真成为了朋友,他帮过我好多次,我也请他到了七里镇的家里喝过酒。
五
到了90年代,柳园火车站变了,更名为敦煌站。盖了新的候车室,行李托运房也安装上了门窗,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过往旅游的、出差的人越来越多了,火车票却更难买了。
我与单位老王去成都出差,到了柳园,老王想尽办法也搞不到车票。无奈之时,老王突然想起学校有个教音乐的孙老师说过,火车站派出所有个陈所长,曾经跟他学过钢琴。老王是老江湖,能说会道,有这点线索,很快就找到陈所长。陈所长外表挺拔,一副刑警队长的气质,当知道我们是孙老师介绍来的朋友后,当即联系车站买票,可的确没有票了。他让我们放心,说直接送我们上车。
火车来了,人多得挤不动,陈所长开辟一条专用通道,送我们上车,还安排小警察买了一箱啤酒送给我们。接洽上乘警长老张和乘警休林后,两人立即安排我们去软卧包房。相互介绍没几句话,四人就开始喝酒,一箱啤酒喝完,我和老王与他们都拉熟了。到了饭点,餐车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吃完旅客才能开餐。休林酒量大,很健谈,个头不高,非常健壮,眼睛毒辣,感觉一眼能看穿别人。我说他非常像电影《最后的疯狂》里的警察,他很开心。乘警长老张却很文弱,酒量也小。晚上接着喝,一瓶白酒见底后,休林出去走了一趟,没有多久,就捧着一堆酒瓶回来了。那些是从硬座车厢没收来几个半瓶酒,有伊力特曲、有金徽、有陇南春什么的。几个人聊得开心,都喝大了,让我们锁门睡觉。
到了半夜,软卧包房门被女列车长打开了,我们被赶了出来,说我们不买票,混吃他们餐车饭,还睡软卧,太过分了。她还给了点面子,让我们坐软卧车厢过道座位,然后锁上软卧包房门就走了。没多久,休林来了,打开包房门继续让我们睡觉。他与女列车长闹翻了,才知道列车乘警是铁路局临时随机派遣来执勤的,与女列车长他们不是一伙的,相互管不了。闹腾一下,此后女列车长就再也不管我们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餐车吃大餐,在包房里喝大酒,他们讲他们多年来火车上的奇遇,我们讲我们传统的石油故事,与女列车长相安无事。
晚上火车翻越秦岭时,他俩忙碌了,说是甘肃的、陕西的、四川的小偷在这里要汇集了。休林身手敏捷,抓了十几个小偷,手铐都用完了,有两个小偷是背过手,用鞋带绑着大拇指的,让我们帮忙看着。乘警长老张在餐车负责做笔录,小偷跪在地上接受询问。
小偷们经受不了,都招了。老张忙着写案卷,小偷不停地按手印,他们要在到达成都前,把所有案卷与小偷都移交沿线铁路派出所。临近终点,终于忙完了,两人一个劲地给我们说抱歉,没有陪好我们。
到了成都,因为没有买票,他们把我们送出火车站。大家互留通信地址,相约以后火车上在聚。望着他俩的背影淹没在人群中,有些难舍。这是一趟幸福之旅,感慨教音乐的孙老师、派出所陈所长、乘警长老张、乘警休林,都是人生中遇到的好人。
六
那一回出差,在成都呆了20多天,办完公事,老王有别的事,我独自返回柳园。
这是趟加班火车,走走停停,磨叽了一个晚上,天亮才到广元。到站后,车厢下了一大半人,总算轻松点,有了座位。火车开出广元没多久,车箱里就有传过来一股好熟悉的酒香味,真提神。一个音色较高的声音也与酒香一起飘过来,仰头一看,车厢中部,有一个老头好像是在演说。慢慢移动过去,坐在他斜对面,想听他说什么,打发这无聊的行程。
这老头精瘦,脸庞黑红,一直红到脖子上,脖子上也暴涨一根筋。他演说一会,就吃口菜,再喝口酒。喝酒的时候,端起杯来,仰脖子倒进嘴里,猛吸一下,发出“嗞——”地一声响,很刺激人。我假装没事,悄悄观察。
他说话听着很悬,有说书人的感觉,一惊一乍,抑扬顿挫。听的人是越聚越多,对面的听客肯定是上车才认识的。
记得他说:当今社会,高手云集,大多武林侠士都隐藏于民间,没准我们身边就有武林高手。
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前一段时间在成都,我亲眼所见,一小女子把一个壮警察轻轻一拍,那壮警察就倒地昏死过去……
听他讲了很多,我想这人神经有毛病。
火车开到秦岭附近,临时停车,老头也讲累了,也停嘴了。
我点了支烟。
车停的时间很长,烟抽完了。我用两个手指把烟头往地上一弹,很随意,可那烟头在地上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翻滚几个跟头后,竟然站立在那里,还冒着青烟。
这一幕让老先生看到了,他瞪大眼睛盯着我看了一阵,再看看地上的烟头,又抬头看看我。
之后,他突然双拳一抱,冲我行礼:小兄弟原来是武林高手呀,看似这么年轻,就身怀绝技!
他拉我坐到他的身边,不待解释,倒酒双手相敬。我这人是喝酒从来都不会劝别人,但我又经不起别人劝,喝吧,怎么办。
我反复说自己没有功夫,他哪听得进。他说,越谦虚的人,说明功夫是越深呀,我就是他寻找多年的武林高手。他很虔诚的样子,拿出好多好吃的请我吃。特别是他带的臭鸡蛋,臭到极处就是香,我不吃就是不礼貌。又拿出白酒请我喝。吃吧,喝吧,几杯之后,我就把自己真当成了武林高手了,这段路途不再寂寞了。
他竟然与我是同路,他去新疆,我到柳园,可算是有个伴了。到了宝鸡要转车,人太多,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就挤散了,试图找他好几圈,也没找到。
总是忘不了这爱说武林高手的老头,特别是那脖子的那根青筋,也许他永远活在他的武林世界里。
七
这趟回程是出入柳园最艰难的一次。我从宝鸡登上过境到兰州的火车,站了一夜才到兰州。还没出站,就发现对面到乌鲁木齐的绿皮火车停在那里,于是跟着人群往车上挤。我上去的时候,脚都沾不着地了,顺着人流被抬了进去,快被挤扁了。我挤到乘务室门口站着,腰都也直不起来,火车开起来后,晃荡晃荡,才感觉好点。
我站立在乘务室旁边,本来就拥挤,身后有人故意挤我。开始我怀疑是个小偷,后来发现不对劲,那人用下体顶着我的屁股。扭头一看,却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他离开我了一点,没过一会又贴上来了,还用鼻子闻我的头发。我狠狠地蹶了他一屁股。
乘务员过来了,是个漂亮的女孩,长得高中生模样。我侧身,她挤进乘务室,没有关门。我眼前有了舒服的空间,开始试探着与她聊天。她是铁路技校的实习生,为套近乎,我说我是石油技校的实习生。她说她想去敦煌玩,我说我一定带她去爬鸣沙山。我拿出成都的豆腐干给她吃,她给了我一颗水果糖。一来二往,就被她请进了乘务室就坐,真不容易。站立在外面的人堆和小白脸,看着我这样待遇,羡慕得都快流口水了。那个女孩叫李小莉,郑州铁路局的子弟,与我们“油二代”很相似,都是老国企,体制都差不多,很快我们就聊熟悉了。我大胆地告诉她,我在兰州上车,还没有买票,柳园站是个全国先进火车站,票查得很紧,没票出不了站。她出了个主意,快到柳园时,她去给我补张票,这样省钱。
夜里,我几乎把我所知道的笑话搜肠刮肚,都讲给李小莉听,逗得她很开心。小小乘务室里,充满了我们俩的荷尔蒙,相互吸引着,又相互克制着。
车到柳园之前,她被列车长找去开会,没等到她回来,我就下车了。我孤独地站在站台上,望着西去的绿皮火车,站了好一阵,算是在给李小莉的告别。她真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可惜之后再也没遇见过她。
出站的人都走完了,车站工作人员过来,问我干吗的。我说是等火车出发的,对方就不再管了。半个小时后,他们都放松了警惕,我就从出站口西侧的工作人员通道溜出站了。
柳园火车站新楼。董政权摄。
过了几年,敦煌通火车了,有了名正言顺的敦煌站,柳园火车站把名字又改了回来。渐渐去柳园的机会越来越少,交通出行的方式变了,坐绿皮火车成了过去的回忆。
结婚后,我再也没回过故乡。后来我离开油田到北京工作,家也搬到北京,儿子却把石油小镇七里镇当成了他的故乡。
再没有去过柳园,但是它在我心中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 完 ——
题图为80年代的柳园火车站。梁泽祥摄。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李炯,60年代末生于甘肃戈壁石油小镇,辗转于青海柴达木、上海、北京工作,学过绘画、电影,当过石油钻工,扛过摄像机,拍过纪录片,结交三教九流,能饮善讲,装着一肚子故事。现居北京,在一家行业媒体工作。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