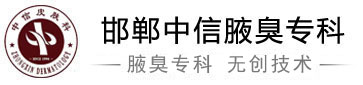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 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
我认识的3个有狐臭的女人(1)
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我认识了林女士。我是最晚报到的,她刚好一个人住。于是,会务组就将我和她安排在一个房间,我欣然同意了。
晚上,她不停的找我说话,我特别的累,想要睡觉,出于礼貌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着她。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洗漱完毕,我们一同去吃早饭。总感觉她身上有奇怪的香味,还混杂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却说不出来奇怪在哪里,和晚上房间的味道一模一样,让人很不舒服。
早饭之后集合出发,我和大家都不太熟悉。我也是在人群之中跟着大家的步调,服从会务组的安排。她时不时会过来跟我说话,或者问我别人说了什么?我就更加奇怪了。
后来,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刚好跟她坐在了一桌。她不停的唠叨着,她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会务组的人就又给她另外点了饭菜。但我们吃的饭菜她也一个不落的都吃过了。我的好奇之中又多了一份厌恶,这人太能作了。
白天的参观结束之后,吃完晚饭我就回到房间开始写稿,她也回来了问东问西的。我没怎么搭理她,继续写我的稿子。
而且,我总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莫名的味道,很刺鼻的。我起身打开了窗户。
她又问,你觉得热吗?你可以打个空调呀。大家都要去泡桑拿了,你怎么不去呀?
我一直在电脑上忙着。她看我不说话,慢慢走到窗户边,关了窗户。我刚好背对着她,一直都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事。然后她气乎乎地走了。
房间里的味道很难闻,我起身想打开另外一个窗户,才发现我先前打开的窗户已经被关上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没有打开它。
我愤怒的打开空调,忍受着刺鼻的味道写稿发稿,之后就去楼下了。大家都在天然地热水中玩耍,我也愉快的加入其中。
大约12点的样子,同伴们要去吃宵夜了。我不想吃回了房间。我敲门,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帮我开门。
房间里依然弥漫着刺鼻的臭味儿。而且更加的浓烈。
房间里什么味道呀?我说。
有吗?我怎么没闻到呀?她一脸不悦的盯着我说。我很无语,更是无奈。
一夜无语。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一个人去吃早饭。头昏脑胀,无精打采。
吃过早饭,会务组安排我们去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参观。
路上,有一个老师问我,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呀?
我吃惊的说,是啊,我基本上一夜没睡,我脸色很差吗?
她诡异的一笑,你是不是和林老师住一个房间?
我说是啊。
那就难怪了。她一副恍然的样子。
为什么呀?我莫名其妙的看着她。
她轻轻的说,林老师有狐臭,我第一天晚上和她住,臭死我了。后来我调了房间,才休息好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怪不得房间里一直弥漫着刺鼻的臭味,她还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太可怕了吧,我愤愤不平的说。
她之前和我住,我说了她两句,还跟我吵架,熏得我彻夜未眠,会务组的人都知道。这几天搞活动,她一直都不理我。素质太差了,有这病还出差,这不害人吗?
有时候她会喷上药水,狐臭的味道就不太明显了,有时候她不喷,那味道太上头了。
关键是身体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内心的那份龌龊。那么能作,作死得了。吃饭挑三拣四,让人特别反感。
活动还有两天才结束,你今天晚上别跟她住了。否则这身体吃不消呀。
我无奈的点点头,谢谢你啊!确实不能再和她一起住了。
晚上,刚好有一个女孩子去找当地的朋友玩,她让我住了她的房间。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就此结束了。我真的真的没有歧视过她,还有些同情她,只是忍受不了那个味道而已。
学术交流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各奔东西,回到了各自的城市。那位林老师,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和她有任何的联系。
#2022职场年终盘点#
老舍的西红柿:维生素热与民国时期的花样“番茄食谱”
那是19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姑姑递给我一个红艳艳、形状扁平而且有些柔软的水果,告诉我它叫西红柿,也叫番茄,味道很美。面对稀有水果的诱惑,加上内心的一丝好奇,年幼的我立刻咬了一口。然而,我的味蕾并不喜欢它,汁水刚刚被挤出时,我的胃立马翻腾起来。从此以后,我对番茄敬而远之。直到成年后,一位朋友递给我一盘糖拌番茄,我才对它重新建立起一丝好感。
糖拌番茄
与我有类似记忆的人并不少见。早在一百多年前,很多人就抱怨它的怪味。老舍的评价尤为苛刻,说西红柿散发着一股“青气味儿”,像个“有狐臭的美人”,甚至认为“连小孩儿拿它玩耍,仿佛也是出于不得已”。
可是在今天,番茄炒鸡蛋和番茄炖牛肉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餐桌上的常见菜肴。那么,这个曾经被称为“有狐臭的美人”是如何成功俘获中国人的心呢?
一、营养热带动了番茄热
在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之后,我发现与番茄相关的史料大多围绕“营养”二字,尤其是维生素,或者它的另一个中文译名——维他命。老舍也谈到了这点,他说:
至于整个的鲜西红柿,还没多少人肯大嘴的啃。肯生吞它的,或者还得算留过洋的人们和他们的儿女,到底他们的洋味地道些。近来西医宣传西红柿里含有维他命A至W,可是必须生吃,这倒有点别扭。不过呢,国人是注意延年益寿,滋阴补肾的东西,或者这点青气味儿也不难于习惯下来的;假如国医再给证明一下:西红柿加鹿茸可以壮阳种子,我想它的前途正自未可限量咧。[1]
中国人一向注意饮食养生,为了延年益寿,往往愿意尝试各种食材,无论多么苦涩,比如清热消暑的苦瓜,或是多么臭味刺鼻,比如说包治百病的鱼腥草。从老舍的描述来看,番茄的推广主要受西医宣传的影响。
不过,也有人认为吃西红柿是由日本人带动起来的:
番茄,又名西红柿,俗名洋柿子,茄科一年生草本,乃西洋输入东洋之蔬菜类植物也,为西餐馆主要食品,近来国人受日人之传染亦多嗜食之。[2]
认为番茄是“西洋输入东洋之蔬菜类植物”的说法尚有待考证。“东洋”一词可能指代日本,也可能泛指整个东方世界。而且,历史证据表明,番茄最晚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就已经传入中国,并非一定经由日本而来。无论是受到西方人还是日本人的影响,中国人推广番茄的食用,归根结底都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 “现代营养学”的兴起。
“现代营养学”与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发现有着密切关系。1900年,人类已知的营养成分仅限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不久之后,欧美国家相继发现了与身体缺陷或疾病有关的其它营养物质。1911年,丰克(Casimir Funk)为该类营养物质创造了 “vitamin” 一词,由拉丁文表示生命的vita和生命中的重要物质amine组成。1912年,麦科勒姆(Elmer McCollum)发现了维生素A,丰克发现了维生素B。在短短十年内,维生素C、D和E相继被发现了。
维生素C,化学分子式
邻国日本在营养学先驱佐伯矩(Tadasu Saiki)的努力下,营养学发展更是迅速,甚至对全球营养学产生了影响。佐伯矩于1876年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因为在1904年发现萝卜中含有淀粉酶而闻名。萝卜淀粉酶可以分解淀粉,有助于消化。1905年,他到美国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他积极向日本民众普及营养知识,创建健康家庭食谱。1920年,他担任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营养研究所——日本帝国政府营养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佐伯矩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营养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学术研究,还应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帝国营养研究所不仅进行科学研究,还向乐于参与学习和实践的参观者开放。更重要的是,佐伯矩关注下一代的成长,为学龄儿童设计营养餐。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硝烟战火、民不聊生的状态。1910年至1930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瘟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为了强国健民,中国几乎与世界同步,大力宣扬营养的重要性。尽管信息传播网络不如今日发达,但是中国人获取科学进展的速度并不落后,还积极创办了营养研究机构。
营养学知识也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1942年,中国粮政协进会在提倡节约粮食时,有人就提倡应以科学方法节约粮食,明确指出 “以为营养就是吃饭,吃饭就是求饱” 的观念极为不正确,提出 “吃饭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求得营养”的观点。[3]
其中,作为营养中的重要物质,维生素的普及在1930年代就因为维生素C人工合成的实现和商业化推广而达到高潮。1935年,中国就有相关报道:
现在可以在工业上作大规模的制造了。这个制造法非常复杂,是新近才发明的,也是用化学方法制造维生素的第一次。这种人造维生素,叫做赖得生(Redoxon)。
自从匈牙利著名科学家孙家驹教授,professor A. Szent-Gyorgy在英国科学协进会发表这个发明以来,颇引起医界的注意。加之刚在这个发明之前,有人发明注射维生素C可疗治多种一向所谓不治之症,所以这项发明愈加轰动。[4]
赖得生(Redoxon)就是力度伸,对于刚刚经过了新冠大流行的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对此一定不陌生。我至今还记得,在2003年“非典”期间,力度伸维生素C泡腾片就曾经一度风靡。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现代营养补充剂还未开发和普及时,历来重视“药食同源,食疗食补”的理念,即通过饮食获得维生素仍然是首选。因此,富含多种维生素的番茄顺势成为了宣传的主角。
二、番茄可治病可美容养颜
不管番茄在营养学上多么有诱惑力,但是要将这“有狐臭的美人”送入中国人的口中,仍然有些困难。为了克服它的特殊味道,有人甚至特别提出要学会忍耐:
番茄养分之多,决不下于香蕉,特别是病人及病愈后者,应以多食为佳。初食番茄时觉稍有臭味,不大可口,但食久之后,渐渐好吃起来。须尽可能的忍耐着养成喜食番茄的习惯。故茄中若混以盐、则其味尤佳。番茄中含维他命A、B、C俱有之,可预防脚气等病。酒醉而心神不爽时,亦可食用之。慢性肠胃病,亦可用番茄疗治。[5]
这类宣传有夸大番茄的营养作用之嫌疑。譬如,脚气病主要由维生素B1摄取不足引发,而且,根据现在的研究数据,番茄中并不含有维生素B1。当然这种夸大其词的宣传并非个例。1941年,《大同报》也曾经号召有坏血病、 四肢软弱、面色苍黄、血流不止和肠肾有痨症的人多吃番茄。
至于番茄可以治疗慢性肠胃病的说法,在欧美国家并非新鲜事。1946年,中华自然科学社曾经报道过一位美国医生的研究,探讨 “番茄渣治痢病” 的效果,据称患者每三小时服用一次,数日后即可痊愈。在美国,早在1830 年代,番茄酱就曾被当作药物出售,据称可以治疗腹泻、消化不良和黄疸等疾病。如果要追溯番茄具有治病功能的传闻,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都离不开西方人为了推广食用番茄而夸大其医疗效果的努力。
番茄
老舍曾说如果西红柿加鹿茸可以壮阳,那它的前途就无可估量了。虽然没有找到关于番茄壮阳的宣传,但是我挖掘到了一些鼓动女性购买番茄的煽动性广告,例如:“它的生食,有清血之效,对美容上也是极有好处的呀。爱美的仕女们,倒很可以把它当作水果的代用品。”[6]至于男性方面,当时有人宣称维生素乙(即B族维生素)可以治疗男子不育病,相关报道如下:
中华自然科学社讯,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毕斯金博士,近发明报告谓,乙种维生素(即维他命),可以治疗男子之不育症。盖在男子体中,雌雄两种内分泌素,原皆存在。雌性内分泌素,能为肝脏所破坏,此种破坏作用,须有乙种维生素之帮助。故如缺乏乙种维生素,则肝脏不能破坏体中之雌性内分泌素,致使男子不育,而服食乙种维生素则能治疗之。[7]
尽管壮阳和不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无后为大”的观念主导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番茄确实富含B族维生素,那么读者必定会趋之若鹜。更有甚者,1947年还曾报道了“西红柿精抑制皮肤病菌”:
美国贝鲁特司维鲁之农业部尔纹博士、房腾博士及武德博士发现西红柿叶及姜之叶能抑制使人生运动足症(Athlete’s foot)菌之生长。此种有效成分现命名为“西红柿精”(Tomatin),但现尚未能提出此种纯粹物质,仅能制成浓液,并将叶绿素分离去掉。[8]
这则新闻源于美国农业部Beltsville研究中心的Irving, Fontaine 和Doolittle 在1945发表的研究,他们从番茄植株中分离出了杀真菌剂化合物,他们开始命名为Lycopersicin。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个名字是“lycopene”的同义词,然后将化合物改为“tomatin(现在译为番茄碱)”。不过,他们是用来检测“番茄碱”对造成番茄枯萎病的真菌的抑制作用。
1946年,他们发现番茄碱对于人类的某些真菌亦有抑制作用,因为也就出现了可以抑制 “运动足症” ,即 “脚气”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此脚气与缺乏维生素B1引发的脚气病(beriberi)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不过,1948年,Fontaine和Irving就从番茄中分离出了番茄碱。
不仅如此,我们在1939年的《南宁新闻报》上,还能读到意大利人用番茄皮制作橡皮,只不过产量极低,四百吨番茄才能制成一吨人造橡皮。
综上所述,在报纸媒体中,番茄是一个多么多才多艺的“美人”呀!谁能不为之心动呢?
三、幼儿番茄汁
尽管纸媒夸大了番茄的功能,但是它确实富含叶酸、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C、K和钾。 至于番茄的“青味”,食客似乎可以通过多吃几次就习惯了。1922年,在天津一家著名报纸上,一位作者就描述了从厌恶到喜欢的经历:
前有同学自大胜关农场实习归,带来番茄数枚,颇肥美,鲜红可观。午膳时,同学欲调制之以为肴。余止之曰,余等不惯尝此物,请留之以供观赏,勿食之可也。同学笑谓余曰,君第尝之,当知其味之无穷也,吾辈到场实习时,初亦不知尝此。后因该场出产番茄甚多,职员农夫三餐食之,吾辈因此而尝得其味。余闻其言,姑请其先调制一枚,食之觉其味固清美,惟稍有一种不快之感。以后饭时再尝几次,始觉津津有味。[9]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反复尝试。因此,如何将番茄变成美味佳肴是厨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为了更好地锁住养分,最好的方法是生食。有人提出用凉拌的方法就可以缓解它的怪味。通常做法是,挑取颜色鲜红且熟透的番茄,洗净后切成八瓣,加少许白醋和红糖,等糖融化后再食用。味道甘甜微酸,是佐酒的理想搭配。
凉拌番茄并不适合幼小婴儿,然而幼儿期又是预防维生素缺乏症的重要时期,否则可能导致发育不良,甚至严重的健康问题。因而,番茄汁也能成为补充维生素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番茄汁的制作也有一套特定程序。1941年的《南华报》提供了一种制作番茄汁的做法:
一、系将番茄擂烂成浆状,再用滤器将其渣滓滤出,又加少量之糖、盐、醋……等以调味,加热后即成。
二、若依第一法制造,仅能作短期之应用。如作长期用时,应将番茄汁于加热时再加百分之二三的硼酸粉,以资防腐,装罇——或装罐——时,应将罇内之空气抽出,始能久贮而不变味。[10]
这里提到了使用“硼酸粉”作为食物防腐剂。然而,硼酸粉在当时主要用于伤口消毒,而且硼酸粉具有累积毒性。我不确定这个方法是否被广泛接受。1934年出版的《番茄研究》则不提倡在制造番茄汁时加入任何物质,指出如果要防腐,只可加少许食盐,否则番茄汁就变味了。
四、为食物增鲜的番茄酱
中国菜除了凉拌,还有炒、炖、煮等多达几十种烹饪方式。不论哪种方式,烹饪的最高境界都逃不过一个“鲜”字。清人李渔对“鲜”的理解极为透彻。肉类中,他重鱼,他说“食鱼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能事毕矣。”蔬菜中,他推崇笋。“不知其至美所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只在一字鲜。” 并指出:“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但将笋肉齐烹,合盛一簋,人止食笋而遗肉,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
如果他能够穿越到20世纪,或许会改变看法,该称赞:“菜类甚多,鲜味杰出者非番茄莫属。”老舍曾说:“煮熟之后屁味没有,稀松一堆,没点嚼头。”这无疑低估了番茄的美味。富含谷氨酸的番茄本身就自带鲜味,因此,有人就将番茄酱取名为“西红柿酱油”,并建议:“煮红烧肉时可作酱油之用,红烧牛肉味道更美。小孩们及病人做汤、菜、煮挂面时,放一些,味道可好极了。”[1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种西红柿馅蒸饺的做法:
用西红柿做饺子馅,许多人会想到不可能,其实还是一种最味美易制的食品。
西红柿,去皮去仔,放在油锅里炒,最好把需要的酱油同时注入,一边炒一边用炒铲剁碎,一直到像买的黄酱一样即可取出。把炒的鸡蛋剁碎,牛肉(或猪肉)和葱姜等佐料都剁碎,再加入香油,少许的盐一起拌匀,这就算成功。[12]
在这个食谱中,番茄仍是发挥了“番茄酱”的功能。首先将番茄在锅内炒碎,直到变成了酱汁样,再与炒熟的鸡蛋或者肉类以及调味品拌匀,饺子馅便制作完成了。
蕃茄酱
这"稀松一堆",除了做酱,其实做汤也别具风味。用"鸡汤 番茄"来煮汤,可以让鲜味更加浓郁。这是很多年前一位上海人向我传授的经典做法,如今我也常常如此烧制。在1930年代,番茄做汤已经有多种食谱,比如将番茄切块,与其它蔬菜或者肉类简单煮成汤。我还依稀记得在上海的一所高校食堂,曾经提供一种免费的“伪罗宋汤”,是用番茄、卷心菜和少量肉沫星子简单乱煮而成。对于穷学生来说,这汤既解渴又勉强算得上是一道加菜的汤品。不过,在货真价实的罗宋汤还未进入寻常百姓家时,它仅仅是俄国人餐厅的专属菜品。
在炒菜和汤菜系列中,番茄大多数用作调味品。逐渐地,人们发现番茄不需要制成酱,与肉一起炒制也能成为一道佳肴,例如,下面这道“西红柿洋葱头炒牛肉丝”:
材料:瘦牛肉五两、洋葱头十颗,西红柿五个,香油一两,酱油,姜。
作法:西红柿预先置沸水锅内浇片时,以便摘皮去籽,同时可拔去酸味,切成细丝,再将牛肉用油煎白,放入洋葱共炒,随倒酱油,及西红柿即成。[13]
其中番茄丝是最后加入的,成品不会是“稀松一堆”。
纵观上述食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在烹饪前,番茄通常需要去皮去籽。
既然吃番茄是为了补充维生素,增加营养和强健体魄,而且,在20世纪初,细菌致病理论已经广为普及。因此,媒体在推广生食番茄时,自然也会提醒人们如何正确冲洗番茄,防止细菌入侵。例如,建议让番茄过一道沸水,这样不仅能充分发挥沸水的杀菌功能,番茄皮也更容易脱落。
去皮的原因很好理解,除了有助于除菌外,还能满足一些不喜食皮的人,并且菜品的外观也更加漂亮。那么为何又要去籽呢?除了美观之外,《三江报》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番茄有子,不易消化,食时务宜去之,否则连子同食,不幸入盲肠中,易导致发炎成患。”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还举了一位朋友因未去籽而导致腹泻的例子。
随着番茄产量的增加,以及成熟番茄软烂难以运输,除了制作番茄酱和番茄罐头,针对过剩的番茄,还出现了腌制番茄的方法来,主要有盐腌和酒腌两种方式。制作过程尤为注重消毒,番茄需用沸水烫过,储藏器皿也需用开水烫过。腌制后需等待一个月左右方可食用。这种方法被认为不仅可以延长了番茄的保存时间,而且对维生素C的损失也比煮成酱的方法少一些。
就在“维生素热”成功地推动了番茄在中国的普及时,有人开始认识到维生素并非万能的,开始理性对待维生素的作用。譬如,1949年《国华报》写道:
去年美国人在维生素上花了二亿元,我们可以很安全的说,多数的人把他们的金钱无谓消耗了。
维生素是无害的;倘使在你的饮食中不能获得必需的分量,它们自然可以发生应有的效力。不过切不可存有幻想,以为它们可以增进你的健康,充沛你的活力,或者使你容貌美好。它们是无能为力的。[14]
无论如何,在民国期间,番茄至少已经在中国的都市中普及,成为了百姓餐桌上的一道常见食材,并发展出了一道国民菜——番茄炒蛋。如今,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有狐臭的美人”,仅仅记得它曾经是那么的美味,转而抱怨当下的番茄“无味”,而且硬邦邦,难得“稀松一堆”。
注释:
[1]刘泽学主编:《中外精美散文:老舍散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221-222页。
[2]《西红柿为有益身体之食品》,《大同报》,1936年10月09日第7版。
[3]《粮食节约与营养》,《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06月02日第5版。
[4]《维生素》,《光华报》,1935年09月21日第3版。
[5]《水果治病》,《蒙疆新报》,1941年06月19日第3版。
[6]《夏之餐桌上的西红柿》,《新民报》(南京),1947年06月06日第3版。
[7]《维生素乙治不育,邓伯道莫悲无儿》,《通报》,1946年09月25日第2版。
[8]《西红柿精抑制皮肤病菌》,《医药近讯-华北日报》,1947年07月28日第6版
[9]《西红柿之食法》,《益世报》,北京,1922年09月23日第8版。
[10]《问番茄汁制法》,《南华报》,1941年05月27日第4版。
[11]《怎样制西红柿酱油》,《解放日报》,1943年09月11日第4版。
[12]《拿手菜》,《华北日报》,1947年07月06日第6版。
[13]《炒牛肉丝》,《新北京》,1939年07月10日第3版。
[14]《不吃维生素药品也可以增进健康》,《国华报》,1949年04月23第4版。

上述文章内容有限,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解决疑问,可 点击咨询 直接与医生在线交流
相关推荐
MONTH'S ATTENTION
热点文章
HOT QUESTION
本月关注
MONTH'S ATTENTION
医生推荐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